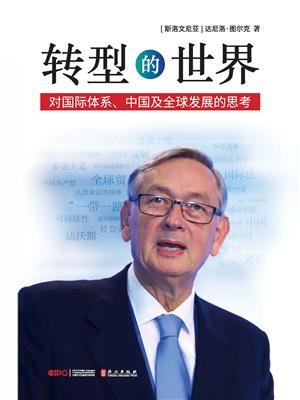04 规范、价值观和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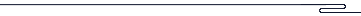
国际政治不是机械式的,价值观、规范和制度均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处的重点应放在政治上。正是借助政治的动态进程,才使得权力要素接触到价值观和规范;政治进程也决定了制度的实际运行。所以,必须以政治为中心。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国际政治局势以争夺权力为主导,持续动荡。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到眼下备受关注的叙利亚冲突和中东局势的不稳定,这种局面持续如此。历史不断提醒我们,权力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修昔底德通过巧妙地阐述“米洛斯对话”传达了一种悲观的见解:“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至今仍能在国际政治的许多情形下引发共鸣。权力总是凌驾于道德论证之上。
但是,笃信“国际政治中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是由权力和军事力量决定的”则与事实相悖,也为道德所不容。人类精神的作用、思想的力量和人类价值观的重要性将普通大众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力量决不能被低估。
然后我们来谈谈规范。政治现实主义之父尼古拉·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提醒人们注意罗马政治学家和法学家西塞(Cicero)在很久以前提出的道德观点:进行争夺有两种手段,要么借助武力,要么通过法律,但是往往必须诉诸武力,因为法律并不总是那么充分。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人,马基雅维利明显偏爱法律手段。同时,作为一名政客,他又很现实地认识到法律在治国方略和国际政治方面只是一种作用有限的工具。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建议君主要果断和铁腕。
然而,在国际政治中存在一些时刻,使用武力反而会适得其反,占上风的是人性中柔软的一面。人类价值观最终取胜,大众选择将法律作为持久的解决方案。对战争持谨慎态度的人们总是尝试寻找摆脱战争的方式,而这种探索引领他们敲开了规范与制度的大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就是这样一个时刻。该和约结束了欧洲三十年战争,构成了一个基于国家领土主权为法律原则的新国际体系。自那以后,这种法律途径一直是国际体系的主要组织原则,需要审慎对待。它的产生曾让人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它在当今乃至未来仍然是保证和平的基石。
在规范和制度中寻求解决方案的另一个重要例子见于拿破仑战争时的思想中。彼时的政治家们不得不设计出一个新体系来保持战后欧洲的稳定,因此他们苦苦搜寻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价值观、规范和制度。1805年,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在其撰写的备忘录中提出了一种有希望的方式。该备忘录的标题十分贴切,同时又雄心勃勃:《欧洲的拯救与安全》。文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创新观点,即战后的安排不能只基于欧洲帝国之间的边界变化和力量均势。皮特认为,当时需要的安排,是能够实现“欧洲普遍而全面的公法体系,并尽可能地压制未来扰乱整体安宁的企图……”
皮特备忘录成为维也纳会议上的英国外交战略蓝图,并促成了神圣同盟的建立。会上,欧洲各主要大国通过结合领土变化与政治举措,恢复了和平局面,并为此增加了新的规范和制度维度。这种方式的规范性重点是“欧洲公法”要素,是在20世纪得到深入发展的现代集体安全概念的关键。在两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无法想象倘若欧洲没有密织法律网络,即前述“欧洲公法的综合体系”——也是现代欧洲和平与安宁的可靠保证,欧洲是否还存在。
同样的规范性理念激发了20世纪全球集体安全体系的构建。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惨痛代价使政治领导人确信“集体安全”理念是构筑和平条约的核心,并扩大国际法的范围作为“争赛方式”(使用马基雅维利所做的一种表述)。1919年签订的《国际联盟盟约》提出了一系列新规范和新制度。这一新体系将仲裁和裁决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途径,整个设计源自法律思维。这并不奇怪,因为它的主要缔造者——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一位杰出的宪法教授。这位伟大领袖为此做出的卓越贡献足以获得全世界的由衷感激。
同时,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与“国际政治中规范性思想和法律途径的局限性”有关的历史教训。国际联盟过度依赖法律规范和制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鉴于历史条件,可能无法)结合另外两个关键要素——力量均势和一个共同价值观平台。这两个因素对旨在维护和平的国际机构的成败至关重要,国际联盟的解体非常清楚地验证了这一点。
事实上,联合国作为国际联盟的继任者在这方面的表现要好许多。《联合国宪章》非常成功地结合了力量均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设计及其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具有充分的历史意义——这一点已得到证实。联合国还提供了一个共同价值观的广泛平台:它包含对“视和平为最高价值”的内在承诺。在这种承诺之下,旨在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综合法律制度得到逐步发展。虽然这种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但它仍然要比早期历史上已知的其他人类价值观体系先进得多。
联合国的建设发展历程漫长而艰辛。安全理事会在冷战的四十年中似乎陷入瘫痪,彼时《联合国宪章》本身的充分性受到质疑。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前10年,在这段几乎跨越了整整一代人的时期中,安全理事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联合国宪章》缔造者的预期,这应被视为历史性的成功。
联合国系统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始于《联合国宪章》中对人权的初步规定。其中关键的发展是在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国家的共同成就标准……”
有时存在这样的观点,即“鉴于世界上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人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权实际上不能成为共同价值观的平台”。
这种批评合乎情理,引发了大众对人权的持续热议。不过,应当理解的是,制定《世界人权宣言》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主宰,而是源于对“建立一面强大的防火墙来对抗死灰复燃的压迫”的希冀——压迫是引燃二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厌倦战争的一代人来说,建立一个帮助防止压迫与战争卷土重来的制度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些压迫与战争已使得民不聊生。此外,随着人权制度建设的推进,涌现出了许多观点,提出了各种新的理念,其中包括人民自决权和人类发展权。而争论也在持续进行。人权的普遍性正在逐步、稳定、可持续地加强。
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的国际政治必须始终考虑到普遍人权的要求。人权是全人类共有价值观的一种重要体现,因此必须通过实际行动予以最大程度的奉行。现行规范、制度和国家权力都必须将之纳入其中,方能满足当今时代在这方面的基本要求。毕竟,这是人类共有价值观的目的——必须在现实生活中保护和保障人权。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做?
显然,这个问题没有唯一或统一的答案。常言道:“条条大路通罗马。”要让人权成为现实,需要做的事情还有许多。在此,让我们了解一下与国际安全问题特别相关的人权历史。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人权的实现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诞生了新的机构,最引人注目的要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同时,旨在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际体系得到了重大改进。
此外,新形势带来了人权胜利的喜悦氛围,并创造了新的道德制高点。对此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侵犯人权时期之后的情况,以及如何处理蓄意侵犯人权的人?正义就是答案,恣意妄行是为世人所不容的。但正义指的是什么?在许多情况下,它指的是起诉与严惩;在其他许多情况下,答案是真相与和解。正义似乎是新时代的主旋律。
尽管如此,人权胜利的喜悦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20世纪90年代的种族灭绝事件说明,对人权的依赖存在极为现实的限制。国际社会及其组织很难在早期阶段防止或制止暴行。相反地,人们一致认为作恶者应被起诉。为此,新的国际机构成立了,包括一系列国际刑事法庭,以及最终的国际刑事法院,它拥有广泛的、几乎遍及全球的管辖权。
在近30年后的今天,一些基本的东西变得如同它们最初时那样清晰。与不得不起诉反人道罪和战争罪犯相比,防止暴行产生的效果应当更好,预防胜于治疗。但是,在规范的作用有限,且在“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的国际政治环境中,这一点该如何实现?很少有战争是能够被明确预防的,即便能够预防,也很少是因为必要的紧迫感或必需的统一目标而采取的预防行动。对武装冲突的预防仍然是国际合作中最难以捉摸的一个方面。
如何在早期阶段应对武装冲突,以减轻其破坏性和人类遭受的苦难?冲突的形成、发展和解决都需要耗费许多宝贵时间,正如国际社会不断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事件中得到的教训。当今时代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了人类生活,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国际社会完全有理由加强其机构的职能,使它们能够尽早采取行动——当然是以外交手段,在必要情况下借助军事手段。
这种道德需求在近期几项国际声明中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在备受热议的“保护责任”(R2P)这一概念中,并且它还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大力支持。凭借2005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这种需要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规范性基础和制度支持。“保护责任”这一概念是国际社会意愿的最重要的单独表达,这种意愿要求纳入价值观、规范和制度,以防止因大规模侵犯人权造成可怕的反人道罪和给人类带来巨大苦难。
但是,仅凭联合国大会的政治声明还不够。除了道德需要、规范性及制度支持外,还必须拥有足够多的权力,而且至关重要的是采取合理的政治判断和可靠的政治指导。
后一点要求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在冲突的防止和解决上,没有其他手段可以代替合理的政治判断和可靠的政治指导,因为它们可以指引所有其他要素,尤其是军事力量。
虽然这听起来不证自明,就像一个抽象原则,但它在现实中却不易实现。在发生武装冲突之前和冲突期间,任何局势的实际情势通常都不甚明了,不可避免地被“战争迷雾”所掩盖。对实际情势的政治评估和军事评估通常不尽相同。这是因为局势本身比较复杂,或是由于参与者的政治利益所产生的认知存在差异。此外,在当今这个被媒体驱动的时代,从来不缺少支持一系列分析或特定行动方案的言论和图片,无论它们多么不严谨、不充分。这使得决策者进行有效应对变得更加复杂。
除此之外,决策者在争辩时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他们既不能混淆言论,也不能搅乱真实想法。而且,他们必须防止因偏见而削弱自身听取“令人信服的、尽管不那么受欢迎的论点”的能力。
在决定动用军事力量时,必须考虑一系列标准。对此,不能以言论代替严谨的思考。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自始至终都不存在“轻度的军事干涉”。因此,对“军事精简”方案的表述必须弃之不理。维和人员不得被派往没有和平可维护的战争局势中。除了存在种族灭绝和大屠杀威胁的情形外,不应在其他情形中尝试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而在这类情形中,需要动用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
此外,任何关于使用武力的思考都必须包含对其结束或退出策略的设想。鉴于战争形势通常是不可预知的,这点很难做到。但没有退出策略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军事专家、政治决策者和资深外交官都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为此要做的是尽早制定一套有效方案,以确保取胜,同时将冲突后正常化的可靠方案落实到位。
然后,必须让诉诸武力合法化。来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授权可以做到这一点。
过去数十年的经验一再证明了这样一个简单而基本的事实:对负责任的决策者而言,不存在“军事精简”或“外交精简”这类途径。当军事途径被视为必要与合法时,其主旨必须是为了确保实现其所宣称的目标。外交途径应包括充分参与外交的意愿,例如承担必要的外交“重任”。
如果没有包含军事力量在内的实权的支持,就很难借助政治和外交途径实现安全目标——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这一假设反过来也成立:如果脱离了价值观、规范和制度的框架,那么诉诸武力和军事力量也将徒劳无功。这是超越“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的国际政治环境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