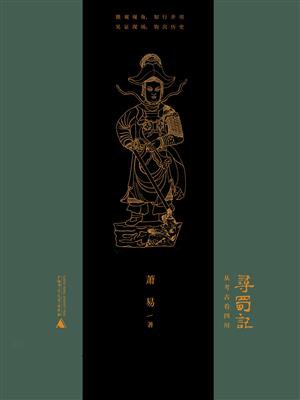宝墩遗址
改写中国文明版图的史前古城
土埂子下,隐藏古蜀密码
新津县宝墩村距离成都市区约40公里,与散落在成都平原中成百上千的村落一样,春华秋实,西河与铁溪河分别从村子东北、西南面穿过,汩汩清泉灌溉着这片沃土。要说宝墩村有什么特别之处,一马平川的旷野中,却突兀地耸起一道道高二三米、宽一二十米的土埂子。关于这些土埂子,村里流传着这么个传说:古时一条金龙与一匹天马在天空中嬉戏,霞光万道,祥云飞舞,突然,金龙与天马一头栽到村子里,一时间地动山摇,大地上就横亘着一道道类似“龙脊”的埂子了。
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些土埂子就引起了文物部门的关注。1953年,西南博物院学者徐鹏章来到宝墩村,在土埂子上找到若干汉砖、陶片,推断其为战国—汉代的古城墙。1984年,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又在土埂子上找到了若干汉代砖室墓。两年后,在成都平原另一端的广汉鸭子河畔,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被发现,出土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金杖等诸多珍贵文物,令世人得以窥见古蜀文明的荣光。有细心的学者发现,从考古地层来看,三星堆一期文化与二、三、四期文化差别很大,似乎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不过,这个质疑很快就湮没在“一醒惊天下”的喜悦之中了。
两次考古调查并没有给土埂子带来什么改变,在宝墩村,它们往往被开垦成农田、菜地,也有人觉得地势高、风水好,在上面建起了房屋。在此过程中,一些残破的陶片、磨得滑溜溜的石块也被刨出来。1995年秋收后,成都市考古队再次来到宝墩村,在一段叫真武观的土埂子上开挖探沟,结果出土了大量陶片、石斧、石锛、石凿,证实真武观确是人工夯筑成的城墙,不过其年代却比想象中的战国—汉代提前了大约2000年之久——城墙夯筑于4500年前,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龙山时代。
1996年底,一支由成都市考古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日本早稻田大学、新津文管所组成的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进驻宝墩,经过数月的调查,认定诸如蚂蟥墩、李埂子、余埂子等土埂子也是城墙遗址,它们围成了一座长1000米、宽6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的古城,这也是成都平原乃至中国西南最大的史前古城。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段课题的前期调查工作,从2009年开始,成都市考古队再次来到宝墩村,寻找到有关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的更多线索,游埂子也就成了本次调查的突破口。
276万平方米,中国第四大史前古城
我来到村里时,游埂子已被一条20余米的考古探沟拦腰斩断,站在2米多深的探沟中,城墙的横截面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根根不规则的曲线,如同藏在泥土中的水波纹。曲线是古人夯筑城墙的遗迹,古人担一些土,尔后斜向拍打夯实,一条曲线就代表这样一个过程。(图1-2、3)
游埂子长约500米,残高0.5—3米,最宽处22米,与真武观同样采用堆筑技术。这也是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古城常用的筑城方法:由平地起建,在中间堆筑数层后,再由两边向中间斜向夯打,城内侧斜坡堆筑层次多,故坡缓;城外侧堆筑层次少,故坡略陡。这样堆筑起来的城墙往往墙体庞大,坡度却比较缓和。出于防御的考虑,城墙外围往往开挖壕沟,也就是通常说的“护城河”,而中国南方充沛的降水量与频繁的洪灾,也需要壕沟排水、泄洪。
游埂子距离1996年发现的西城墙约600米,同为东西走向,这是否意味着它可能是宝墩古城的外城墙?此后,石埂子、狗儿墩、王林盘等土埂子又相继被确认为宝墩时期的城墙遗址。新发现的城墙皆位于1996年的古城外围,围成了一个更加恢宏的古城。原来,宝墩古城由内外两重城墙包围,内外城墙四个方向都挖有壕沟。就年代而言,外城墙晚于内城墙,推测宝墩古人最早生活在内城,尔后由于人口急剧膨胀,这才拓展到了外城。宝墩古城内城与外城的城市格局,是迄今世界最早的城市规划,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1许多朝代的蜀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1-2游埂子西段探沟

1-3游埂子西段剖面,城墙内部的水波纹,即是古蜀夯筑城墙的痕迹
经过测算,宝墩外城为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长约2000米、宽约1500米、周长近6200米,面积则达到了惊人的276万平方米,仅次于陕西榆林石峁古城、浙江余姚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四大史前古城。有学者曾推测宝墩内城墙土方量在25万立方米上下,按照这个比例来算,外城墙土方量约115立方米,内外城墙总土方量达到了140万立方米,今天看来依旧是个庞大的工程,这也使得后人在惊叹于宝墩古人精湛的建筑技巧的同时,对古城的人力、政权也有了全新解读——在新石器时代,人人平等的氏族公社制度已走到了尽头,贫富分化促使阶级出现,王权逐渐掌握到少数人手中,城墙就是权力与秩序的象征。
古城中心,议事厅还是宗庙?
宝墩古城的中心,有个叫鼓墩子的圆形土堆,残高约2米,周围没有相邻的土埂子,这就排除了它作为城墙的可能性。村民传言,诸葛亮曾率蜀军七擒蛮将孟获,鼓墩子是诸葛亮操练兵马的点将台。不过,传说中的金戈铁马并未在发掘中出现,从地层面貌来看,鼓墩子过去是块水田,汉代人垒起了几十个一两米长的土埂子,排列成扇形;宋代人则开挖了一道道沟渠,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历朝历代的蜀人在田间辛勤劳作的痕迹。
随着汉代、宋代地层被一层层清理完毕,大约500平方米的考古探方中露出了42个1米见方的方形柱坑,根据走向可分为三部分,主体建筑长20米、宽10.5米,保留柱坑28个,其中东、西侧各8个,南北侧各5个,房屋内部2个;两侧各有个厢房,北厢房长10米、宽7.5米,南厢房长9米、宽8米,组成了一个“品”字形复合建筑。这也是宝墩遗址最大、成都平原最早的大型建筑遗址。
为了修建这几座大房子,宝墩古城的“建筑师”可谓殚精竭虑:建筑采用立柱式承重,先开挖柱坑,竖立梁柱后再加盖主体建筑,42根大型梁柱,可以想象主体建筑有多么恢宏。
进一步发掘表明,几座大房子周围并未发现灰坑等生活遗迹,倒是出土的陶罐、陶壶做工精细,纹饰精美,暗示这里并非普通百姓的居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多年来一直主持良渚古城的发掘,他认为大房子与良渚古城发现的大型建筑颇为相似且规模更大,可能是原始议事厅或宗庙场所。(图1-4)
鼓墩子外围有一些小型房屋基址,从残存的柱洞与基槽来看,应为“木骨泥墙”结构。所谓“木骨泥墙”,墙体用树干做骨架,在此基础上编排篱笆,敷上厚厚的湿泥,再架上柴火将其烤干,这样的房屋具有通风、防潮的优点,在南方尤为流行。
房址附近的灰坑出土的陶器、石器、种子,则成为复原宝墩古人生活的线索:水稻、粟的出现暗示宝墩古人已是刀耕火种,过上了定居生活,他们还时常采集野生薏仁、豇豆、小米;狩猎是宝墩古人获得肉食的主要来源,锋利的石镞、石刀是得心应手的兵器;生活器皿则以陶器为主,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曲沿罐、折腹钵等,其上装饰水波纹、新月纹、指甲纹、长条纹等。
源自古羌,追踪宝墩人迁徙之路
迄今为止,成都平原并没有更为古老的遗址发现,那么,宝墩人究竟来自何方?岷江上游的茂县营盘山,曾发现一个距今5000年左右的遗址,出土文物既与宝墩文化相似,又与甘肃、青海一带的马家窑文化有诸多关联。从年代上说,马家窑文化更早,历来被认为是古羌人创造的文化。如此说来,便有这样一种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一支古羌人从西北高原而下,经岷江上游来到成都平原,成为最早的拓荒者。

1-4宝墩古城大房子航拍图,这座规模庞大的史前建筑可能是古城的宗庙


1-5郫县古城遗址,正中等距离分布着五个竹编围成的鹅卵石台基,可能是古城的祭台
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江章华副所长认为,这支迁徙的队伍种植小米,最初活动在平原西北至西南靠近山地的边缘地带,这里地势相对较高,人口少,聚落也不大,比如2009年在什邡市发现的桂圆桥遗址,距今约5000年,与营盘山文化十分相近。大约4500年前后,长江中游的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成都平原,这时期的古人开始平整土地,修建灌溉设施,种植水稻,逐渐向平原腹地移动。水稻的种植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人口不断增长,聚落不断增多——习作方式的改变最终带来了文化面貌的变化。
江章华的推断是建立在诸多考古发掘基础上的,自1996年以来,几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陆续在成都平原被发现:郫县古城(图1-5),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崇州紫竹古城、双河古城,2001年与宝墩古城一起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大邑盐店与高山两座古城又相继被发现。
几座古城中,郫县古城尤值得一提,古城长620米、宽490米,城墙最宽处尚有40米。在古城的中心地带,鹅卵石围成了一个长51.5米、进深10.7米的房屋基址,正中等距离分布着五个竹编围成的鹅卵石台基。这座约550平方米的奇特建筑被推测是郫县古城的宗庙,五个台基寓意五座祭台。祭台周围并未发现礼器,也许这座宗庙还略显简陋,不过这里吟唱的咒语与上演的仪式,却是成都平原上最古老的祭祀史诗。
八座古城出土陶器以绳纹花边口罐、敞口圈足罐、喇叭口高领罐、宽沿盘、浅盘豆为主,与龙山文化典型的陶鼎、陶鬲、陶甑、黑陶高脚杯风格迥异。(图1-6~9)综合陶器、城墙,成都平原八座史前古城明显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又以宝墩古城面积最大、最为典型,由此命名为“宝墩文化”,大约距今4500—370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这也是继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商末周初的十二桥文化(以2001年发现的金沙遗址为代表)之后,成都平原发现的又一文化类型,也是成都平原最久远的文化章节。
恢宏的城垣与奢华的建筑,暗示着宝墩古城已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城市,中国学者也称为“都邑”。西方学者往往将青铜、城市、文字与祭祀体系视为文明的标志,由于古城尚未发现青铜、文字,宝墩文化似乎还未迈入文明的门槛,不过在我看来,它却如启明星一般,照亮了文明前夜的成都平原。
划破长空,证明长江流域文明多样性
宝墩文化的意义远远未竟于此,此前,许多游客在惊叹于三星堆无与伦比的青铜文明同时,时常追问:“那些凸眼球、长耳朵的青铜人是否是外星人的写照?”“三星堆是外星人创造的文明吗?”他们的导游对这样的问题往往未置可否,一笑了之。的确,这曾是考古学家也无法解答的问题。

1-6敞口圈足罐

1-7宽沿平底尊

1-8喇叭口高领罐

1-9绳纹花边口罐
答案就隐藏在宝墩文化中。曾经令诸多学者困惑不已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出土的宽沿平底尊、浅盘豆、敛口钵、敞口圈足罐,大多是宝墩文化典型陶器,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极为相似。如果将三星堆文明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宝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
唐代诗人李白有感于古蜀历史的神秘,在《蜀道难》中发出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感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相继发现,揭开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面纱,宝墩文化则将成都平原的历史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并成功建立起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以金沙遗址为代表)连续的考古学序列。
宝墩文化同样改写了中华文明版图。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过去受中原中心说的束缚,黄河流域一直被认为是文明起源的中心。近半个世纪以来,诸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的文明高度与黄河流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独特地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进而将中国古文化喻为“满天星斗”,文明起源又有了多元说,中原地区、山东地区、辽宁—内蒙古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地区、江浙地区都曾被视为文明起源的“星斗”。
中国西南考古起步较晚,此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少之又少,文明的火种一度“星光黯淡”。宝墩文化却如流星一般划破长空,证实了巴蜀地区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一元,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交相辉映,进而说明长江流域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2011年12月,鼓墩子附近又发现两座大房子基址,宝墩古城还在不断带给世人惊喜。但频频发现的城墙、大房子却掩饰不了宝墩古城少有精美文物出土的尴尬,同为史前古城,良渚古城以精美的玉璜、玉璧、玉琮、玉镯、玉牌、玉钺为代表,陶寺古城则发现了诸如特磬、龙盘、鼍鼓等高规格礼器,而宝墩仅有简单的陶器、石器出土。
根据陶寺、良渚的发掘经验,龙山时代高规格文物往往见于墓葬中,比如良渚反山、福泉山、瑶山、汇观山、寺墩的大墓,棺、椁中以玉琮、玉璧、玉钺随葬;陶寺古城则有整齐划一的墓葬区,面积超过30000平方米,小墓往往空无一物,大墓则葬有木棺,随葬品有一两百件之多。迄今为止,宝墩古城只发现了几座小墓,墓坑浅而窄,墓中空无一物,可能是下层百姓的墓葬,而巨大的城垣与奢华的大房子,暗示着在宝墩村的某个角落,一定藏着宝墩王者的长眠之所。
站在鼓墩子上,向东,向南,向西,向北,四野尽收眼底,一片片冬小麦铺满大地,中间点缀着稀稀落落的村舍。4500年前,不可一世的宝墩王者是否这样环顾着他的国度,尔后选择自己的灵魂栖所?这块风水宝地究竟埋藏在何方?伴随王者长眠的又是什么?从1995年开始,我们走进了宝墩古人的城市以及他们的生活,却从未走进他们的内心。对于宝墩文化的探索,或许才刚刚开始。

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了众多精美的青铜器,纵目大面具,眼睛呈圆柱状往前伸出;青铜大立人通高260.8厘米,是世界同时期最大的青铜雕像……这些自成体系的青铜器,被古蜀人用于祭祀,追忆和崇拜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祖先、无所不能的神灵,向后人展示着他们天马行空的幻想、艺术乃至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