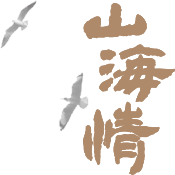
一
从苦水村到金滩村,四百多公里的路程,几乎全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水花足足走了七天七夜,谁都无法想象其中的艰辛与困难。
得福问过,水花轻描淡写地说,也不太难,反正觉得难熬的时候,就叫女儿晓燕跟她一起叫,你一句快了,我一句快了,就这样大声叫着,似乎就不觉得难了。
水花说她还唱歌,唱西海固流行的花儿:
……走远咧……越走越远了,心里的惆怅种下了,走了走了,越走越远了……
当然也有困难的时候,比如晚上实在走不动了,就扎营睡觉。水花说她一个人要先在沙地上靠板车支顶篷,风吹得帐篷布扑拉拉响,系都系不住。好不容易将篷支起,让女儿坐进去,再去将永富背下板车,她力气小,有时腿一软两个人都摔在沙地上。
但是支好篷了,一家人或坐或睡挤在篷里,水花说那时候她心里却是十分安宁。
得福听着,心里又是难过又是酸楚,却强笑着说来了就好。
是的,来了就好。
水花的到来,让整个事情峰回路转,得福被逼到走投无路的通电工作,因为水花这一户,五十九加一,刚好六十户。得福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他最无助绝望的时候,突然伸手拉他,不仅让他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巨大的困难,还能够让他从此天天都可以看见从前的爱人,生活一下子变得美好起来。
但是他父亲马喊水显然不这样看。
这天晚上,得福急匆匆回到家里,在院里杂物堆里翻箱倒柜地找东西。
马喊水从屋里出来问他干啥,得福犹豫了一下,还是坦白说水花来了,水花她男人腿砸坏了,还带个娃,他找东西去给她把地窝子顶加固一下。
马喊水听见水花的消息,吃了一惊,问:“她咋来了?她不是没有指标吗?”
得福继续翻找:“大,你咋知道她没指标?她是主动来移民的,我明天就带她去找张主任申请指标。大,咱家不是还有剩的牛毛毡……”
马喊水没听见儿子的问话,他在低头思考问题,片刻,他就下了决心,抬头说:“儿呀,你在吊庄办干事,给大帮个忙咋样?”
得福一愣问道:“啥忙?”
马喊水看着儿子,认真地说:“把水花一家办到别的移民村去。”
得福吃惊道:“这是为啥?咱村就差一户就能通电了……”
马喊水打断他,直截了当地说:“看你刚才那㞞样,一说水花,脸颜色都变咧。我给你说清楚,你现在端着铁饭碗,吃着公家饭,你得进步,得发展,得往前看,别再想这些八竿子都该打远的事。”
得福又是尴尬又是不悦,苦笑着说:“大!都这么些年了,你还……”
马喊水说:“我还咋?当年你俩闹腾的,你差点儿连学都上不成咧。不是我果断出手,把你拉回来,还有现在的你吗?”
得福无奈地叹着气说:“你以为我还像当年一样是不是?我跟你说,水花早不是原来的水花了,我也不是原来的我。我就是觉着她可怜,能帮就帮。再说,安置好每个来的吊庄户,那也是我的工作和职责……”
马喊水不耐烦地打断道:“就问你这忙帮不帮?”
得福沉默。用沉默表示反对。
马喊水转身便走,冷笑道:“行,不给你老子面子,我找你们张主任去。”
得福赶紧喊道:“大!大!”
马喊水头也不回地走了。
得福苦笑着喊道:“你去了也是白去,张主任也会优先考虑通电的事……”
马喊水才不会愿意让得福的“生活变得美好”呢!他了解自己的儿子,同时对儿子寄予厚望,“福娃子有官相”,他不允许水花影响他马家唯一将来可能做官的娃,即使只是一种假设也不行。
他推出自行车拧着眉骑上,直往村外冲,要连夜去吊庄办找张主任。
可是他突然一捏刹车停住,目光直直望向前面。
只见水花满脸是汗,从架子车上搬下一大件家什,又转身回去背另一件。双腿残疾的安永富抱着四岁的女儿坐在地窝子旁边的地上,水花筋疲力尽,大口喘着气。
马喊水看不过去了,走上前给水花搭手。
水花抬头认出马喊水,不禁一怔,又露出笑脸道:“喊水叔。”
马喊水冷着脸点头,帮着水花把东西放在地窝子前的地上。水花让女儿叫马喊水爷,又给丈夫永富介绍说是娘家门上的喊水叔,永富面无表情地招呼了一句,水花歉意地笑笑,晓燕突然猛咳不止。
马喊水关切地问:“娃咋咧?”
水花抱起女儿,捶着背说:“唉,来的时候光知道远,一走才知道有多远。七天七夜,路上吃路上缓,娃嗓子就成这咧。”
马喊水望着水花蓬头垢面的样子,望着永富残疾的腿,望着晓燕,又看了眼架子车上还没来得及卸下的农具和灶具,眼睛瞬间潮湿。
他伸手揉了揉眼窝说:“你这地窝子有时间不住人咧,这顶不行了,回头我让福娃子来收拾一下再住。”又看了一下晓燕,说:“应该是水土不服了,没啥事。”
此时得福带五蹲、拴闷、秀儿等一行人,背着物资来修地窝子。熟悉的村民热情地打着招呼……
看到帮忙的老爹,得福露出了笑容。马喊水瞪他一眼,说:“把顶子好好收拾一下,都弄结实了。”又喊水花,带上娃去家里,先做口饭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