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
冤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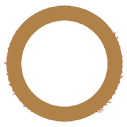
在刘大鼻子的山地上,蛇仔春拿着一条藤鞭,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这是一片松杉林,前前后后有五万多株,全是属于刘大鼻子的,其中有些是他霸占山地,强迫农民给他植苗的,有些是连林和地一起霸占的,有些是租出山地给农民植苗,没有到期又给他借口收回的。这一片松杉林,看去苍翠葱茏,十分可爱,实际上这里也是血泪斑斑。金石的父亲就是吊死在这里的一个,因为他租了山地,用了全部家当,借了债,种下了树苗,指望到期有个收成,不料刘大鼻子那年从省城回来,说他旧欠未清,硬生生地收回去,他才寻了短见。刘申在刘大鼻子家当长工,也曾被工外加工,赶到这里种过树苗。蛇仔春从这头走到那头,一路吆吆喝喝:
“快点啊!要想领工钱就快点!啊?”
松杉林里,有二三十个农民在砍伐已经成材的杉木。斧头伐木的声音,锯木的声音,一棵大树倒下来了,树枝折断的声音,还有人声,响成一片。采伐杉木一共是一千根,是刘大鼻子的弟弟刘德铭代他接洽卖给省城的,他从县城回来之后,马上就开工。
刘申也是被雇的短工,他的病还没有好,勉强起床带病上工。爬上山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汗湿透了褂裤,眼睛发花。拿起斧子,手抖得厉害,砍几下要歇一会,别人砍倒了一棵大树,他还只在树根处添上几道白印子。
蛇仔春走到他面前,用藤鞭在他背上敲了一下,冷笑说:
“啊,我们请了一个老太爷来了!”
“冯先生,我病了几天,气力不够,咳……”
“气力不够?喝点人参汤补一补啊!”
“冯先生,请你包涵点!”
“他妈的,是下帖子请你来的,还是派轿子接你来的?做不动,你来干什么?”
“家里没有吃的,没有办法,……咳……”
“好,是你自己说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不能领有办法的工钱!你就可要记清楚呀!”蛇仔春再盯了他一眼,荡到另一边去了:“你们看什么?快干!”
太阳落山之后,大家都收工回去了,刘申一步一拖地走着,金石在旁边陪着。
“申哥,你不该来的,累坏了身体,还要受蛇仔春的龟气!”
“唉,累死好过饿死,一天不做,一天没得吃。”
“晚嫂呢?她身体好,能扛能抬,是一把好手,不比我那个。”
“一个妇道人家,能做也有限啊!再说,现在有什么可干的,淘沙,轮不到我们;托杉,又没有个准;唉,难呀!不知道怎么个了局。”
“饭给刘大鼻子一个人吃尽了!田是他的,山又是他的,兄弟做县知事,自己当乡长,独霸一方,我看皇帝也不会比他好多少。有他的份,自然就没有我们活的!”
“金石,快别这样说!传到他耳朵里去,又该我们倒霉!”
“倒霉,我们的霉也倒尽了,还有什么可倒的?申哥,你在刘家打长工,有二十年吧,人累坏了,别说他应该养你的老,人情总该有一份呀!好,一脚踢出门,……”
“只能怨我的命……”
“申哥,我说你就是怕事!”
到刘大鼻子家时,蛇仔春照花名册发工资,只剩下三五人,其余的临时工差不多散清了。刘申和金石站在一旁等候。最后,蛇仔春对金石说:
“刚才叫了你,你死到哪儿去了?人穷架子倒不小!家里不等钱用,是吗?不等钱用,就别来!”
“你以为我想来的吗?你以为我喜欢这份工的吗?”
“他妈的,口胃倒不小!”
“将力气换饭吃,有什么口胃小不小!”
“刘金石,我知道你的牛脾气,小心点嘛!”蛇仔春卷起花名册,转身走了。
“冯先生,还有我呢?”刘申慌忙上前追问。
刘大鼻子走出门口,站在台阶上,大狼狗跟他一起出来,在他旁边摇尾巴。
“你还想要工钱?”蛇仔春将花名册在手心拍了一下。“我问你,你做了多少工?”
“冯先生,我是做少了……”
“少做就不给!你自己说过没有办法……”
“你这是哪一门子的道理?少做顶多是少给,怎能不给呢?”金石气愤得抢前一步,大嚷起来。
几个临时工也回转来看着他们。
“你是谁?你知道在哪儿说话?”刘大鼻子的鼻子更红了,大声的骂起来。“混蛋,在我家里都敢吵闹,还有王法吗?”
蹲在地上的大狼狗,听见主人骂人,“汪汪”的吠了两声。
蛇仔春在旁边也帮腔:“不知死活的家伙!”
“王法?……”金石还想说话。
“金石,你少说两句吧!”刘申拦住了金石,转身向刘大鼻子:“老东家,我做得少,你就少给些吧,他们五斤米,我两斤米都值吧!”
“一斤也不给!”刘大鼻子说。“告诉你,我刘德厚不是克扣下人工钱的人,可是你误了我的工,这就误了大事,不罚你,已经是我老东家的宽厚了!”
“罚我?”
“是呀,罚你!”蛇仔春开口了。“东家砍木头是国家大事,啐,说了你也不懂……”
“少跟他说废话!”刘大鼻子打断了蛇仔春的说话。“刘申,你不去,我可以请多一个工,你挂名不做事,有工夫鬼混,我可给误了大事。滚吧,再呆下去,惹我发脾气,那就不能怪我了!”
“老东家,咳,咳……”刘申走近刘大鼻子,想再求求他。
“欧兮!”刘大鼻子唤狗去赶刘申。
大狼狗跳起来,就向刘申扑过去,吓得他一面急忙向后退,一面伸拳作势来招架。大狼狗逼得刘申退到墙角,它还是举起前腿,站得老高的要咬过去。
“你们要杀人哪!他是有病的人,你们用瘟狗来吓他,还有良心没有?”金石跳到刘大鼻子面前,拳头举得高高地对他说。
刘大鼻子对蛇仔春说:
“赶他出去!”
这时,突然听得刘申“哇”的叫了一声,他的右腿上裤子破了,连皮带肉给大狼狗咬下一大块,血淋淋的。大狼狗也给刘申顺手拿到的木柴,打中了鼻子,躺在地上直喘气。刘大鼻子和蛇仔春,急忙抬它到屋里去。
金石扶起刘申,那几个农民也过来帮助。他们一路走,一路骂。刘申腿上的血,一路向下淌。走过小木桥,刘申又吐了一口血,血饼落在河里把河水映红了。
送到家里,刘申眼睛发黑,睡在床上,胸口象火烧似的难过,腿上也疼得很。申晚嫂一面用破布将伤口包扎,一面听金石讲原委。她恨得牙痒痒的,不断咒骂:
“狼心狗肺的东西!……”
阿圆吓得缩在一边,睁着大眼睛望着。
邻舍们来了一大群。四婆坐在小凳上,感叹地说:
“还说是老东家?老东家就下这样的毒手!”
“他妈的,刘大鼻子,这个吃人不见血的笑面虎!”金石更是愤慨。“申哥帮他做了二十年工,身体糟蹋坏了,他养申哥一辈子也是应该,现在为了两斤米,你们说说,就是为了两斤米,两斤米都不够他刘大鼻子一口洋烟,就这样干了!我操他十八代的祖宗!”
“绝子绝孙啊!”
“有钱人的心是铁做的啊!”
申晚嫂包扎好了伤口,刘申昏昏沉沉的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晕了过去。她想:这回是完了,人搞成这个样子,又没钱医,要想复原,怕难有希望了。自己嫁了三次,咳,命多苦啊!现在又加上一个阿圆,孩子可怜,瞧她缩在墙角,又惊又怕。有钱人家的孩子,十岁八岁还要喂饭吃,我们的孩子什么苦也尝够了。唉,阿圆的爸,你要是好好的,我们一起来熬日子,会有出头的一天。如果……,苦还会有个尽头吗?天诛地灭的刘大鼻子!我们一家子算完了,坑在你手上了。她越想越乱,越想越恨,在乱里头她很清楚的想到刘大鼻子,恨集中在刘大鼻子身上。突然,她站起来,向门口冲去:
“我跟他拼了!”
许多人来拉住她,劝她:
“晚嫂,不行呀!”
“照顾申哥要紧,有账慢慢来算。”
“鸡蛋哪能跟石头碰啊!”
阿圆也哭着跑过来拉着她的腿:
“姆妈,姆妈!”
申晚嫂气得涨红了脸,一面想挣脱,一面申诉:
“这口冤气,叫我怎么忍得下去啊!”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刘申已经醒在床上,他听外面狗吠得厉害,人声嘈杂,由远到近,好象到他家来似的。他吃惊了,紧张地叫醒申晚嫂,她急忙下床,轻轻地开了大门,只见蛇仔春带了几个乡公所的所丁,从金石家里,将金石反绑了手,推推搡搡地拉了出来。旁边有些农民愤愤不平地望着。
“我犯了什么罪?”金石大声喊叫。
“恭喜你呀!”蛇仔春阴险地笑着。
“壮丁中了签,送你去升官发财!”
“他是独子啊,拉走他叫我们母子怎么活呀?”
“他妈的!”蛇仔春用力推开金石二嫂。“当壮丁嘛,又不是要他去见阎王!再说,中了签,大总统的儿子也要去的。”
申晚嫂转身告诉刘申,他一怔,出了一身冷汗,咳嗽着,断断续续地说:
“咳,……都是为了我!”
“不为你也要抓的。”
“他这个牛精脾气!唉,二嫂怎么过呢?”
“……真叫人受不了!”
蛇仔春一脚踢开大门,“嘭”的一声,吓得刘申在床上跳起半寸多高,阿圆也惊醒了。
“好啊!你们高卧未起,打扰啦!”蛇仔春一副泼皮无赖相:“刘申,你闯了好大的祸,知不知道?”
“冯先生,……咳,我们是粗人……”
“粗人?怎么着,粗人就可以造反?”
“他生病,你有话好说,不用这样嚷!”申晚嫂捺着性子,严正地说。
“喷,啧!哎哟!生病?你他妈的是贵人多病啊?”蛇仔春说得更大声。“姓刘的,告诉你,大先生的狼狗给你打死了,我来给你算账的。”
“人咬伤了还没有去算账,狗死了倒来算账?”申晚嫂怒冲冲地说。
“男不跟女斗,鸡不跟狗斗,我知道你是泼妇,我问你,你家里有男人没有?”
“冯先生,……”
“谁要你叫冯先生!大先生的大狼狗是死了,这是他心爱的东西,本来要叫你垫棺材底,不过看在老宾东的份上,他说免了。可是,钱总得要赔,他买回来的时候,花了五十块港币,四年的伙食,一顿四两牛肉,还有米饭、人工,他妈的,反正这笔账算不清了。他老人家吩咐,不必算细账了,你佃耕的八分水田,他收回去了,今年的收成,全部归大先生,另外,你住的这间房子,也算是赔偿,还要外加两担谷子……”
“这不是杀人吗?”申晚嫂冲到蛇仔春面前。
蛇仔春转身就走,走到门口,他说:
“话是说定了,限你们五天搬家!田里不许动一下,要是去了,当心你们的狗腿!”
申晚嫂气得要发疯了,抿紧嘴,手握成拳头,站住一动也不动。来了几个邻舍,心里恨得要命,但不晓得怎样说话才好。申晚嫂看到阿圆蜷缩在床里边,象一只受惊的小猫,令人可怜。刘申闭着眼睛,脸色灰白得象麻布,嘴唇合拢,嘴角上流出泡沫和血。申晚嫂跑过去伏在他身上嚎啕大哭。四婆慌忙上前,探探胸口:
“胸口还暖,是昏过去。谁有艾绒?”
有人跑回家拿了艾绒来,点好放在刘申鼻子前,熏了一会,他慢慢苏醒。大家帮他抹掉泡沫和血,又倒了一杯开水给他,这才安定下来。
申晚嫂坐在刘申床前,看到他一时清醒,一时又昏昏沉沉。清醒的时候,两眼无光,直流眼泪,对她说:
“我不中用了,害了你们两母女!……”
“你别……”
申晚嫂想叫他别说丧气的话,别把一切罪过自己担戴起来。是谁害了她们的,分明是刘大鼻子,不是他。她一向不满意他的胆小怕事,树叶子落下来怕打破头,连她稍微反抗一下,他都吓得赶紧拉她回去,但是看到他在生产上勤勤恳恳,对自己又好,更加上病不离身,平素也就原谅他、顺从他。现在,他们和刘大鼻子仇深似海,她以为一定要报仇,他却绝口不提,老说些丧气的话,她恨他的懦弱,同时也怜惜他。想到结婚以来,两人恩爱,半路上少了一个,将来的日子,多可怕啊!她忍耐住,转而安慰他:
“你放宽心吧,养几天就会好的……”
刘申摇头。
“晚嫂,你出来,我有句话跟你说。”
四婆在门外叫她。四婆这两天要去金石二嫂家里,又要到刘申家里,两头忙。这个老人家变成了他们的支持力量,帮他们出主意。
“晚嫂,他这个病不轻呀,一定要请个医生看看。”
“四婆,你知道……”
“当然知道。不过,我是过来人了,不怕你生气,家里少一个男人,就象屋子少了一根顶梁……”
“是的,我……”想起两次守寡的生活,她忍不住哭泣。
“你瞧,金石被拉走之后,二嫂好象天坍下来似的。晚嫂,人总是要紧哟,留得青山在……”
“我也是想医好他……”
“想办法啊!”
有什么办法好想呢?借,没处借,卖,没得卖;人又非尽力救治不可。她仿佛掉在黑漆漆的山谷里,摸索不出一条路来。
“晚嫂,你不要骂我狠心,我看,阿圆……”
“卖阿圆?”申晚嫂睁大两只眼睛,吓得慌慌张张。
“不行,不行!”
“你救申哥要紧啊!再说,不要卖断,订五年期,到时有钱再赎回来。”
“不行!我不卖,死也不卖!”
当晚,她睡在床上,阿圆和她一头,睡得很熟。她一只手放在胸前,一只手握住申晚嫂的手臂,好象怕妈妈跑掉似的,申晚嫂将她拉近些,脸靠着脸,她轻微的呼吸吹着她的脸。申晚嫂看到她可爱的模样,懂事聪明,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她。
“这是我的性命,怎样也不能卖!”
刘申又发出呓语,一连串的胡话还夹着哭声,半夜听到叫人汗毛直竖。申晚嫂的心,象给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抓着,感到绞痛。
“眼看他死掉不救?”
“不能!不能又怎样呢?”
“卖女儿?不行!不是卖,是押,五年之后赎回来。不行,到时候没有钱赎怎么办呢?不要紧,我们两个人做工,五年也能省下点钱。不行,我舍不得!不是卖,是押!人还是自己的,可以赎回来。丈夫死掉了,还有什么呢?……”
一夜都是反复斗争,申晚嫂睁眼到天亮。早上,她的头痛得厉害,眼皮也肿了。
“今天是第五天了,他们会来赶我们的,晚嫂,……我死都没有个地方……”刘申时刻忘不了蛇仔春的威胁,象一根骨头卡住他的喉咙。
“大清早,别说这些——我就不搬,看他们怎么样?”
“大腿比不上人家胳膊,拗不过他们!”
“拗不过,拗不过!”申晚嫂将下面的话忍住了:“你说这些干什么?叫人心烦!”
申晚嫂走到四婆家里。四婆一见了她,放下手上的功夫,急忙对她说:
“晚嫂,昨儿跟你说的话,你不要怪我。我不是拆散你们母女,我是为你打算的呀。你以为我喜欢人家卖儿卖女吗?一想起我那个丫头,卖出去之后,生死存亡,一丝风声都没有,我的心就碎了。你家的阿圆,乖巧伶俐,别说你舍不得,我何尝舍得呢?唉,能有第二条路走,谁肯走这条路?”
申晚嫂做事从来有决断,她的性格象一块钢,如果能够敲的话,会“铛铛”的响,现在,一头是丈夫,一头是女儿,叫她来分个轻重,她就手掌手背分不出厚薄了。等四婆说完,她自言自语的说:
“不卖,一定不卖!”
“能有别的法子想,不卖就不卖吧。申哥今儿好些吗?”
“好些了。”
她随口应了一声,慢吞吞走了。走出门口,她又责备自己:
“好些了?谁说好些了?要不快点医治,人影子也没有了。……我来干什么的?话没有说清楚就走,真是掉了魂!”
她回转身又进去。四婆摸不清她干什么,连忙迎上来。她劈头就问:
“是不是一定要卖?”
“不一定,不一定!卖不卖,你自己作主,人家怎能逼你卖呢?”
“不是,我问你:不卖可以不可以?”
“可以,可以!”四婆赶紧申辩。“我不是一定要你卖的!”
“不是,我说押给人家……”
“哦!前几天我听说迳尾黎木林,他要‘妹仔’,买、押都行,……”
申晚嫂自管想着,四婆再说些什么话,她听不见了。她下了狠心:
“救他的性命要紧!救他的性命要紧!暂时押出去,暂时押出去!”
她回家的时候,一路说着这几句话。回到家里,拣出一套算是最好的衣服,给阿圆穿上,又拿邻舍送来的米,煮了干饭,要阿圆吃饱,吃了还要她再添,阿圆天真地问:
“姆妈,今天是过节吗?”
申晚嫂听了这话,好似万箭钻心,她想伏在桌上大哭一场,当着刘申和阿圆的面,怎能这样做呢。她背转身,偷偷抹眼泪。
阿圆又问:
“眼睛有灰吗?”
“乖乖,你吃吧!”她紧紧搂着阿圆。
“你们有什么事?”刘申也忍不住问了。
“你别理!”申晚嫂想到这样说不妥当,接着说:“我和阿圆去傜坑,怕她肚子饿。”
“扛木头不要带她去呀!”
“留在家里没有人看她……”
“晚嫂,”刘申拗起半身,想拦阻她们,但一阵急促的咳嗽,使他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才断断续续地说:“你不要做糊涂事啊!”
申晚嫂拉着阿圆的手,走出门来,正遇着四婆来找她。
“你不要去吧,申哥要照料,我来送阿圆。”
“不!”申晚嫂拒绝了。“我自己送她去,心里好过些。请你照顾一下他。”
申晚嫂背起阿圆,还带了一副空箩筐,眼睛红红地走了。四婆望着她们,轻轻地摇头,叹了一口气,就进门去看刘申了。
从虎牙村到迳尾有四十里山路。申晚嫂一路和阿圆谈个不停,她用谈笑来遮掩心里的痛楚,用谈笑来表示对女儿的情爱。阿圆从来没有看到母亲这样快活过,她也是快活得很。在母亲的背上,摸摸母亲的发髻:
“姆妈,你没有梳头。”
申晚嫂心里回答:“妈的心快碾碎了,哪有心思梳头!”
有时,阿圆看到一些野果,就问:
“这是什么果子?姆妈,我要吃!”
申晚嫂不但去摘,而且摘了一大把,阿圆两只手也捧不完,漏掉很多。阿圆笑得浑身动起来,连连说:
“好多啊,好多啊!”
申晚嫂心里在说:“孩子,你要什么,妈给你什么,你要妈的命,妈也给你。”
走到迳尾,找到了黎木林的房子,一连三进的大屋,原来是一个大地主。申晚嫂的心都凉了:
“这不是送女儿入火坑?不行!”
她脚步停下来,然后回头走了几步。
“姆妈,我们又回去?”
“回去?”申晚嫂想道。“回去怎么成呢?不是等钱救命吗?”
到底她还是进了门。阿圆的头靠近申晚嫂,在她耳朵旁边,低低地问:
“我们来做什么?”
“阿圆,妈害了你……”
“姆妈,你说什么?”
“没有什么,这里有好东西吃……”
黎木林看看孩子,尽在挑剔:
“太瘦,太小,要养多少年才能变钱呢?”
黎木林的老婆,拉他到旁边,对他小声说:
“长得倒是眉清目秀,将来可以捞他一笔。”
“她是押的,不是卖的。”
“啊哟,量这穷鬼也赎不回去。”
谈好身价,然后黎木林的老婆领她走开。
“姆妈,我不去!”阿圆缩在妈妈背后。
“去,乖孩子,太太有糖给你吃!”申晚嫂哄了好久,她才答应。申晚嫂最后一次紧紧抱着她,用力的亲吻她,小心地替她把衣服拉好,又抹平她的头发。
“姆妈,你等我呀!”
阿圆走了。申晚嫂象被打了一棍,差不多昏倒。她跌跌撞撞地又追出去看,看不见了,她冲到黎木林面前:
“我求你不要难为她,她还小,不懂事!”
“废话!你舍不得,领回去好了!”
申晚嫂糊糊涂涂地在契约上盖了指模,黎木林又说:
“我们讲明在先,往后你不许来找她。再有,契约上写明,限期五年,到期不赎,就算卖断了。你明白吗?啊?”
申晚嫂象犯了罪似的,只求快点离开。头脑昏昏,脸上象火烧似的热烘烘,胸口好比受了重压,气也透不过来,听不清黎木林说些什么。她走出大门,还想再看一眼阿圆,黎木林恶狠狠地挡住了她。她出了村子,忍不住放声大哭:
“阿圆,妈狠心,坑了你啦……但愿救了爸爸的命,一定来接你回去!”
申晚嫂回到虎牙村时,已经快要上灯了。刚进村,只见村西鱼塘边的烂屋门前,围着一大群人。这两间烂屋,是本村的公共屋,堆放些柴草杂物,但早已放弃不用了。它们互相依靠着,假使将它们分开,哪一间也不能单独站得住。屋顶倾斜,好些地方的泥砖倒坍了,露出三四处的缺口。这是虎牙村最破烂的房子,平时简直没有人来过问,一直孤零零地被冷落着。今天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莫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情?申晚嫂的心抽搐,挑着卖女儿的八十五斤谷子,摇摇晃晃地站不住脚。
“回来了!”有人嚷着。
四婆从烂屋里跑出来,眼泪鼻涕一脸的拉着申晚嫂,半晌说不出话。
旁边有一个人说:“申哥过世了!”
申晚嫂石头般的站着,失去知觉有一两分钟。肩上挑的箩筐滑落,谷子倒翻地上。
“真是缺德呀!封房子、赶人,送掉一条性命。”
“蛇仔春将他摔出大门,跌在露天,又生气又受惊,怎能不死呢?”
申晚嫂进了烂屋,看到刘申躺在那儿,说不出,哭不出,邻舍们在帮她出主意,安排料理后事。
蛇仔春又带着一班人来了,看到谷子,冷笑道:
“好,说没有钱,原来还留着谷子送终!来呀,挑走!”
跟他来的人,心里也有些不忍,踌躇着不敢下手。蛇仔春暴跳起来:
“他妈的,看什么?挑走!”
乡公所所丁赵三被他威逼着,只好慢慢上前去挑,嘴里嘀咕:
“挑就挑喽,恶什么?”
蛇仔春的突如其来,蛮横不讲理,使得在场的人也都动了火,大家愤愤地盯着他。申晚嫂慢慢从烂屋走出来,看到蛇仔春在那儿大模大样的指手画脚,她一把就扭着他的衣领,打了两个耳光。他挣不脱,就求饶了:
“不是我的主意,是大先生的吩咐!……”
“大先生,什么杂种大先生!我收拾了你,再去收拾他!”
蛇仔春用手来叉她的咽喉,被她一口咬住他右手的小指,他杀猪般的狂叫。有人怕闹出命案,上前拉开他们。蛇仔春被放开了,他又神气起来,转身威吓:
“我操你的娘,老子总要杀了你这个烂货!”
申晚嫂又追上去,旁边的人也气愤极了,大家叫喊着追上去:
“打!打这个龟孙子!”
一直追到小桥边,申晚嫂和梁树、彭桂、麦炳等几个农民,还想冲到石龙村去。年老的和稳重的农民,象梁七、四婆等人,拦住了他们:
“算了,算了!不要吃眼前亏,有账慢慢算!”
连拉带劝的将申晚嫂拥了回来,大家才跟着转头,一起去料理丧事。
从虎牙村到山下去,要赤脚涉过沙河,爬上对面河岸的斜坡,才到得了峡道。如果从石龙村下山去,那就另外有一条便道,一面沿着沙河,一面沿着山边,弯弯曲曲,一会高一会低,约莫一里多路长,然后也是穿过峡道下山。这是石龙村的地主们下山必经之路。这条便道虽然是又小又窄,但是在它穿过村边的一片果树林的时候,却是平坦的沙土路,而且也算宽阔,只是树木太密,地上落叶和蒿草太多,有些阴暗潮湿。
在贴近道路的几棵柚子树旁边,有一个大草堆,申晚嫂在草堆后边已经等候了整个下午。她早晨看到刘大鼻子下山,中午就藏在这儿。自从刘申死后,她好似完全变了个人,以前的坚决刚强,一下不见了,成日不说话,坐下来象一尊石像,老半天动也不动。四婆和金石二嫂她们逗她说话,她也不答理。大家不免为她担心了:
“晚嫂失魂落魄,你们可要留神,不要再搞掉一条人命啊!”
“丈夫死了,女儿卖了,可真惨!要一个人不变形,确实也难啊。”
她坐在草堆后面,思前想后:
“她们怕我寻死,我才不干哩!他搞得我家破人亡,我一定要报仇,打死这个老狗才能雪恨!寻死?我不是那种人!刘大鼻子希望我死,我偏要活下去!”
她从果树的缝隙中,远望山边的便道,不见有人影。
“太阳快到山背后了,还不见他回来,莫不是在县城过夜了?……回去吧,不!这个死老狗缩在窝里难得出来,前几天我去找他算账,他就是不见面,今儿不能放过他。不回去,等到天黑也要等,等到他回来;要末他死在山底下,如果回来,我可不会饶了他!……”
再过了一个时辰,申晚嫂等得太累,不觉打起瞌睡,靠在草堆上睡着了。她并没有睡得很熟,仍旧在想着怎样才能痛快地打击他,怎样才能报仇……
刘大鼻子和蛇仔春,四个轿夫,沿着便道走回来。他和蛇仔春走在前面,轿夫抬着空轿子跟着。刘大鼻子得意洋洋地说:
“这批木头真是卖了好价钱,达春,你准备一下,我要请一次客,不要怕花钱,要有个排场!”
“当然,我到高要去采办东西……”
“到广州去也行!哈哈!”
一阵笑声,惊醒了申晚嫂。他们已经走到她的跟前,她象猛虎一般地跳起来,冲到刘大鼻子身边,没头没脑地擂了他几拳,打在他的头上,脸上,胸口上,顿时头发披下来,嘴里流血了,胸口痛得直不起腰。刘大鼻子被打了一顿之后,才弄清是怎么回事。申晚嫂还扭着他打。他叫道:
“你们还不替我抓住她!”
蛇仔春拔出手枪,刘大鼻子怕他乱开枪打伤自己,连忙叫道: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蛇仔春又不敢靠近来,他挨过申晚嫂的打,右手小指上还包扎着纱布,心里害怕,他命令轿夫去抓她。那几个轿夫在一旁看着,又惊奇又高兴。
“抓住她!抓住她!”蛇仔春用枪逼着他们。
轿夫上前拉开时,刘大鼻子已经血流满面,弯着腰在喘气。
申晚嫂被他们押到乡公所,蛇仔春将她绑在门口的旗杆上。当时风声传了出去,有不少人围在那里看着。
“真够胆!连大鼻子也敢打!”有人悄悄议论。
“打得好!”
“她要吃苦喽!”
申晚嫂虽然被反绑着,她站得很直,头昂得很高,大眼睛放光,薄嘴唇抿得紧紧的,显得又愤怒又高兴。
冯氏听说刘大鼻子被打了,一路跑着,一路嚷着:
“不得了啦,造反啦!”
她经过申晚嫂面前,想上去打她一下,骂她两句,申晚嫂威严地瞪了她一眼,她停也不停地又跑进乡公所去。
“哎哟,德厚啊!你,你……”
“你吵什么?大惊小怪!”
刘德厚已经抹掉了血迹,重新梳了头发,坐在他的乡长室中。他的脸色白里透青,眼睛阴险地䀹着,隐约看出紫红色的大鼻子在掀动。蛇仔春坐在另一角落,瞅着他,不说话。
冯氏碰了一鼻子灰,弄不清他为什么动火。她瞧瞧蛇仔春,他轻轻点头,暗示给她:刘大鼻子正在发脾气。
“你伤得重不重?”冯氏殷勤地问他。
“伤,什么伤?”
她吃惊地退后一步,以为他一定是恨申晚嫂,所以火气那样大。她讨好地说:
“气什么呢?她不是在你手掌心里,……”
“我说,杀了她倒干净……”蛇仔春插嘴。
“你们懂个屁!”
刘大鼻子吼起来。他被申晚嫂突然的袭击,弄得很心烦。他一开始的念头,是杀了她。这是毫不费力的事。再一想,如果杀了她,不就是承认了她是打过自己,她是反抗过自己,这是很失威风的。一个女人敢起来反抗,以后自己还能说得嘴响吗?不杀,一定要想个妥善的办法,既要挽回自己的面子,又要整得她很厉害才行。
冯氏眼看讨好反碰了钉子,生气也是撒娇地说:
“为了这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也值得……”
“对了!”
刘大鼻子刷一下站起来。
“对了!她是疯子!你们出去对人讲,她是疯子。我刘大爷不会跟一个妇道人家,跟一个疯子计较……”
“你说放掉她?”
“当然放掉她!你慢点奇怪。我要杀掉她,容易过杀一只鸡,不过杀掉她就显得做事不漂亮。你还记得你在虎牙村动了公愤吗?那就太蠢了。放掉她,我要她认得我刘德厚,要她活活的饿死。阿春,你通知大家,以后谁也不许雇她做工,批田给她自然更不行,我看她有什么活路!”
申晚嫂被绑了一天一夜,背上一个“疯子”的名声,放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