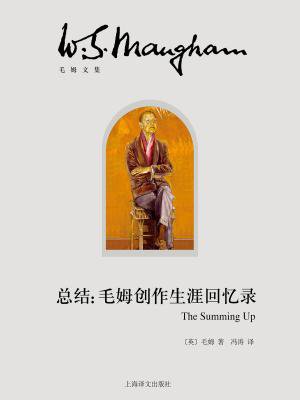三
我这辈子有过不少感兴趣的东西,在本书中我将尝试着把有关这些东西的想法整理清楚。可是我所得出的这些结论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一艘沉船的残骸那样,在我的脑海中漂浮不定。在我看来,如果我能以某种秩序将它们确定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更加明确地看清它们的真面目,从而也就有可能赋予它们一种首尾一致的连贯性。我早有此意,而且不止一次,比如说在开始一段将持续几个月的旅行时就下定决心付诸实施。这种时机似乎是很理想的。但总是发现我被这么多繁杂的印象所困扰,我看到这么多新奇的事物,见到这么多激发了我的想象的人物,结果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回忆往事了。瞬时的经验是如此鲜活生动,我都没办法调节自己的心绪去内省和反思了。
另一个使我无法下笔的原因是,我厌恶自说自话,以自己的身份记下自己的想法。尽管我已经站在这个立场上以这种观点写了很多东西,但我那是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来写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可以将自己视作小说中的一个人物。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使我在通过我塑造的人物开口说话时感觉更加自在。相比较而言,决定他们的所思所想反倒比确定自己的想法更为容易。前者对我来说一直都是种乐事,而后者却是一桩我宁肯推脱了事的苦差。不过现在我已经无可推脱了。年轻的时候,展现在一个人眼前的时光是如此悠长,你简直很难意识到总有一天它们也将成为过往,即便是人到中年,对于人生仍旧还有彼时那些平常的企望,还是很容易为那些本该去做却不想去做的事情找到拖延的借口;但终于还是到了必须认真考虑死亡的时候了。同时代的人物相继开始凋零。我们知道人必有一死(苏格拉底是个人;所以——如此这般的道理),但一直到我们被迫认识到在世间万物日常进展的过程中,我们的终点距离我们已经不再遥远之前,这对我们来说都不过是个逻辑上的前提而已。偶尔瞥一眼《泰晤士报》的讣告栏,你会认识到人一上了六十岁,那健康状况就颇为堪忧了;长久以来我就在想,如果我在写这本书以前就撒手而去的话我真是会死不瞑目的,所以我想还是马上动手的好。等我把它写完以后,我就能内心平静地去面对未来了,因为我已经圆满完成了我这一生的工作。我不能再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写这本书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因为如果时至今日我还没有下定决心去做这件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事的话,那么将来再去做的可能性就更是微乎其微了。我很高兴,终于把已经在我意识的各个层面随波逐流了这么久的所有这些想法都收拢到了一起。等把它们全都写下来以后,我跟它们的纠葛终于算是银货两讫、功德圆满,我也就能放下包袱,自由自在地去想些别的事情了。因为我还希望这并非我写的最后一本书。一个人不会在他立完遗嘱以后马上就死掉的;立下遗嘱是为了以防万一。把自己的各种事务安排妥帖是一种非常好的准备工作,这样就可以没有任何牵挂地安度自己的余生了。等我写完这本书以后,我也就知道我确切的立身之处了。到了那时,我也就能够从容地去选择如何去度过我一息尚存的岁月了。 [1]
[1] 毛姆一九三八年在六十四岁上写完《总结》( The Summing Up ),之后不仅又活了二十七年,而且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刀锋》( The Razor's Edge )就出版于他七十岁高龄时。此外的作品尚有长篇小说《情迷佛罗伦萨》( Up at the Villa ,1941)、《过去和现在》( Then and Now ,1946)、《卡塔丽娜》( Catalina ,1948),短篇小说集《换汤不换药》( The Mixture as Before ,1940)、《环境的产物》( Creatures of Circumstance ,1948),以及文学评论集《巨匠与杰作》( Ten Novels and Their Authors ,195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