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基层社会治理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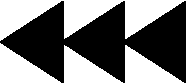
一、民主协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原有的提法上,又新增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两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民主协商,重在协商,难在“真协商”。民主协商的本质是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协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充分体现了尊重群众、了解群众和依靠群众。凡是民主协商的结果是基层群众的自我决定,自己说到就必然能够做到,这是基层民主协商的最大魅力。

浙江是基层民主协商的先发地,早在 20 世纪末就涌现出了以温岭“民主恳谈”、武义村务监督制度等为代表的民主协商的典型经验。新时期以来,又探索出以海宁市“信访评议团”、诸暨市陈家村“村规民约”、枫源村“三上三下”民主议事机制及诸暨市各级“乡贤参事会”等为代表的城乡民主协商的新途径、新经验,涉及城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诸多领域。这些创新和探索把民主协商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挖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协商治理的有效机制,丰富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创新和实践。
 北京房山区南广阳城村是一个把基层民主协商做到极致却又非常低调的农转居小区,通过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让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全面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北京房山区南广阳城村是一个把基层民主协商做到极致却又非常低调的农转居小区,通过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让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全面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二、社区网格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社区网格化管理是一种以网格单位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精细化管理为目标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充分体现了社区建设的整体观和系统性思维,改变了过去传统、被动、定性和分散的管理,开始迈入现代、主动、定量、系统和信息化治理的新时代。
 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将网格化治理与社区党建密切结合,建立起以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为主体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和在党总支领导下的社区治理体系,为有效解决基层党组织“力量不凝聚、阵地不固定、作用不明显”等问题提供了新思路,能够为居民提供更方便的服务。
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将网格化治理与社区党建密切结合,建立起以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为主体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和在党总支领导下的社区治理体系,为有效解决基层党组织“力量不凝聚、阵地不固定、作用不明显”等问题提供了新思路,能够为居民提供更方便的服务。
“红色网格”是浙江省金华市近年来推进党组织网格化管理、落实党员网格责任制以及提高“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水平的一种实践探索。具体而言就是将街道分为若干网格,把支部建在网格上,由支部书记任网格长、驻村(社区)干部担任网格指导员,支委干部任专职网格员、党员任网格员,按照就亲、就近、就便原则,每名红色网格员联系 5—10 户群众,常态化开展基层的民生服务、矛盾调处、隐患排查等工作,形成以“小网格推动大党建、带动大治理”的工作格局。同时,在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党建带群建以及建立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区域党建联盟等,引导各类基层自治组织、群团、驻社区单位等在网格中发挥作用,确保群众服务在网格、问题发现在网格、责任落实在网格、矛盾化解在网格。
 陕西西安秦汉新城大力推行“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设置了“新城党委+党(工)委+党支部+党员中心户(党员示范岗)+有能力的党员”五级网格,从负责总体部署协调的一级网格长到负责具体细节执行的五级网格长,均明确责任、落实到人,确保社区基层党建工作无缝隙、无死角、无漏洞,在服务大局中更有力,在服务群众中更有效。
陕西西安秦汉新城大力推行“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设置了“新城党委+党(工)委+党支部+党员中心户(党员示范岗)+有能力的党员”五级网格,从负责总体部署协调的一级网格长到负责具体细节执行的五级网格长,均明确责任、落实到人,确保社区基层党建工作无缝隙、无死角、无漏洞,在服务大局中更有力,在服务群众中更有效。
三、智慧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可见,科技支撑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前景广阔,是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和 5G等前沿信息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能够促使新时代社会治理信息平台的优化、执行力的增强、治理效能的提升以及安全稳定的升级,最终实现通过科技支撑把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

实践中,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积极探索信息化互联网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五微共享社区”党群服务平台,其中,“微平台”开辟了党组织网上工作的“新阵地”,“微心愿”开启了居民表达诉求的“快车道”,“微实事”搭建了实施惠民工程的“投票箱”,“微行动”成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的“路线图”,“微星光”成为汇集先进模范的“光荣榜”。现代互联网技术在基层党建的运用,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技支撑,实现了党建智能化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
 重庆迈瑞城投公司创造性地构建了集学习管理、考核管理、发展党员等为一体的智慧党建系统,深度开发官方微信公众号,基本形成了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党建管理新模式,可实现对各项信息数据的融合及提取,对党建工作全过程进行智能统计分析,使智慧党建系统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平台、与时俱进的党员教育平台、联系服务党员的互动平台,实现基层党建引领、服务、分析、监督“四位一体”。
重庆迈瑞城投公司创造性地构建了集学习管理、考核管理、发展党员等为一体的智慧党建系统,深度开发官方微信公众号,基本形成了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党建管理新模式,可实现对各项信息数据的融合及提取,对党建工作全过程进行智能统计分析,使智慧党建系统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平台、与时俱进的党员教育平台、联系服务党员的互动平台,实现基层党建引领、服务、分析、监督“四位一体”。
四、社会组织
在当前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党与社会各类群体保持着紧密联系,引导和组织动员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大势所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责权、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重申,要“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就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给社会组织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也为新时期社会治理注入了新的力量和形式。
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自 2007 年以来,整合区域内社会调处类社会组织资源,创设“社会维稳专业联盟”,通过提升专业服务和打造专业团队,聚焦化解社会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发挥了“社会协同”的重要作用,成为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重要补充。其中静安区劳动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帮助用人单位健全劳动制度,法律工作者协会帮助接待法律咨询和信访,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通过电话、网络、现场等方式提供心理咨询并接待来信来访,少数民族联合会帮助化解了少数民族来沪人员的房屋租赁等多起矛盾纠纷。
 此外,四川成都同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武侯区凉水井街社区营造的凉水井文化项目也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范例。同行社工根据“饮水思源,奉献之泉”这一主题,广泛调动凉水井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营造。其间,老人给年轻人讲凉水井的故事,年轻人用钢笔画出凉水井老街景,就连外国留学生也对凉水井的故事产生了兴趣,纷纷前来帮忙。同行社工通过这一行为的倡导,让居民以自身的集体行动,挖掘社区文化,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氛围,让居民对社区有了更好的认同;同时,还增强了居民的自治意识,提升了居民社区治理能力。
此外,四川成都同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武侯区凉水井街社区营造的凉水井文化项目也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范例。同行社工根据“饮水思源,奉献之泉”这一主题,广泛调动凉水井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营造。其间,老人给年轻人讲凉水井的故事,年轻人用钢笔画出凉水井老街景,就连外国留学生也对凉水井的故事产生了兴趣,纷纷前来帮忙。同行社工通过这一行为的倡导,让居民以自身的集体行动,挖掘社区文化,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氛围,让居民对社区有了更好的认同;同时,还增强了居民的自治意识,提升了居民社区治理能力。
五、三治融合
三治融合即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治理模式,最初主要着眼于解决社会转型期的基层维稳难题,由于长期实践中三治融合的良好治理效应以及基层社会事务和矛盾的日益复杂化,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开始在基层社会治理各领域中广泛运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并强调“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重申,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推进三治融合治理,首先是要调动居(村)民自治的积极性。依法制定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组织公职人员进社区认领楼道长,成立红色乡贤“乡村智囊团”,围绕公共事务服务、供需对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人才联动,创设服务项目,丰富群众自治形式。其次是要用好本土法治资源,全面依法治理。推动法律服务平台建设,实现镇街公共法律服务站、村社公共法律服务点全覆盖,法律服务团队驻点服务、入户服务、按需服务,以案释法,以身边人说身边事、身边人教育身边人,感受法治正义,领悟法治精神,增强法治意识,让百姓自觉遵法、学法、守法、护法、用法。最后是要以德教化,广泛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传统乡贤文化、儒家文化、孝文化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完善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关爱帮扶和礼遇机制,褒扬先进、惩戒落后,引导广大居(村)民从每个小家做起,重家教、立家规、传家训、正家风,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

浙江桐乡是三治融合的示范地、引领地,突出党建引领,推动政府、社会组织、群众等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创新“一约两会三团”机制,充分体现了自治法治德治综合运用、协同发力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一约”即村规民约,让村民参与制定和监督,以“村言村语”约定行为规范、传播文明新风;“两会”即百姓议事会和参事会,通过专题会议、个别访谈等多种形式,解决和协调村里的相关事务,实现农村事务的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三团”即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和道德评判团,以志愿服务、法律服务、道德评判为抓手,将定期坐诊、按需出诊、上门问诊相结合,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