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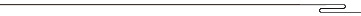
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他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少年时代就随着已成为华侨农场主的哥哥长期生活在国外。十二岁以后,在夏威夷群岛和香港,系统地受过十多年近代教育。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中国社会中还不曾有过。这使他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政治代表。
从夏威夷归国时,他已不是出国前那个农民的孩子了,也不是中国旧式的士大夫,而是一个新式的近代知识分子。在他重新接触到清朝封建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时,格外敏锐地感到这个政府的腐败贪婪和中国人民所受的残酷压迫是无法忍受的。他到香港读书时,又正值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失败,给了他极大刺激,深深感到这个政府的统治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后来,他进入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学习,课余常同陈少白、尢列、杨鹤龄一起高谈革命,自称“清廷之四大寇”。
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常常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包含着种种矛盾和冲突,需要经过某些迂回和曲折。一种新的社会思想的产生,尤其是这样。尽管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开始产生,但他们毕竟只是在谈论革命,并没有实际从事革命。他思想上还有一些摇摆,总还想尝试一下:推动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条路是不是还有可能行得通。
一八九三年,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取得外科医生行医执照,在澳门镜湖医院当医生,又开设药局。第二年,回广州行医,并开设东西药局。当时西医在中国内地极少,因此他在社会上很有名声,上层社会中有不少人请他治病。就在这时,发生了他上书李鸿章的事情。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在一八九四年六月,正好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夜。他为这次上书做了充分的准备,放下医生和药局的工作,回到家乡闭门十多天把信稿写成,到上海找人介绍,再赶到天津去见李鸿章。他在这次上书里提出:应当在中国解除对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束缚,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择人才的制度。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说:“此四事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并且批评李鸿章和洋务运动:“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这些,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主张,也是很温和的主张。
这些,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主张,也是很温和的主张。
但是,李鸿章对孙中山抱着满腔热情的上书,却极为冷淡,没有见他。这给孙中山很大的打击,使他经过尝试,破除了原来对清政府还抱有的一点幻想,明白像这样昏庸腐败的政府要进行根本改革是不可能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又使他无法再等待下去。温和的道路走不通,就使他下定决心开始革命活动。他的好友陈少白描述了这段过程:“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在遭到李鸿章拒绝后,孙中山“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

暴力革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当反动统治势力表面上还很强大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要下决心抛弃自己已取得的社会地位,甘冒杀头破家的危险,领头起来革命,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有一个严肃思考和内心冲突的过程。孙中山的青年时代,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孙中山建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是兴中会。它最早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然后在香港建立总会。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先后入会的有一百二十六人,大多是有爱国心的华侨资产阶级。它的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而且影响深远的口号,就是这时第一次提出来的。孙中山起草的会章大声疾呼地指出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

兴中会名称中的“兴中”两个字也表明了这个意思。虽然孙中山这时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他领导的革命活动,具有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是没有疑问的。
由于檀香山兴中会的成员大多由较富裕的华侨构成,身家顾虑较多,他们有爱国心,同情革命,但成立后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实际行动。第二年年初,孙中山来到香港,同杨衢云等的辅仁文社联合,成立兴中会总会。它的成员和檀香山时不同,大多是有着近代思想的新式知识分子和有反满思想的会党分子,政治态度比较激进,开始形成第一个能够采取革命实际行动的战斗核心。
孙中山的思想也有新的发展。据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这年春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写到孙中山曾向他表示:要“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
 可见孙中山至少在这时已决心为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而奋斗。
可见孙中山至少在这时已决心为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而奋斗。
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立刻筹划这年十月二十六日(农历重阳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从他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并没有像世界近代许多革命党那样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宣传酝酿和组织准备,而是很快就把武装起义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来。这是他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个重要优点。
为什么会这样?第一,当时中国面对的民族危机特别严重,国家的生死存亡已悬于一线,这使当时的革命者产生一种异常急迫的心情。有如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所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
 第二,在清朝统治下,国内民众没有一点民主权利,任何温和的办法都不可能得到结果,孙中山自己上书的失败就是明证。这就迫使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剩下拿起武器一条路可走。第三,中国是一个富有人民革命传统的国家。有这样的传统和没有这样的传统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时间相隔只有三十多年而在两广地区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对孙中山有着不小的影响。第四,甲午战争失败后,人心愤激,也使革命者觉得有机可乘。
第二,在清朝统治下,国内民众没有一点民主权利,任何温和的办法都不可能得到结果,孙中山自己上书的失败就是明证。这就迫使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剩下拿起武器一条路可走。第三,中国是一个富有人民革命传统的国家。有这样的传统和没有这样的传统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时间相隔只有三十多年而在两广地区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对孙中山有着不小的影响。第四,甲午战争失败后,人心愤激,也使革命者觉得有机可乘。
广州起义因为内部步调不一致,贻误了时机,又有人告密,没有发动起来就失败了。孙中山等被迫流亡国外。但它是一个重要起点。到二十世纪初,当人们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和对清政府的愤怒越来越强烈时,孙中山在十来年前已开始革命行动的先驱者形象便博得越来越多人的敬重,日益在人们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象征。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经日本、美国来到英国。抵英国后不久,他被清朝公使馆诱骗囚禁十三天,准备秘密押送回国,经他老师康德黎多方营救才获释。这件事轰动一时,使他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革命家。
辛亥革命时期的先进中国人是向西方学习的。但西方国家内部的种种社会矛盾已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之间的急剧分化,社会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引起孙中山的极大关注。那时的英国正处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居于首屈一指的领先地位。孙中山在这里认真考察英国社会情况,广泛阅读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他说:“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他受到美国学者亨利·乔治的著作《进步与贫困》的影响很大。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它点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巨大的物质进步,一方面却积累起令人颤栗的贫困;进步与贫困并存,而且伴随着一起发展。在孙中山直接接触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现实以前,这些问题在他脑子里并不存在。尽管亨利·乔治没能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途径。但是,当中国的先进分子正醉心于学习西方、对西方的种种都顶礼膜拜的时候,孙中山已敏锐地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社会问题,这在一百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孙中山已来到日本,在一九〇〇年十月六日发动了广东惠州起义。这次起义的依靠力量仍是会党分子,坚持了一个月,最后仍失败了。但他的处境和先前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孙中山写道:
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除了八国联军之役后人们痛感国家命运的危急、对清政府越来越不抱希望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前面说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但那种新的社会力量在国内毕竟太少,几乎微不足道;进入二十世纪后,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有了长足的进步。拿新式知识分子来说,最集中的地方,一个是留日学生中,一个是上海。革命思潮也就在这两个地方首先高涨起来。
留日学生中很早就有一些激进分子,在一九〇一年创办过有革命色彩的刊物《国民报》,但他们的人数还很少。一九〇二年起,留日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各种宣传新思想的留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湖南游学译编》等。这些刊物的主要内容是痛陈严重的民族危机,介绍西方近代的各种学说,并从各方面探讨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落后和遭受侵略的原因,力求找出救亡图存的途径和方法。但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仍比较温和,没有多少革命色彩,主要是: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的国家;发展教育,学习并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进行“学战”;主张以省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并从各个方面提出改革社会、救亡图存的办法。这反映出当时大多数留日学生的政治态度和认识水平。
留日学生中的思想转折点是一九〇三年春夏之交的拒俄事件。那时,沙俄侵占东北大部分地区已两年多,一直不肯撤兵,还提出七项无理要求。由于日俄之间的矛盾,四月二十八日,东京各报详细报道了它的内容,《时事新闻》并出版号外,刊登俄国代理公使对记者的谈话,内有“今宁断然取之,归入俄国之版图”等语。
 这个消息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强烈震动。他们纷纷集会,痛哭流涕地要求拒俄。但这个活动最初并不带有革命色彩,只是要求组织义勇队,在清政府指挥下开赴前线抗敌。他们还推定两个特派员回国联络。但清政府对学生爱国行动的对策却是坚决镇压。六月五日,上海《苏报》揭露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电:“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又载清政府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
这个消息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强烈震动。他们纷纷集会,痛哭流涕地要求拒俄。但这个活动最初并不带有革命色彩,只是要求组织义勇队,在清政府指挥下开赴前线抗敌。他们还推定两个特派员回国联络。但清政府对学生爱国行动的对策却是坚决镇压。六月五日,上海《苏报》揭露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电:“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又载清政府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

这件事,对留日学生的刺激太大了。一大批原来并没有“革命本心”的留日学生,在清政府如此倒行逆施的驱迫下,走上革命的道路。七月份出版的《江苏》第四期上发表的《革命其可免乎》的文章,很可以代表当时许多人的看法:
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借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而端方,而蔡钧,必欲合并而混同之,务极倾陷以为快。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忠于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转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是故余乃抚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于我留学生,并以谂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曰:呜呼!革命其可免乎?

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这年下半年起,留日学生刊物的政治态度倏然一变,大批人走上革命道路。拒俄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黄兴、龚宝铨等分别回到湖南和上海,成为第二年成立的华兴会和光复会的发起人,成为国内两湖地区和江浙地区革命活动迅速兴起的重要火种。
正当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开始步入高潮的同时,革命思潮在国内也迅速高涨起来。它的起点,是刚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邹容(这年十八岁)所写的《革命军》一书五月间在上海出版。这本书以通俗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鼓吹革命,宣传共和国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打开这本书,劈头就可以读到这样热情洋溢的话:
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

由于这本书充满着炽热的革命感情,笔调又通俗明快、犀利有力,使人读了就像触到电流一样,无法平静下来。它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销售总数当在一百万册以上。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回忆道:“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如果说邹容的《革命军》着重从正面鼓吹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那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从批驳康有为反对革命言论的论战中,阐述了革命的巨大意义。康有为以人民智力道德低下、不配革命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章太炎则用具体历史事实来论证:“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康有为以革命会引起社会紊乱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章太炎指出,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康有为把光绪皇帝说成尧舜以来所未有的“圣明之主”,鼓吹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章太炎则竭力摧毁这种虚构的神话。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上的名字是臣民万万讲不得的。章太炎偏偏选准这个目标,直斥光绪的名字。一声“载湉小丑”,震动远近,顽固派为之暴跳如雷,中间派为之目瞪口呆,而革命派却为之扬眉吐气。
 这种震撼人心的巨大影响,我们今天已不容易完全体会到了。
这种震撼人心的巨大影响,我们今天已不容易完全体会到了。
六七月间,上海租界当局应清政府的要求,逮捕了邹容、章太炎等,制造了“《苏报》案”,并进行公开审讯。这件事轰动一时,万众瞩目。结果,更扩大了它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布。《江苏》的时评说得很清楚:
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脑髓中。

拒俄事件和《苏报》案后,留日学生和上海等地区的政治空气和以前相比判然不同。留日学生中,革命已到处昌言无忌,如何进行反清革命已成为留日言论界的中心话题。在上海,《国民日日报》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和种种奴隶道德,各种新学书籍和革命书籍继续流行。众多的爱国知识分子以空前的规模,冲破旧的精神枷锁,急速地倾向革命。他们中一些最积极的分子,下一步自然要求组织起来,投身到革命的实际活动中去。
一九〇四年的历史特点是,内地的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它们中最重要的有: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在湖南建立的华兴会,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的科学补习所,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柏文蔚、陈独秀等在芜湖成立的岳王会,杨庶堪等在四川成立的公强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中国同盟会的创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