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一般社会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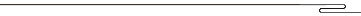
历史的现象常常充满矛盾: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在表面上的一片胜利声中到来的。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像猛烈倾泻的急风暴雨,骤然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政治格局。突然的变化使人感到头晕目眩,对眼前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难以立刻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它行将带来的无数新问题既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更缺乏应对的经验。
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时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由于自身力量太弱,没有料想到推倒清政府和君主专制制度会那么快到来。这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随后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也将在短期内同样顺利地实现。这种普遍的乐观和幻想,使人们倾向于强调维持现状,认为需要思考的只是如何在民主共和制度的新格局下建设这个国家,对旧社会势力的斗争已不那么重要,甚至因害怕引起破裂而处处趋向妥协。
还要提到,许多革命党人在民国成立后社会地位起了变化,纷纷跻身上层社会之列,更使他们中不少人容易醉心于维持现状。革命的共同目标已逐渐淡化,各人似乎已可各奔前程,更加自由地追逐自身的利益和发展,继续改善自身的地位。原来就相当涣散的革命团体,进一步失去凝聚力,变得更加涣散,甚至出现明显的分化。
在一般国民中,妥协的心理更为普遍。胡汉民作过一个对比:“当武昌倡义以后,举国响应不为不快。各地不但党人领导着运动,连国民也跟着运动,大家都觉得满清非推翻不可了;就此群策群力,一鼓作气,把他很快的推翻掉。”但经过破坏以后,临到建设,国民心理就显出三大弱点来:
第一个心理上的弱点是苟且。大家以为大乱过去了,应该赶紧休养生息,不必再闹了。革命党员毕竟是含有暴烈性的朋友,现在用不着他们了,同他们疏远些,另外接近稳健派的人物吧!……(有些革命党员)跑了一程,已出了一身汗,马上就要歇住脚来休息,也不管时机容许不容许停顿,而真正目的地相去尚有多远,就此躺下来不再动,任你催促他也是无益了。
第二个心理上的弱点是侥幸。以为过去已有的牺牲,或者已经够了,够达所求的目的,不必再多奋斗了。大家总想以廉价来买得贵物,实际上有无把握是不管的,只望其侥幸而中罢了。
第三个心理上的弱点是倚赖。凡事托人去办好了,自己一概不管。从上面两个弱点中,他们认为满意的办法,是“维持现状”;认为满意的人才,是“非袁莫属”……这两句话原来是一呼一应的,作用很大,当时竟有人大为宣传,用以压倒一切。

妥协和厌乱的心理构成压倒一切的浓重氛围。这同革命前夜的社会心理形成明显的反差,在无形中起着左右局势的作用。
孙中山在临时政府结束后,对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个党深感失望,对三个月来置身政治旋涡中心而又难有作为的日子感到痛苦和厌倦。章太炎曾嘲笑他那时的处境说:“政府号令,不出百里,孙公日骑马上清凉山耳。”
 对他不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国家内外局势的复杂情况,孙中山并不是毫无觉察,但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一时难有所作为。他在给宋教仁的一封信中写道:
对他不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国家内外局势的复杂情况,孙中山并不是毫无觉察,但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一时难有所作为。他在给宋教仁的一封信中写道:
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

孙中山自然知道政治的重要性。但他这时认为:现实政治有如一团乱麻,一时谁也难以措手足。如果从这里着手,只会越弄越乱。倒不如自己暂时把政治问题放一放,先集中力量发展实业,特别是要专心致志于铁路建筑,等到“民生充裕,国势不摇”了,回过头来解决政治问题也许好办得多。他认为这才是“从根本下手”的办法。
他的愿望是良好的。发展实业,对贫穷落后的中国确实太需要了。把兴建铁路看作发展实业的先行条件,也是有道理的。可是,他期望“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在那时中国的国情下,当国家政权仍掌握在旧社会势力手中时,结果只能事与愿违。这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再出现的沉重教训。孙中山在十年内建设二十万里铁路的宏伟设想最后完全化为泡影,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当时在同盟会中,在社会上,谈论得最热闹的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主张,把它看作建设新国家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最理想设计。
宋教仁在清末流亡日本后,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财政等制度相当熟悉,翻译过《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书籍,而对国内的实际革命活动参加得比较少。“当是时,先生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
 因此,他的书本知识要比许多人多,实际社会经验却比较少。
因此,他的书本知识要比许多人多,实际社会经验却比较少。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觉得他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他特别注重西方国家民主的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只要把这一套搬到中国来,就是抓住了事情的根本,中国的面貌就会发生大变化。他到武昌后,起草了《鄂省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担任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不少法规章则。他到处滔滔不绝地发表这方面的议论,很得到一些人的赞赏。一个同他很接近的人扼要地叙述宋教仁当时的见解,那就是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
宋教仁的主张最坚决的,就是责任内阁制。他认为要建设进步的国家,必须有健全的政府,有权而后尽其能,有能而后尽其责,是之谓“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这样的内阁,必须有强大的政党,又有人才,又在国会中取得大多数的议席,才可以建立起来,巩固起来。

宋教仁真相信:只要组成强大的政党,同其他政党竞争,通过选举赢得胜利,夺取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就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组成责任内阁,实现他们的全部政治主张。因此,他全力以赴奔走的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第一,组织一个大党;第二,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这两点是互相关联的:组织大党的着眼点主要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多得席位;而在议会中夺取多数席位又是为了实现政党的政治主张。但步骤上又有先后之分。
他首先着手的是组织一个大党。在他接替汪精卫担任中国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掌握党务实权后,不顾蔡元培等反对,立刻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联络,在八月二十五日合并成立国民党,出任代理理事长。他到处拉人入党,“简直是拿着本子乱填,谁要进党都可以登记,大批因势趋利的投机分子都混了进去”
 。这一来,不仅使政党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党的性质,只满足于党在议会中的活动,大大降低了它的革命性。胡汉民对宋教仁这种做法一直很不满意,批评道:
。这一来,不仅使政党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党的性质,只满足于党在议会中的活动,大大降低了它的革命性。胡汉民对宋教仁这种做法一直很不满意,批评道:
他以为我们那时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只要到国会中去做那政治活动者就是。他为扩充国会中的势力起见,要将当时五个政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兄弟对于他这种主张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把本党的革命性销蚀大半了。……而宋先生那时不独忽略了这一个要点,而且想以选举运动、议会运动替代了革命运动,那如何行呢?

国民党这个大党一成立,宋教仁立刻把工作重点转到国会竞选活动上,力图通过选举在国会取得多数席位。他奔走湘、鄂、苏、沪等地,为国民党竞选。一九一三年二月一日,他在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大会上说: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选举之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他在不久所写的另一篇文章里充满自信地说:只要有“强有力之政党主持于上,决定国是”,又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的分划有条理地加以确定,“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

重读宋教仁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豪言壮语,只能慨叹它实在是过于天真的书生之见。宋教仁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是真诚的,但他满脑子都是书本上看来的学理,对中国的实际国情太缺乏了解了。在想象中似乎相当完美的政治设计,一进入实际生活就走了样,收到的并不是设计者预期的结果,甚至适得其反。纸上的空文并不会自然地转化成民众的实际权利。当宋教仁兴奋地写下五年如何、十年如何那段话时,谁能想到,离他被袁世凯指使人暗杀惨死只剩下十天了。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不能一蹴而就。如果袁世凯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不但没有被触动,而且还掌握着一切实际权力的时候,如果不经过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单靠搬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是太可笑了吗?名重一时的宋教仁,其实仍是一个不懂世事的书生,这真是可叹的悲剧!
处在旁观地位的著名记者黄远庸看得很明白:“其新者以为法律万能,但能全本抄录外国之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其旧派则任有何种法律,然我曹自有我曹之窟穴,自有我曹之本领及伎俩,一切国法,弁髦视之。此二派水火之不能相容。”
 这是对“法律万能”论的辛辣嘲讽。他所说的“新者”就是指宋教仁这些人,所说的“旧派”就是指袁世凯为首的旧社会势力。事实确实是这样:对袁世凯说来,只要实力在手,“任有何种法律”,到时候都可“弁髦视之”,使它成为一张废纸。对中国社会实际有更多了解的黄远庸比宋教仁看得清楚:以为“但能全本抄录外国之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这只是天真的虚幻梦想。
这是对“法律万能”论的辛辣嘲讽。他所说的“新者”就是指宋教仁这些人,所说的“旧派”就是指袁世凯为首的旧社会势力。事实确实是这样:对袁世凯说来,只要实力在手,“任有何种法律”,到时候都可“弁髦视之”,使它成为一张废纸。对中国社会实际有更多了解的黄远庸比宋教仁看得清楚:以为“但能全本抄录外国之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这只是天真的虚幻梦想。
在政党活动中,仅次于国民党的政治力量是原清末的立宪派。它们先成立了共和党和统一党(也有一些原革命党人士参加),后来又成立民主党,到国会产生后合并成为进步党。它的精神领袖是梁启超。
这些人仍可说处于中间状态,但当时的政治态度是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清朝被推翻后,梁启超原来鼓吹的“虚君共和”已没有可能实现。袁世凯一当上临时大总统,还在海外的梁启超立刻写信给袁世凯,建议他以共和国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并主动表示对他支持,说:
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今国中出没于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阘冗佥壬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袁世凯在复信中热情地写道:“政党一层,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四月间,梁启超又写了一本《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主张新建立的共和国的立国大方针,首先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行“保育政策”;不能效法美国,由“立法部掣肘行政部”,限制中央集权;不可由地方自选都督,以免造成藩镇之祸。这本书先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印刷两万册问世,后又由《庸言报》连载,在社会上产生不小的影响。
他所以提出这些主张,仍然由于认为中国国民程度不够,必须先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对民众实行“保育政策”,否则就会“步武凌乱,节奏脱落”;也由于认为中国现在国势危急,必须有一批“富于经验”的“旧官僚派”组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不至于陷入混乱,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同他原先的“开明专制”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不仅梁启超如此。当时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是厌乱思定,认为民国成立,革命时期已成过去,现在需要的是强有力的、具有治国经验和能力的人出来担当这个任务,袁世凯似乎就是这种强有力的人。同梁启超比较接近而没有参加什么政党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写道:“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他也讲道:“大抵今日之崇拜袁公者,开口动云‘老袁了不得’,或曰‘老袁必有主意’。”至于那些旧官僚派自然更对袁抱着依赖的心理。一时,袁世凯仿佛成了可以维持安定的力量所在。所谓“非袁莫属”,就由此而来。但黄远庸对袁世凯的认识比梁启超等清醒。他在讲了袁世凯有五条长处后,接着写道:“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当时能有这样清醒见地并公开发表出来的人实在不多。
当时能有这样清醒见地并公开发表出来的人实在不多。
梁启超等所以支持袁世凯,是期望能得到这个强有力人物的信任,从而得以逐步实行他们的政治主张;却没有想到袁世凯对他们也不过是暂时利用,一旦把劲敌原革命党人打败了,很快就把梁启超等也一脚踢开。这实在是梁启超等始料之所不及,也成为对他们原来所抱幻想的无情嘲弄。
当时弥漫社会的那种妥协心理,自然便于城府很深的袁世凯得以一步一步地独揽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