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论》作者“推倒”“古典文学”之考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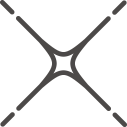
考察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讨论“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历史意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都应该是重要的文献。其中《文学革命论》尤以态度较为激进而引人注意。然而在文章基本内容的理解方面,虽然八十多年已经过去,学界对之却未必有确切的定见,甚至还可能存在某些严重的误读。例如,对《文学革命论》作者所谓“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这一说法,长期以来就当作陈独秀否定中国古代文学——封建时代文学来理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成为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彻底性的标志之一(虽然没有忘记指出它的“偏激”)。到了80年代,这又成为指责“五四”带来了“文化断裂”的根据。两种一正一反几乎截然相反的评价,都建立在相同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却很少有人对这一理解本身是否准确、是否科学、是否符合陈独秀的原意提出怀疑。
陈独秀确实说过要“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他是在对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声疾呼表示支持时说这番话的: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里,陈独秀所谓的“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究竟是什么意思?按照20世纪后半期人们的通常理解,“古典文学”一词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指过去年代的经典性作品,二是泛指古代文学。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版为例,对“古典文学”的释义就是:“古代优秀的典范的文学作品。也泛指古代的文学作品。”如果采用这两项解释中的任何一项,毫无疑问,都可以认定陈独秀对待中国古代文学的态度是绝对错误的。中国古代文学有着辉煌的成就,创造了许多独特的堪称经典的作品,陈独秀怎么忽发奇想就叫喊“推倒”呢?这个陈独秀莫非有点精神病?要不然,实在太粗暴、太野蛮、太愚昧无知了,“五四”的历史实在太可笑了!但是,且慢!当我们将上述理解安放进《文学革命论》文章的具体语境中,就会发现,上面这类理解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有两重明显的障碍跨不过去。
第一,陈独秀所谓“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要“推倒”的和要“建设”的两项目标本来都是反义而对称的。像“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对应的方面就是“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像“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对应的方面就是“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只有中间这一条“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同“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从词性到意义上完全不能对应。“写实文学”体现的是一种创作方法或创作态度,古代、现代都可能有;而“古典文学”是文学史上时间阶段的划分,也可能意味着经过时间考验的一部分比较优秀的作品。这两个概念并不能构成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古典文学”中,像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丰折臂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本来就是“写实文学”或基本上是“写实文学”,为什么要“推倒”重来?将“古典文学”与“写实文学”相对立,这从形式逻辑上讲不也明显说不通吗?
第二,说陈独秀排斥和否定古代文学,这种理解也同《文学革命论》全文的意思直接抵触。因为就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对相当多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方说,他肯定了《诗经》的主体部分──“国风”,还肯定了楚辞,说“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用“斐然可观”四个字去赞美,还不高吗?接下去,陈独秀又说:“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可见,他对南北朝及其后的五言诗的新鲜活泼,评价也很高。由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对“诗至唐而极盛”的现象已多有涉及,陈独秀没有在唐诗方面再作申述,只对律诗尤其排律表示非议。而对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则称他们“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自是文界豪杰之士”。至于“元明剧本,明清小说”,陈独秀更称之为“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所以,从《文学革命论》全文来看,陈独秀绝对没有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的意思。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陈独秀进一步提出‘推(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
 ,那显然是受了表面文字的迷惑而导致的误读。
,那显然是受了表面文字的迷惑而导致的误读。
这样说来,陈独秀所“推倒”
 的“古典文学”这个概念,既不是在“古代文学”的意义上使用的,也不是在“经典文学”的意义上使用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的理解──无论是称赞或者责备──都不符合实际。我们应该换一种思路来接近陈独秀所谓“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的本意。比方说,不妨从近代汉语词汇变迁的角度去考察一下“古典”“古典文学”这些概念的演化。
的“古典文学”这个概念,既不是在“古代文学”的意义上使用的,也不是在“经典文学”的意义上使用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的理解──无论是称赞或者责备──都不符合实际。我们应该换一种思路来接近陈独秀所谓“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的本意。比方说,不妨从近代汉语词汇变迁的角度去考察一下“古典”“古典文学”这些概念的演化。
“古典”这个词在汉语中出现得很早(至少东汉时就有),但词义与20世纪20年代起流传的很不一样。《后汉书·儒林传论》说:建武五年,“乃修起大学,稽式古典”。这里的“古典”一词仅指古代典章,并不包含后来的“经典(Classic)”的意思。直到民国四年(1915)商务印书馆初版《辞源》仍然这样释义:“‘古典’,古代典章也。”在“古典”一词中注入“经典”这层含义,是欧洲文艺史上Classicalism这个外来词语经过日本学界而传入中国,并且被译成“古典主义”之后。“古典主义”,可以说是由日语转入的汉字原语借词。1915年的《辞源》初版中来不及收入“古典主义”一词,待到民国二十年(1931)出版的《辞源续编》,才开始收进这个词条,并有这样的释文:
古典主义Classcalism,此指十七八世纪欧洲文坛的主潮。十八世纪为理智的时代,文艺亦大受其影响。所谓古典主义,即以追摹希腊、罗马古代作家之典范为目的,以匀整平衡均一为技巧之极。故其结果,为压制个性,绝灭情思。十九世纪初兴起之传奇主义(今称浪漫主义──引者),即为古典主义之反动。古典主义最盛期约一百年,自一六七五年至一七七五年,意大利、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各国文学,皆受其影响。

其中所说“希腊、罗马古代作家之典范”,就是“经典”之意。而“以匀整平衡均一为技巧之极。故其结果,为压制个性、绝灭情思”,则是学界公认的欧洲“古典主义”的特点和明显的局限。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通过日本学界而对欧洲文艺史上的“古典主义”思潮有所了解。“古典主义”效法希腊、罗马的一味仿古和束缚作家个性的那套严整的艺术规范,都使陈独秀联想到中国文学史上崇尚靡丽、看重对偶音律而内容相对空虚的骈体文以及明代的前后七子和桐城派归、方、姚、刘的复古主张,他把这些作品看作中国的古典主义文学,竭力想将这类仿古文学和崇古思潮从主流文坛上驱赶出去。自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起,陈独秀就想让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了解世界文学经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陈独秀称之为理想主义)而走向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这种发展趋势。他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就说:
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此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文学者反对模拟希腊罗马古典文体。所取材者,中世之传奇,以抒其理想耳。此盖影响于十八世纪政治社会之革新,黜古以崇今也。

陈独秀将欧洲古典主义的特点,看作“模拟希腊罗马古典文体”,而将其对立面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则称之为“黜古以崇今”。在以“记者”身份回答张永言的《通信》中,陈独秀又说:
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

在回答张永言的另一封《通信》中,陈独秀对中外“古典主义”文学表现了更加鲜明的批判态度。他说:
欧文中古典主义,乃模拟古代文体,语必典雅,援引希腊罗马神话,以眩赡富,堆砌成篇,了无真意。吾国之文,举有此病,骈文尤尔。诗人拟古,画家仿古,亦复如此。理想主义,视此较有活气,不为古人所囿;然或悬拟人格,或描写神圣,脱离现实,梦入想像之黄金世界。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

这是陈独秀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他自己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前一年多所写的一些文字。可见他在那时对中国文学革新问题早已形成了许多想法。他的矛头所向,对准了四六骈体,对准了仿古文学,对准了当时文学中浮华颓败的风气,其精神乃至用语都是和后来的《文学革命论》相连贯的。如果说《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曾登载过友人的长律还说过捧场的话,那么,稍后在反对仿古文学并坚信“古典主义之当废”
 方面,就始终和胡适等人坚定地站在同一战线上。而在《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后两个月,陈独秀又刊出《答曾毅书》,更鲜明地反对“抄袭陈言之古典派”,并且说:“仆之私意,固赞同自然主义者,惟衡以今日中国文学状况,陈义不欲过高,应首以掊击古典主义为急务。理想派文学,此时尚未可厚非。但理想之内容,不可不急求革新耳。”
方面,就始终和胡适等人坚定地站在同一战线上。而在《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后两个月,陈独秀又刊出《答曾毅书》,更鲜明地反对“抄袭陈言之古典派”,并且说:“仆之私意,固赞同自然主义者,惟衡以今日中国文学状况,陈义不欲过高,应首以掊击古典主义为急务。理想派文学,此时尚未可厚非。但理想之内容,不可不急求革新耳。”
 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这里的“古典文学”其实是他所理解的“古典主义文学”——而且是在前面加上了“陈腐的”“铺张的”两个定语的“古典主义文学”。不过为了字数相等、对得工整,他把“主义”两个字省略掉了而已。确切一点说,陈独秀“推倒”的是一种仿古文学。陈独秀绝没有要“推倒”或者“打倒”中国古代文学乃至经典文学的意思。如果采用这种理解,那么,前面所说的“古典文学”与“写实文学”意义上不能对应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他要“推倒”的是“古典主义文学”,“建设”的是“写实主义文学”,两者都具有创作方法或创作态度的性质,对应起来一点都不勉强了。这样,陈独秀的本意也就显露而豁然开朗了。
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这里的“古典文学”其实是他所理解的“古典主义文学”——而且是在前面加上了“陈腐的”“铺张的”两个定语的“古典主义文学”。不过为了字数相等、对得工整,他把“主义”两个字省略掉了而已。确切一点说,陈独秀“推倒”的是一种仿古文学。陈独秀绝没有要“推倒”或者“打倒”中国古代文学乃至经典文学的意思。如果采用这种理解,那么,前面所说的“古典文学”与“写实文学”意义上不能对应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他要“推倒”的是“古典主义文学”,“建设”的是“写实主义文学”,两者都具有创作方法或创作态度的性质,对应起来一点都不勉强了。这样,陈独秀的本意也就显露而豁然开朗了。
应该说,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后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是按这种理解去看待陈独秀所提的“三大主义”的。以《新潮》杂志为例,它从创刊时起,就按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主张来做。第一卷第一期就刊登《社告》(相当于稿约)对“本志”来稿作出规定,第二条说:“文词须用明显之文言或国语,其古典主义之骈文与散文(本志)概不登载。”第四条说:“小说、诗、剧等文艺品尤为欢迎,但均以白话新体为限。”可见,陈独秀“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专指“古典主义的骈文与散文”这一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过什么歧义。产生误读是后来的事。
顺便说一下,如果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军三大主义”翻译成外文的话,我主张把他要“推倒”的“古典文学”译成“仿古文学”为好。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外文出版社想要把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翻译成英文、日文、西班牙文三种文字,我和该社英文部的朱惠明女士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赞同我的意见,不是把陈独秀提出的“推倒古典文学”翻译成Get rid of the Classic literature,而是翻译成Get rid of the literature in the Style of Classics。这是研究了《文学革命论》全文和陈独秀当时的整个文学思想之后才得出的看法,从而避免了翻译上“断章取义”的毛病。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也接受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有些见解的影响。胡适文章在论述“用典”方面比较细致,也比较精辟。正像钱玄同《寄陈独秀》信中所说:“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也。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中之最下劣者。”胡、钱这些看法,更坚定了陈独秀反对骈体、反对仿古的决心。《文学革命论》中指责“贵族之文”“古典之文”的地方,例如“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的泥塑美人”之类,其中也包括了典故运用上的“铺张堆砌”在内。这恐怕是由于陈独秀多少混同了欧洲与中国两种不同的“古典主义”的缘故──如果说中国文学中也有“古典主义”的话。
原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