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长篇小说的追踪与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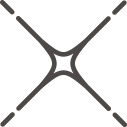
不管人们对穆时英有多少不同的评价,却大概都会承认:他是一位有才华(“鬼才”也罢,“天才”也罢)的中国新感觉派的代表性作家。
穆时英的作品,通常知道的有《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四种,都是短篇小说集。20世纪80年代初我编《新感觉派小说选》时,曾发现《第二恋》《狱啸》《G No.Ⅷ》等集外小说,却也都是短篇或中篇连载未完的。至于穆时英发表过长篇小说没有,虽然有一些线索可寻,却一直得不到确证。
所谓“有一些线索”者,一是穆时英将《上海的狐步舞》称为“一个断片”,意味着它可能是长篇的一部分;而《现代》杂志二卷一期发表《上海的狐步舞》时,编者施蛰存所写《社中日记》则明确地说穆此篇“是他从去年起就计划着的一个长篇中的断片,所以是没有故事的”。可见他确实写着长篇小说。二是在1936年年初的《良友》图画杂志一一三期和别一些刊物(例如《海燕周报》)上,曾刊登过“良友文学丛书”将穆时英长篇小说《中国行进》列作丛书之一的广告,其广告词说:
这一部预告了三年的长篇,现在已全部脱稿了。写一九三一年大水灾和九一八的前夕中国农村的破落,城市里民族资本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作者在这里不但保持了他所特有的轻快的笔调,故事的结构,也有了新的发见。
既然“全部脱稿”,当然就有正式出版的可能。于是我在1983年5月写信请教当年“良友文学丛书”主持人赵家璧先生:《中国行进》这部长篇到底是否出版过?家璧先生当时正在病中,病愈后他在7月10日复信说:
家炎同志:
…………
穆时英是我大学读书时同学,颇有写作天才,如此下场,我对他颇有惋惜之情。第三辑《新文学史料》里,将发表我又一篇回忆史料,其中有一段提到他,但非常简短,未提及你要了解的那个长篇。
这部最初取名为《中国一九三一》的长篇是我鼓励他写的。当时我对美国进步作家杜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三部曲很欣赏,其中一部书名就叫《一九一九》。穆借去看了,就准备按杜斯·帕索斯的方法写中国,把时代背景、时代中心人物,作者自身经历和小说故事的叙述,融合在一起写个独创性的长篇。这部小说后改称《中国行进》……
据我的记忆,这部书曾发排过。由于用大大小小不同的字体,给我印象较深。但此书确实从未出版,其中各个章节也未记得曾发表在任何刊物上。如果你们现在不提起,我简直想不起来了。上述一点史料,不知能满足你的要求否?下次如来沪出差开会,希望抽空来舍谈谈。
敬颂
著安
赵家璧
83.7.10
赵家璧先生的答复当然最有权威性,我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继续追寻了。但是,有一次西安的钟朋先生来访,他说到黑婴曾告诉他,穆时英有一部长篇,似乎曾在上海一家报纸连载过,到底是什么报却记不甚清楚。这样,我又从希望的灰烬中看到了一点火星。从种种迹象判断,我猜想,黑婴先生说的这种报纸,大概会是《晨报》。去年夏天,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李今女士要到上海查找穆时英、刘呐鸥的资料时,我就将这一线索告诉了她,请她前去一试。
李今女士在上海用许多时间认真翻阅了《晨报》以及《小晨报》,结果是:《中国行进》这部长篇小说并没有找到,却意外地发现了穆时英的许多散文作品和理论文字,尤其是有关电影艺术和文学方面的许多佚文,像《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电影的散步》《电影艺术防御战》《文学市场漫步》等几组论文。这些文字既显示了穆时英的文学艺术见解乃至社会政治观点,也表明了他所受到的西方电影、戏剧、小说的熏陶,以及他当时的苦闷与思考。接着,李今女士又根据香港嵇康裔一篇回忆文章(这是Chrys Carey先生帮我复印的)所提供的线索,在1936年上海《时代日报》上发现了穆时英写上海“一·二八”抗战的一部长篇——《我们这一代》(可惜这部长篇因作者去了香港而仍未连载完毕);此外,还发现了穆时英的几篇不为人知的短篇小说。李今女士这些经过辛苦劳作而获得的发现,总计有四十万字左右,大大丰富了学术界对穆时英的资料掌握,足以将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连穆时英到底是汉奸还是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个谜,或许也可由此获得旁证。
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穆时英全集》并未在1997年写完《编后记》的较短时间内获得出版。但迟迟未能出版也有好处,就是可以补收进一些后来继续发现的穆时英的作品,其中也包括我们寻觅已久的《中国行进》(初名《中国一九三一》)。——发现它的功劳,则首先应该归于旷新年先生。
大约是2001年岁末,旷新年先生到蓝旗营家中来看我,谈到近期在翻阅30年代刊物时,发现了穆时英在《大陆》杂志上曾经连载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三一》。我真是喜出望外,请他赶紧代我复印一份。校阅的结果,虽然知道这依旧并不完整,但毕竟证明穆时英确曾在当时报刊上发表过这部长篇,也就留下了将来或许还有机会能补全的希望。
此后又继续获得了新的发现,那就是《上海的季节梦》,它是穆时英长篇小说《中国行进》中的一部分,连载于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出版的旬刊《十日杂志》第七期至第十五期,发现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张勇先生,而由解志熙教授热心地告诉了我们(解本人还发现了穆时英的一篇散文)。它与旷新年博士此前从《大陆》杂志上发现的《中国一九三一》,都是同一部长篇的一部分。我们特在此向旷、张、解三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一九三一》《上海的季节梦》两个部分的相继发现,不但确证了《中国行进》这部长篇小说的存在,而且改变了我们对此前发现的若干作品的看法。例如,我们曾经以为《我们这一代》是一部专写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独立作品,《田舍风景》是一组散文化的短篇小说,或一个中篇小说,但后来一对照其主要人物形象,才发现它们原来都是《中国行进》中的一部分。
这样,迄今为止,关于《中国行进》确实已经发现了四个部分,连同原先作为短篇发表的《上海的狐步舞》,就已经有了总计近十五万字的五个部分。我们在《中国行进》这个总标题下暂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将来如果还有新的发现,经过整理研究,剔除某些可能有重复的文字,也许可以较好地恢复这部小说的原貌。
我还想提到另一位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那就是吴福辉先生。他在深入研究海派小说的过程中,发现了穆时英还有一部最早创作并正式出版的长篇:《交流》。这部约十万字的小说在1930年由上海芳草书店印行。书末作者自署:“二十三日,五月,一九二九年,于怀施堂。”写作时间简直与《狱啸》难分先后(《狱啸》写毕于“一九二九,五,十五日”)。应该说,这是穆时英真正的处女作。当时穆时英只有十七岁,完全没有什么名声,别人无须利用他的名字来推销假货赚钱。小说情节建立在凭空编故事的基础上,破绽颇多,技巧相当幼稚,但语言中诗的质素和回旋复沓的调子,证明它确属穆时英的手笔。也许作者后来对它和《狱啸》这两种最早的作品都很不满意,所以绝少提到,以至几乎无人知道。现在发掘出来,对我们了解穆时英的成长过程和文字磨炼功夫,仍是有意义的。
总之,这部《穆时英全集》,可以说是我们根据某些线索追踪穆时英的长篇小说,在此过程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收获的结果。我们最初只想找《中国行进》,无意于编这样的《全集》,后来却意外地形成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这或许就叫作“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吧!
既然编成了《全集》,我们也就乐于在书的最后部分附录那些好不容易搜集来的前人对穆时英回忆、评论的文章,作为史料留存。其中有几篇是日本作家在侵华战争时期发表在日本杂志上的文字,也由李今女士请李家平、王升远先生将它们译成了中文。我们相信,附录所有这些资料,对于广大读者、研究者,都将是一种方便。
我和李今女士在编辑这部《全集》时,得到多方面的帮助。穆时英发表在香港报刊上的文字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咏梅小姐提供的,陈兴宽先生补充了穆时英的几篇散文。另外,在这些资料的照相、还原、复印等方面,得到了上海辞书出版社王有朋、何香生先生,北京图书馆边延捷女士的热情协助,谨在此致以我们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1997年3月18日
2006年8月15日增补修改
原载《穆时英全集》第三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