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穆时英的文学史地位
——《穆时英全集》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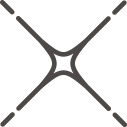
在中国,真正的现代都市小说,大概只能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感觉派出现的时候算起。其发祥地则是上海。
30年代的上海,有点像80年代的香港,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世界性的大都会。它有“东方巴黎”之称。其繁华程度,就连当时的东京也难以匹敌,虽然它呈现着明显的半殖民地畸形色彩(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大的租界就设在这里)。中国现代都市小说——而且是带有现代主义特征的都市小说,最早诞生在这里,绝非出于偶然。
鲁迅在1926年谈到俄国诗人勃洛克时,曾经赞许地称他为俄国“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并且说:“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如果说20年代前半期中国确实没有“都会诗人”或“都会作家”的话,那么,到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可以说已经产生了——而且产生了不止一种类型。写《子夜》的茅盾,写《上海狂舞曲》的楼适夷,便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他们是站在先进阶级立场上来写灯红酒绿的都市的黄昏的(《子夜》初名就叫《夕阳》)。另一种类型就是刘呐鸥、穆时英等受了日本新感觉主义影响的这些作家,他们也在描写上海这种现代大都市生活中显示出自己的特长。其实,这样的区分多少含有今天的眼光。从当时来说,两者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楚。刘呐鸥在20年代末,思想上也相当激进,对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都表示支持。他在上海经办的水沫书店,曾经是左翼文化的大本营。穆时英最早的小说,也称半殖民地上海为“造在地狱上的天堂”,揭露外国殖民者和资产阶级的荒淫丑恶,明显地同情下层劳动者和革命人民。而“左联”成员楼适夷,也曾尝试用新感觉主义手法来写《上海狂舞曲》,只是后来听从冯雪峰的劝告,才中止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可见,无论在日本或中国,新感觉主义和普罗文学运动最初都曾以先锋的面貌混同地出现。
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属于现代大都市。场景是夜总会、赛马场、电影院、咖啡厅、大旅馆、小轿车、富豪别墅、滨海浴场、特快列车。人物是舞女、少爷、水手、资本家、姨太太、投机商、小职员、洋行经理,以及体力劳动者、流氓无产者和各类市民。小说的语言、手法、节奏、意象乃至情趣,也有明显的革新和变异。这类作品比较充分地体现了20世纪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种种特点。如果说刘呐鸥(1900—1940)由于自小生长在日本,他笔下的都市生活上海味不浓,有点像东京,语言也多少显得生硬的话,那么,穆时英(1912—1940)却以他耀眼的文学才华和对上海生活的极度熟悉,创建了具有浓郁新感觉味同时语言艺术上也相当圆熟的现代都市小说。杜衡在30年代初期就说:“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都市而没有采取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在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这是时英。”(《关于穆时英的创作》)苏雪林也说:“穆时英……是都市文学的先驱作家,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和保尔·穆杭、辛克莱·路易士以及日本作家横光利一、堀口大学相比。”(《中国现时的小说和戏剧》)可见穆时英的都市小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穆时英最早的集子《南北极》里的小说,大体是写实主义的。到1932年以后出版的《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三个集子,则呈现出颇不相同的现代主义倾向。作者把浪漫主义、写实主义都看作“过时”的货色。在一个短篇小说中,穆时英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对话,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态度:
“你读过《茶花女》吗?”
“这应该是我们的祖母读的。”
“那么你喜欢写实主义的东西吗?譬如说,左拉的《娜娜》,朵斯退益夫斯基的《罪与罚》……”
“想睡的时候拿来读的。对于我是一服良好的催眠剂。我喜欢读保尔·穆杭,横光利一,堀口大学,刘易士——是的,我顶爱刘易士。”
“在本国呢?”
“我喜欢刘呐鸥的新的话术,郭建英的漫画,和你(指穆时英自己——引者注)那种粗暴的文字,犷野的气息……”
在1983年编成的《新感觉派小说选》和1996年编成的《穆时英:都市小说》中,我虽也保存了《偷面包的面包师》《断了条胳膊的人》两篇作为穆时英写实小说的样本,却理所当然地着重选录了他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新感觉主义作品,如《上海的狐步舞》《夜》《黑牡丹》《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街景》《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白金的女体塑像》《第二恋》等,因为这是穆时英获得“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称号,或者说穆时英之所以为穆时英的主要业绩。
穆时英新感觉主义的都市小说有些什么显著特色和创造?
特色之一,这些作品具有与现代都市脉搏相适应的快速节奏,有电影镜头般不断跳跃的结构。它们犹如街头的霓虹灯般闪烁不定,交错变幻,充满着现代都市的急促和喧嚣,与传统小说那种从容舒缓的叙述方法和恬淡宁静的艺术氛围完全不同。以《上海的狐步舞》为例,全篇都是一组组画面的蒙太奇式组接,文字简捷而视觉形象突出,富有动感和跳跃性,艺术上得力于电影者甚多。描述舞场情景时,作者有意从舞客的视角,多次回旋反复地安排了几段圆圈式的相同或相似的文字,给人华尔兹般不断旋转的感觉。在快速节奏中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病态生活,这是穆时英的一大长处。
特色之二,穆时英笔下的人物,常常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公墓·自序》)。《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可以说写了当时上海生活的一幅剪影:从舞女、职员、学者、大学生到投机商的五位主人公,每人都怀着自己的极大苦恼,周末涌进了夜总会,从疯狂的跳舞中寻找刺激。黎明时分,破产了的“金子大王”终于开枪自杀,其余四人则把他送进墓地。这在穆氏小说人物中颇有代表性。穆时英的人物形象,尤以年轻的摩登女子为最多,也最见长。她们爱看好莱坞电影,“绘着嘉宝型的眉”,喜欢捉弄别人,把男子当消遣品,而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是男子的玩物。无论是《夜》里那个舞女,还是《Craven“A”》里的余慧娴,或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的黄黛茜,她们尽管“戴了快乐的面具”,却都带着大大小小的精神伤痕,内心怀有深深的寂寞和痛苦。《黑牡丹》里那个女主人公的命运,已经算是够好的了:她在一个深夜为了躲避舞客的奸污,从汽车中脱逃狂奔,得到别墅主人的救护,终于成为这位男主人的妻子。但她一直没有对丈夫说出自己的舞女身份,也要求一切知情人为她保密,她不愿再去触动自己灵魂深处的那块伤疤。能够写出快乐背后的悲哀,正是穆时英远较刘呐鸥等人深刻的地方。
特色之三,穆时英小说中有大量感觉化乃至通感化的笔墨。
新感觉派之所以被称为新感觉派,就因为这个流派强调直觉,强调主观感受,重视抓取一些新奇的感觉印象,努力将人们的主观感觉渗透融合到客体描写中去,以创造新的叙事语言和叙事方法。例如,穆时英将满载旅客的列车开离站台的一刹那,写成“月台往后缩脖子”(《街景》);将列车夜间在弧光灯照耀下驶过岔路口,写成“铁轨隆隆地响着,铁轨上的枕木像蜈蚣似地在光线里向前爬去”(《上海的狐步舞》)。月夜的黄浦江上,穆时英这样写景:“把大月亮拖在船尾上,一只小舢板驶过来了,摇船的生着银发。”(《夜》)黎明时刻的都市,在他笔下被形容为:“睡熟了的建筑物站了起来,抬着脑袋,卸下灰色的睡衣。”主人公坐电梯到四楼,穆时英写作:“电梯把他吐在四楼”(均见《上海的狐步舞》)。这类写法既新鲜,又真切,富有诗意,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穆时英还常常把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些由不同的器官所产生的不同感觉,复合起来、打通起来描述,形成人们常说的“通感”。像《上海的狐步舞》里,就有“古铜色的鸦片烟香味”这类词句。《第二恋》里,当十九岁的天真稚嫩的女主人公玛莉第一次出场时,男主人公“我”感到:“她的眸子里还遗留着乳香。”两人因经济地位的悬殊而遗憾地未能结合,九年以后再见,玛莉“抚摸着我的头发”,“那只手像一只熨斗,轻轻熨着我的结了许多绉纹的灵魂”。应该说,这些都是相当精彩的笔墨。
此外,穆时英在有些作品中还较为成功地运用了心理独白。《白金的女体塑像》就呈现了一位男医生在女病人裸体面前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变化,有两段文字甚至连缀而不加标点,一如西方有些现代派作品那样。《街景》则多少采用了时空错位的意识流手法。这在二三十年代也是一种新的探索。
凡此种种,都表明穆时英对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二十八岁就去世的穆时英,也许只能算是一颗小小的流星,然而,历史的镜头却已经摄下了它闪光的刹那。
原载《穆时英全集》第一卷卷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