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学术领域应该“费厄泼赖”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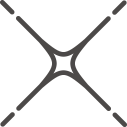
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史上一位杰出的理论批评家。他继承鲁迅的事业,为捍卫革命文学最可宝贵的思想性和艺术生命力,反对左翼文学内部的机械论倾向,持续奋斗了大半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应该重新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评价。
胡风的文艺思想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它包含着一系列真知灼见。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文学是生活花粉酿成的蜂蜜,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这样的命题。他说过,东平、路翎之所以写出好作品,是因为作家“有如一个吸盘,不肯放松地钉在现实人生底脉管上面”。可见胡风非常看重生活,他的文学思想是唯物的,却又避免了机械论的毛病。他提倡“到处有生活”,就比一些左翼理论家在生活题材问题上的狭隘提法要宽广和辩证得多。他提倡写“活的人、活人底心理状态、活人底精神斗争”,表现出对艺术教条主义、主观公式主义的深恶痛绝。由于对文艺特征的深切把握,也由于对中国封建主义统治及其“精神奴役创伤”的深刻了解,胡风在重视客观生活源泉的同时,又强调要充分发挥作家主体的作用。他把现实主义作品看作是作者主体与现实客体拥抱、突入、相生相克进而达到“融然无间”的产物,并且认为作家主体能否对现实客体“突入”“搏斗”“体验”“扩张”,乃是贯彻现实主义的关键。在历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家中,还没有哪一个人像胡风这样把作家主观作用强调到如此突出的程度。胡风与七月派作家的这一重要思想,终于促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一种新形态的现实主义文学——“体验的现实主义”的诞生。
胡风所说的主体对客体的“突入”“扩张”“搏斗”“相生相克”,曾经遭致种种误解、曲解和非议。其实,透过他有点晦涩的文字,我们可以大致归结出其中包含的这样三层意思:第一,胡风认为,创作过程中作者对复杂的客观对象既体现又克服,既肯定又批判,在深入把握客体的同时,由此也引起主体“深刻的自我斗争”。它是一种双向的运动过程。这种认识比“世界观决定创作方法”的简单说法,显然更为辩证和科学。第二,基于对鲁迅小说开创的“灵魂的写实主义”的向往,胡风提出,作者必须深入体验和理解人物的心理,把握人物的灵魂。这是深一层的“突入”,也是表现“一代的心理动态”的必要前提。它同样是胡风的一个很好的见解。第三,胡风还认为,作者在表现对象的过程中,应该自然地将感情渗透溶化进去,防止客观主义,不使作品成为“冷冰冰的绘图演绎”。这个看法明显带着七月派创作的独特印记。上述这些见解,无论对文学创作具有普遍的意义,或只对某个流派具有指导意义,都包含着积极可贵的价值。
为了回答别人的批评,胡风在40年代末写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中提出了自己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估计。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因此,“说知识分子也是人民,是并不为错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估计是符合实际的,难能可贵的。
时代并非没有在胡风文艺理论中留下烙印。局部的“左”的痕迹也是有的。胡风反对主观公式主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而他对茅盾、沙汀等社会剖析派作家所谓“客观主义”的批评,则带有本流派审美观点上的狭隘性(实际上《淘金记》等作品都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并非“客观主义”)。此外,胡风理论也有某种经验论色彩,有表达得并不确切、过分夸张的地方。他早年受过尼采思想和《苦闷的象征》的影响,这同样在著作中留有印记。尽管这样,胡风依然是一个有重大贡献的革命的文艺思想家。
胡风及其文艺思想50年代以来的惨痛遭遇,迫使人们思考许多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我以为是这样一点:
在学术、文艺领域里,任何时候都应该实行“费厄泼赖”的原则。要允许被批评者讲话,保护被批评者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过去谁一挨批,就只有检讨权,根本没有辩护权。不管批评者多么蛮横,多么不符合被批评者的原意,都可以发表;而被批评者如果为自己申辩几句,起码被认为是态度不好,遭致上纲越来越高。结论总是按照批评者的调子来做,而不是按照被批评者的实际来做。这样不但冤枉了许多好同志,而且造成一种最严重的后果——培养起极坏的学风,可以随意断章取义,歪曲篡改,给人罗织罪名。这样一种学风一旦形成,就创造了任何人都可能被打倒、被如法炮制的条件,也就为“文化大革命”准备好了温床。一直到今天,这种学风并未绝迹,影响到正常的学术生活乃至政治生活,实在令人遗憾。
1988年7月
原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