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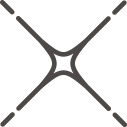
在如今进入古稀之年的同辈学人中,樊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着重大的建树。他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学长。他的学术论著上承前辈,下启后学,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数量虽不算最多,但几乎每篇都很厚重而有分量。其涉及材料之丰富,行文思虑之周严,学术内容之深广与透辟,凡是读过的人,无不感到佩服。
樊骏首先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着突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结合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科的沉浮起伏,他写了不少“研究之研究”的相当扎实的文章,诸如《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等,不仅对过去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并且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意见。他还选择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重要学者中的王瑶、唐弢两位作为个案,就他们的学术道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作了富有深度的研究,写出了《论文学史家王瑶》《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这些沉甸甸的论文。他以自己掌握的大量事例,旁征博引,援古证今,精彩论述了两位前辈学人各自的长处和独特贡献(如王瑶把握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内在联系方面的卓越识见以及善于抓住典型历史现象展开研究的史才,唐弢作为新文学历程亲历者的熟知众多史实与作为创作家的杰出的审美感觉以及表述上的充满诗意),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各自面临的政治要求与学者特性的某种“错位”——“一方面是强人所难一方面是勉为其难所导致的窘迫和焦急”
 ,既让人同情,也发人深省。《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是把这项工作当作“宏大的系统工程”来阐述的,全文长达八万多字,更是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分支学科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不但是对过去几十年文学史料工作的一个综合考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极好的建议,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可以说,这八万字是作者经过长期积累,查阅了至少一二百万字的各种材料才写成的,照我个人看来,实在可以规定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必读篇目和新文学史料学课程的必读教材。
,既让人同情,也发人深省。《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是把这项工作当作“宏大的系统工程”来阐述的,全文长达八万多字,更是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分支学科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不但是对过去几十年文学史料工作的一个综合考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极好的建议,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可以说,这八万字是作者经过长期积累,查阅了至少一二百万字的各种材料才写成的,照我个人看来,实在可以规定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必读篇目和新文学史料学课程的必读教材。
樊骏在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尤其在老舍研究上做出的深刻而独到的贡献,更为学界所公认。他很早就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中肯贴切地评价了老舍的文学成就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老舍的代表作如小说《月牙儿》《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和剧本《龙须沟》《茶馆》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不只是记述个别人物的生活经历,而且真实地再现城市底层的生活场景;不只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尖锐地提出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运的社会课题。它们增强了这类作品表现生活的能力,提高了这类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这是老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贡献,他也因此成为以描写城市贫民著称的作家”
 。樊骏将老舍之于中国比拟为狄更斯之于英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俄罗斯。在稍后发表的《认识老舍》这篇长文中,樊骏更从思想启蒙的题旨,文化批判的视角,习俗心理的描绘,侧重道德判断的人物评价,本色而朴素的写实主义方法,带有悲观色彩的幽默艺术等方面,层层深入并且富有洞察力地考查了老舍作品的鲜明个性与独特风格。他认为,老舍作品最精彩的还在写人物的文化心态。“文化视角,文化剖析与批判,是老舍创作的又一重要特色。由此展开的生动多彩的艺术画面,以及包含其中的深刻命意,都是这位作家的笔墨用力最勤之处,也是他最值得重视的独特创造。”他也对老舍的幽默作了精细的辨析。樊骏还搜集几位不同的知情者所披露的若干材料
。樊骏将老舍之于中国比拟为狄更斯之于英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俄罗斯。在稍后发表的《认识老舍》这篇长文中,樊骏更从思想启蒙的题旨,文化批判的视角,习俗心理的描绘,侧重道德判断的人物评价,本色而朴素的写实主义方法,带有悲观色彩的幽默艺术等方面,层层深入并且富有洞察力地考查了老舍作品的鲜明个性与独特风格。他认为,老舍作品最精彩的还在写人物的文化心态。“文化视角,文化剖析与批判,是老舍创作的又一重要特色。由此展开的生动多彩的艺术画面,以及包含其中的深刻命意,都是这位作家的笔墨用力最勤之处,也是他最值得重视的独特创造。”他也对老舍的幽默作了精细的辨析。樊骏还搜集几位不同的知情者所披露的若干材料
 ,经过综合研究,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在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背后,其实存在着极左思想的可怕干扰,存在着一连串令人吃惊的争议和斗争——尽管这类隐秘情况当时还鲜为人知——从而揭示了早就潜伏着的那些制造悲剧的危险因素。作为研究者的樊骏,常能心细如发,发现一般人很容易放过去的那些问题。举例说,老舍在谈到《赵子曰》等前期作品何以经常对新派青年加以揶揄时,曾经解释说那是因为五四运动的当时他已经工作,以致成了这场运动的“旁观者”“看戏者”。樊骏认为,老舍自己的这个解释“缺少说服力”。在他看来,“老舍对新派青年缺少好感而颇多嘲弄,恐怕还有更为复杂更为内在的原因。例如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革命志士狭隘的排满行径,会不会在身为旗人又刚刚开始懂事的老舍的幼小心灵上造成压抑、惊慌、恐怖之类的对立情绪,从而激起他对那些以新派自居者的直感上的厌恶、怀疑和反感呢?”
,经过综合研究,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在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背后,其实存在着极左思想的可怕干扰,存在着一连串令人吃惊的争议和斗争——尽管这类隐秘情况当时还鲜为人知——从而揭示了早就潜伏着的那些制造悲剧的危险因素。作为研究者的樊骏,常能心细如发,发现一般人很容易放过去的那些问题。举例说,老舍在谈到《赵子曰》等前期作品何以经常对新派青年加以揶揄时,曾经解释说那是因为五四运动的当时他已经工作,以致成了这场运动的“旁观者”“看戏者”。樊骏认为,老舍自己的这个解释“缺少说服力”。在他看来,“老舍对新派青年缺少好感而颇多嘲弄,恐怕还有更为复杂更为内在的原因。例如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革命志士狭隘的排满行径,会不会在身为旗人又刚刚开始懂事的老舍的幼小心灵上造成压抑、惊慌、恐怖之类的对立情绪,从而激起他对那些以新派自居者的直感上的厌恶、怀疑和反感呢?”
 这个推断虽然尚未得到证实,却是较近情理的看法,它显示了考察者自身是何等的敏锐与细致,为其他学者所难以企及。
这个推断虽然尚未得到证实,却是较近情理的看法,它显示了考察者自身是何等的敏锐与细致,为其他学者所难以企及。
与上述两个方面的具体贡献性质有所不同,意义却同样重大的,是樊骏第三方面的建树——在树立良好学风方面所做的贡献。
樊骏先生是位律己极严的人,这种人生态度体现在治学上,就是学风的刻苦,严谨,原创,精益求精,决不马虎苟且。他曾引用马克思将“科学的入口处”比喻作“地狱的入口处”的话,提醒人们要有为学术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精神准备;有时还直接用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来倡导学术上的献身精神(或称普罗米修斯精神、浮士德精神)。而他自己,正是这样率先实践,默默奉献的。通常人们所谓的那点“名”“利”之心,好像都与他无缘。我注意到,在连续几年和文学研究所两位年轻人合写的几篇学科年评中,他那“辛宇”的笔名,总是署在最后。他花不少心血参与修改定稿的一些成果(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现代文学部分),也并不专署上自己的名字。他完成了不少学术成果,却严于编选成书,至今只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篇幅仅占他已刊发的论文的四分之一。他还把香港亲属遗言留给他的一点遗产(约两百万元),分别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用作学术奖励基金,却拒绝使用他自己的名字,而且从不张扬。
 他唯一关心和讲求的是学术质量。研究一个问题,他总要先把所有相关的材料全部读完,把握事情的全貌,否则他不会开始写作。事后如果发现什么新的材料,他也一定会补充进去。连一次普通学术座谈会的发言,他也要认真准备,否则宁可不置一词。他的许多论文,必求史料的充实有力,论析的精当透辟,逻辑的无懈可击;不仅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而且总要改了又改,直到自己满意或比较满意为止。以《论文学史家王瑶》为例,文后就有一段《附记》说:
他唯一关心和讲求的是学术质量。研究一个问题,他总要先把所有相关的材料全部读完,把握事情的全貌,否则他不会开始写作。事后如果发现什么新的材料,他也一定会补充进去。连一次普通学术座谈会的发言,他也要认真准备,否则宁可不置一词。他的许多论文,必求史料的充实有力,论析的精当透辟,逻辑的无懈可击;不仅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而且总要改了又改,直到自己满意或比较满意为止。以《论文学史家王瑶》为例,文后就有一段《附记》说:
本文前后用了半年多时间,写了三稿。1994年5月7日在西安召开的“王瑶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是第一稿。虽然是匆促赶出来的,基本想法都谈到了。《文学评论》编辑部催我将发言整理成文,限定时间与字数,只得略去发言的第五部分,是为第二稿,发表在《文学评论》1994年第五期上。随后比较从容地将文章又改写了一遍,除补入第五部分,其他各节也都作了补充,篇幅几乎增加了一倍。这第三稿才算是定稿。
已经正式发表了,却还要花许多时间继续修改乃至改写,“篇幅几乎增加了一倍”,樊骏写作态度之认真、谨严,于此可见一斑。然而这绝非仅有的个别例证。我们可以再引用论文《认识老舍》在收进《走近老舍》一书时由作者补写的说明:
本文原为1986年老舍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老舍二十年祭》中的一部分,……相隔十年之后,将这部分发言整理扩充成文,着重正面阐述自己对于如何认识老舍的看法。文章连载于《文学评论》1996年第五期、第六期上。这次收入本书,时间又过去了五载有余,发现原文写得匆促,多有缺漏之处和粗糙之弊。为此,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这就是樊骏!他的文章,总是再三修改,认真负责,实实在在,不耍花枪,也从不满足于浅尝辄止。他有一种咬住不放的精神,务必刻苦钻研,绞尽脑汁,求的是结论经得住历史检验,求的是学术论证的深度。达此目的,于心方安。在他身上,治学和做人是完全统一的。他的成果,自然也不免带有历史的印记,也不免会有缺失,但他的学风,无疑堪称表率。
樊骏先生2003年突患脑血栓,最初失语,行动也有困难,住院治疗数月后方有好转,但至今思维、谈话仍存在某些障碍。为了便于人们阅读、研究樊骏先生的学术成果,也为了在学界弘扬他高尚可贵的品格和学风,朋友们一致认为应将他分散于各处的论著编印成集。此次出版这部六十多万字的论文集,所收篇目完全由他自定。朋友们原先建议他多收一些文章,但他本人不同意。即使从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出版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后也仍只选收了三篇。朋友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全书各篇的文字作了校核,改正了错排的个别字句而已。
借此机会,我们诚挚地祝愿樊骏先生早日康复!同时也要向出版樊骏先生这部论文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我们衷心的敬意!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