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谜样的传主解读
——评金介甫的《沈从文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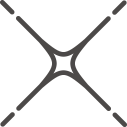
沈从文的一生是个奇迹:他只上过小学,却写了四十多本作品(不算各种选集),成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还当了大学教授、文物研究家,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真令人难以置信!
现在有了另一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以沈从文为传主的第一部传记——而且是资料那样丰富,内容又那样引人入胜的传记,它的作者竟是金介甫(Jeffrey Kinkley,1948— )这样一位西方学者。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也称作一个奇迹;至少在我,读完后确实是感到惊讶和佩服的。
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传》,忠实而详尽地记述了作家沈从文的一生,写出沈带有神秘色彩的复杂经历,以及他同样具有某种神秘色彩的思想和创作。作者在1977年曾完成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以此为起点,金介甫又继续跋涉,艰苦攀登,在海内外(包括在沈从文家乡湘西)进行长期广泛的难以计数的调查、访问,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然后潜心写作,终于完成宏著,198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部《沈从文传》是作者十年心血的结晶。它主要用史实而不是用论断,考察并回答了令人感兴趣的有关沈从文生平和创作的许多问题,诸如沈的苗汉民族血缘关系,近代湘西环境对沈的影响,沈的社会理想以及对革命的态度,沈与丁玲的关系,沈的泛神论思想,沈作品中含有的弗洛伊德思想与现代派文学成分,当年由沈引发的“京派”与“海派”之争,新中国成立后沈在文学上的忽然搁笔,……因而在沈从文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人们常常喜欢用“通过一个人来写出一个时代”这样的话,称赞一部传记。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英文原名《沈从文史诗》),确实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20世纪的中国:它的社会矛盾,它的政治动荡,它的外患内忧,它的深重灾难。作者原本就有这样的意图:“不应该把沈从文的生活只写成作家传记,而应该作为进入中国社会历史这个广阔天地的旅程。”(见《引言》)已成的传记表明,作者这一意图相当圆满地得到了实现。
这部传记围绕沈从文的成长发展,还对近代中国复杂的文化现象作了考察,写出这一文化内在的错综对立的诸般因素:旧与新,中与外,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汉文化与苗文化,以及这些因素对传主的综合作用和影响,从而揭示出20世纪中国文化的某些深层结构,有助于人们从这一大背景上比较科学地把握和评价沈从文的思想和创作。应该说,作者从文化角度对传主思想的若干方面已经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提出的见解也是新颖独到的。如第258页认为:“从政治上说,沈向往的也不是现代民主政治,而是‘原始的无为而治’。”我们也许不一定赞同作者的这一看法,但不能不承认,它是很有见地和深思熟虑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沈从文与现代派文学、与弗洛伊德主义的关系上,这部传记不但提供了不少新鲜的资料,而且已经做了堪称深入中肯的研究。从第四章起,就提到沈从文在20年代“接受了周作人(也就是蔼理斯)的性心理学的观点。1930年又读了张东荪讲性心理分析的厚厚一本入门书《精神分析学ABC》”。第六章指出:“像法国小说家《追忆逝水年华》作者普罗斯特用潜意识来观察人生一样,(沈的小说)对时间作了细致分析。”“小说中角色的每一个质问式动作——他们对现实本身感到半信半疑——代表一种现代的反常状态。”这“使沈的作品有了现代派气味,如果还算不上先锋的话”(第198页)。不仅是沈的小说《薄寒》《第四》《春》《若墨医生》和《八骏图》,就连代表作《边城》,“也有弗洛伊德的气味”(第203—205页)。作者甚至戏称“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可算北京现代派的沈批判上海的现代派”(第189页)。到第七章中,又继续指出:沈于40年代初写的《看虹录》《摘星录》等“思想上、艺术上、主题意义上都使读者‘不知所云’”的作品,乃“是沈从文在受弗洛伊德、乔伊斯影响下在写作上进一步的实验。他想学现代派手法使他的文学技巧达到一种新境界”(第239页)。金介甫的这些介绍与探索,无疑对沈从文研究很有启发性,提高了有关课题的学术水平。
《沈从文传》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基本保持了史学著作应有的客观严谨的态度。作者秉笔直书,忠于历史事实本身,而不是忠于自己的主观好恶。尽管金介甫非常推崇沈从文,认为沈的文学成就高过都德、法朗士,甚至高过莫泊桑、纪德(见《引言》),但他不把沈从文神化,不避讳传主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不隐讳沈的弱点以及在一些事情上应负的责任。如第三章中,作者记述沈从文和阔亲戚熊希龄在香山相聚却并不能消除相互间的“鸿沟”之后,接着指出,“实际上,沈和香山的绅士之间的鸿沟,是沈自己创作引起的,特别是像《棉鞋》《用A字记下来的故事》”,其中就有人身攻击和挑逗失礼的内容(第65—66页)。又如第四章介绍20年代末沈初到上海,确曾写过《旧梦》之类有色情成分的作品,这是由于“经济上的压力才使他不得不下手”(第131页)。再如第六章记述沈从文30年代初在大学教书时,讲课效果不好:“他讲课有如闲谈,大都漫不经心,讲来平淡无奇,声音低得有如耳语。……他在吴淞中国公学第一次教课时,每每咕噜咕噜地讲了几句就退下来,一堂课就此了结。教书显然使他更加感到知识的欠缺。”(第174页)并在注释中引了沈的亲友和家属的话来证明这一点。所有这些,都显示了金介甫作为一个学者的良好品格,从而使他理所当然地赢得读者的信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传记作者有很强的责任感,他确知史学家笔墨的份量,因此,在尊重事实的同时,对一些复杂的学术问题或史实问题,一般都很谨慎,注意讲究分寸,力避过犹不及的毛病。例如第三章中,作者依据公开的资料和调查所得的事实,肯定了沈从文与《圣经》的关系,却又讲得极其适度,字斟句酌,不简单化:既提到“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手持一本《圣经》”,“他有三部作品(可能只有三部)具有真正基督教的象征意义”,“沈懂得基督教就意味着博爱”;又指出沈从文“从来没有对基督教的教规教条有过任何兴趣”(第73页)。同章中涉及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早年的关系时,作者一方面根据沈的《呈小莎》等诗,认为“很可能沈从文早先对丁玲产生过柏拉图式的恋情吧”,另一方面又如实指出:“在20年代后期,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沈岳萌都同沈住在一起,这样,就使谣传的沈丁关系暧昧之说难以置信。”(第69页)我们有些学者讨论问题时常常容易犯感情用事、夸张失控的毛病。《沈从文传》作者下笔时的这种谨慎和有分寸感,既表现了他的严肃,也反映了他的成熟,正是值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不同于原先的中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这次出版的《沈从文传》是全译本。这种版本之所以更有价值,就在于增译了英文原著的六百四十六条注文。符家钦先生在《译后记》中这样说:“金介甫是历史学家,他为搜集传记史料花了大量气力。他的资料卡片多达六千张。传记正文二百八十一页,而用小字排印的注文竟有八十一页,几乎为正文的一半。学术书注释占这样高的比重,在西方学者中也是罕见的。”的确,我认为这正是金氏《沈从文传》的特色所在,也是全书精华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注释不但认真交代了资料的来源(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这点非常重要),而且详尽介绍了有关的事实乃至细节,还阐述了作者本人的若干考证和推测,或者纠正了他人的某些错误,可以说包含了作者的大量心血和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无怪乎金氏要为时事版译本不收这些注释而“耿耿于怀”。例如,对于沈的家世和祖母是苗族的问题,注释中就提供了不少具体材料。对于基督教进入湘西以及田兴恕时代就开始的反基督教渗透,注释中亦有详细记载。又如,关于小说《八骏图》,沈从文自己承认,由于写得过于夸张,得罪了一些朋友。传记作者在第六章注七十七中作了考证,挑明“八骏”的原型除沈自己外,还包括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教授。另如第七章注七十六中,传记作者依据直接间接的材料,指出“沈的散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是沈写他的婚外恋情的作品”,并列出了若干具体事实。所有这类注释,应该说各有程度不等的价值。读者阅读时千万不可缺少耐心,懒得翻看,以免损失许多不该损失的知识养分。
由于历史的和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金氏《沈从文传》也存在某些局限。我想在这里提出两点。一是对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状况显得有些隔膜。作者多次提到内部出版的《文教资料简报》,却不知道已有较长历史也较重要的学术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凌宇的《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就发表在这一丛刊上)。书中还把王瑶、刘绶松、丁易等5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与李何林30年代出版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相提并论,一概称作“左翼方面”,把这些专家排除出“建国以后的批评家”行列(第322页),使熟悉情况者不免觉得奇怪。二是在沈从文与丁玲两位作家的关系上,传记作者对复杂的情况估计不足,受了某些简单化说法的影响,以致夸大了他们之间后来的矛盾。如第193页推测丁玲“迁怒”于沈从文,是因为沈的《记丁玲》把冯达写得太坏;并在第341页注六十三中,对“丁玲为何不悦《记丁玲》”做了三点推断。其实,丁玲何曾“迁怒”于沈!她与沈的思想分歧,早在沈写《记丁玲》前两年就已显露出来,只要读读丁玲以沈从文为原型写的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就会清楚。丁玲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幽囚南京期间,根本不可能自由阅读书刊,怎可断定她一定在当时读过沈的《记丁玲》(何况《记丁玲》中并无对冯达的尖锐批评)!沈本人1949年9月8日致丁玲的信,已经对他当时企图自杀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证之以陈漱渝先生在《人物》杂志上所刊丁沈关系的文章,更可见他们在50年代初仍有友谊的一面。至于有人所说“从1979年到1986年丁玲去世,丁玲都身居高位,使得许多机关都不敢重印沈的作品”,如果我们了解这段时间沈在国内各大出版社出过八种著作共计二十五本,而丁身为作家协会副主席却保不住一本《中国》文学双月刊,即可知道距事实有多远了。虽然如此,这些问题对《沈从文传》来说,毕竟只是个别的,而且我愿意指出,即使在丁沈关系上,作者依然说了不少比较客观的话。《沈从文传》的整个写作,无疑是学风严谨,史料丰富,推进了学界对这位杰出作家的研究的。加上符家钦先生译笔忠实流畅,兼有信达雅之长,就使这部译本成为难得的好书。因此,我衷心乐于向广大读者推荐。
1992年11月22日写毕
原载《读书》1993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