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规范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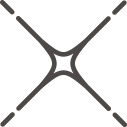
我常想,如果我们从30年代的围剿鲁迅、40年代东北的批判萧军和南方批判萧乾、沈从文等作家,50年代的整肃胡风集团和反右派斗争,60年代前期的文化批评这一系列事件中,精选出一部分最具代表性的批评文章,加以出版,那或许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它提供一面极好的镜子,让人们大长见识,悟出“文革”那样的祸乱其来有自,真正懂得批评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由此可能就批评应有的准则和规范获得某些共识。
在我看来,批评应该有一些起码的规范。
比方说,既然要批评,首先,总得了解自己批评的对象,读过自己想要批评的书。如果没有读过,似以老老实实免开尊口为好。这大概是每位严肃的批评者都能接受的道理。奇怪的是,就有人连对方的一本书都没有读过,竟可以勇气十足、“无惑又无惭”地批判。1948年有位作者批判朱光潜教授时,就坦言:“关于这位教授的著作,在十天以前我实在一个字也没有读过。”这种“没有读过”就断定对方必定“反动”并决意要批判的态度,在当时曾引起学术界的许多议论。所幸这位作者为了批判,毕竟还临时抱佛脚地读了朱光潜一篇《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的文艺随笔,使他可以断言朱光潜所说“人生理想往往决定于各个人的性格”,“有生来是演戏的,也有生来是看戏的”,是在鼓吹“反动”的“宿命”论;并自谓在“演戏”与“看戏”中“我不知道应该属于哪一类型”。其实,这位作者的身份很清楚,他分明在“演戏”,演的是《打虎斩蛟》中蛮横跋扈的周处。瞎子摸象好歹还摸到了大象的躯体的一部分,有的作者却只是听说世界上有大象这种东西,就自以为是地评论起来,凭空推算出某种作品有无价值或是否“反动”。可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岂不成了星相学、算命术?
其次,批评的力量取决于态度的实事求是和说理的严密透辟,并不取决于摆出唬人的声势或抛出几顶可怕的帽子。在我看来,批评者的真正使命是要排出正确的方程式,而不是硬塞给读者一些哗众取宠的结论。试想,对萧乾这样爱国的知识分子扣上“买办”——而且是“标准的买办”的帽子,说他鼓吹“月亮都只有外国的圆”,有半点事实根据吗?不讲什么道理,一味吼叫“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这类口号,能叫作文学批评吗?再说得远一点,20年代末,在署名“杜筌”的一篇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文章中,把鲁迅当作“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来批判,并且定他为“双重反革命人物”,因为“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连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都没有闹清楚,对鲁迅的作品更是完全无知,居然如此气势汹汹地开骂,给鲁迅扣上这样大的帽子,这能说有半点实事求是之心吗?这类文章又能叫作什么文艺批评呢?记得差不多五十年前,刘雪苇老师就在课堂上狠狠挖苦过这类批评家为“善于翻筋斗的表演家”。我希望,这类批评家还是少一点为好。
第三,批评必须尊重原意,忠于原文,不能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另扎一个稻草人为靶子。这应该成为批评者的公德。令人遗憾的是,某些批评恰恰大有背于这类公德。以1948年东北批判萧军为例,所谓萧军“反苏”“反共”“污蔑土改”等罪名,完全由任意拼接、罗织而成:一位中学生在《文化报》上为文记述白俄孩子与中国儿童的争吵,竟被说成主编萧军蓄意挑拨中苏关系;萧军虚拟的人物“老秀才”转变前的思想,竟被摘录出来诬栽到作者本人身上,而对人物转变后“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援前线打倒蒋介石赶走美帝国主义”的言行则故意视若无睹。在整肃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过程中,许多书信的编摘剪接,批判文章的撰写组合,也无不做了很多手脚,用了不少“特技”,借以欺骗世人。以张中晓1950年7月27日致胡风信的遭遇为例:这封长达四五千字的信,竟被摘编得面目全非。原信本为自述身世而作,特别讲到自己1948年5月大量出血、发现患肺结核病已经五六年、陷入贫病交加境地时的悲观心情。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在40年代,患肺结核几乎是绝症,刚发明的青霉素注射液要用金条来买。所以张中晓在信中说:“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来战胜肺结核的,我想,这是使我恨一切的原因。两年来,我所受的苦难比从前的一些日子多,我懂得了什么叫贫困!什么叫做病,什么叫做挣扎!……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很明显,张中晓憎恨的是旧社会、旧秩序、旧制度及其残留物。可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编者却故意删除张中晓这些重要话语,只巧妙地节录了“我过去曾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较再好一点,我准备再写。两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于是,憎恨的来由变得莫名其妙,仿佛只是出于“反革命”本能,而憎恨的对象也从旧社会变成了新社会,终于得到了张中晓向革命者“磨刀霍霍”的“铁证”。这种歪曲篡改之明目张胆,实在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第四,批评宜以对方实实在在的文字做根据,不搞诛心之论。上述断章取义,歪曲篡改,毕竟还利用对方的文字,而“诛心之论”则进了一步,干脆不根据对方实在的文字,只按自己的意图从文字之外想象出对方的罪名,说白了其实是诬陷。有例为证:1948年8月15日,萧军在他主编的《文化报》上,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周年发表了一篇社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说,第一个“八一五”是标志了中国人民战败了四十年来侵略我们最凶恶的外来的敌人之一——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么今年的“八一五”就是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就要战胜我们内在的最凶残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他底匪帮——决定性的契机。同时也将是各色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最后从中国土地上撤回他们底血爪的时日;同时也就是几千年困扼着我们以及我们祖先的封建势力末日到来的一天。
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感觉到萧军这段话体现了一位进步作家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势下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但是,批判他的人,竟从文中“各色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生发出了萧军的罪名。他们刊发了一篇《斥〈文化报〉的谬论》的文章,断定萧军用“各色”两字,意在影射攻击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试问这种手段,和雍正年间查嗣庭因出了“维民所止”试题而被说成要砍皇帝的脑袋的文字狱,岂非如出一辙?
第五,批评就是批评,不要进行人身攻击或造谣中伤。文学批评原属文艺与学术的范畴,发展到文艺、学术之外就不正常。但越出文艺、学术争论的事,历来就有。林琴南五四时期做小说《荆生》《妖梦》,就为了向对方进行人身攻击,并表达出借助军阀武力来镇压新文化运动的愿望。更显著的,则是30年代有人造鲁迅以及左翼作家的谣,说他们“拿苏联的卢布”。这样做,一要诋毁对手的人格,封住他们的嘴巴;二有更加恶毒的用心,即置鲁迅等人于死地,向国民党当局示意这些作家可杀。然而,文人堕落到这种可悲的境地,也就意味着自身文学生命的终结。
提到上面这些,当然不仅为了谈论某一页丑恶的或惨痛的历史,实在也因为在现实中深有感触而发。近年我研究金庸小说,发表了一些看法,就受到有的作者的攻讦。学术见解不同甚至相反,原属常事,我极愿意听到对拙作的批评意见;但我确实无法赞同那种不读任何作品也不了解相关情况就高谈阔论“拒绝”还要骂“北大自贬身份而媚俗”的态度,认为这绝非严肃的作者所应为。在我公开表示对这种荒唐的“拒绝”不值得重视之后,有作者就移花接木,歪曲本意,居然说我把金庸作品当饭吃,竭尽嘲骂之能事。甚至还有人造出谣言说我“拿了金庸的红包”。可以说,半个世纪里发生的种种奇怪事情,这两年在不同程度上也让我摊上了。我实在不明白有的人为什么会那么无聊,不堂堂正正地讨论问题却要采取此等鬼祟手段;也不明白我主张社会要多一点正义感、多一点见义勇为精神、多一点独立思考的头脑,何以如此遭有些人之忌。或许正如鲁迅当年所说:“拿卢布”之类谣言的抛出,“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当然,比起30年代鲁迅等作家几乎被置于死地的境遇,我毕竟幸运得多,至今还没有人说我:“拿了中央情报局的美元”,我似乎理应向造谣者给予的宽容表示感谢!
关于学理讨论和文化批评,伏尔泰有句话说得非常好:“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君子风度,是包括文艺批评工作者在内的一切从事批评人员都应具备的素质。我们应该珍惜伏尔泰所说的这种“权利”。用不了多久,人类就要进入新世纪了。我诚挚地希望,未来世纪的文坛能高扬文明与理性的大旗,将20世纪某些不好的批评风气,作为排泄的垃圾拒之于大门之外。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