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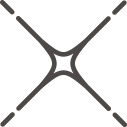
2004年适逢林传甲与黄人两部最早的《中国文学史》面世或撰著一百周年,两位前辈学者当年所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苏州大学(原东吴大学)文学院,联袂在苏州大学举办了“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1904—2004)国际研讨会”。会议不仅就林、黄两位学者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及其史著的价值、意义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取得了基本一致的共识,而且就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反思了文学史研究的不同途径、范式、方法给予教材成果的影响,对这些途径、范式、方法各自存在的长处、弱点做出了细致的分析和有益的探讨。会议的不少论文还就中国文学发展中若干重要环节、重要专题提出了独特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大大有助于这些方面的继续深入研究。
这次会议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多学科围绕一个中心共同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来自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通俗文学五个较大的学科;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和侧面去接触“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这个中心议题,自然地形成相互切磋、相互补充、相互修正的平等对话,因而容易获得比较全面而接近本质的认识。对于我这个平时开惯了单科学术会议的人来说,尤其具有新鲜感,开幕式上,当我听到北京大学陈跃红先生致辞提到中国文学史首先不是由中国人写的,最早的作者和著作应该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H.A.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1901),日本学者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1882),笹川临风的《支那文学史》(1904),认为这些著作对中国学者都有影响时,我马上想到了陈先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特定学术身份。大会发言中,当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以美国《宇文所安〈中国文学思想读本〉的学术取径》为题作发言时,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多学科专家共同讨论问题的优越性。同样,王元骧先生从文艺学角度探讨文学史的写作,听来也别有新意。读日本斋藤茂教授论文《面向新的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时,我作为中国学者,实在感到很受教益,觉得我们很需要听取外国同行的这类意见。苏州大学吴企明教授在他很有见地的论文《文学史研究中的“融通”问题》中说得好:“‘融通’问题涉及的学术领域极广。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外来文化、文学有密切关系,这涉及中外融通的问题。文学发展又与多学科发展有密切关系,这涉及多学科融通问题。文学发展还存在各种不同文体之间产生相互影响的现象,这涉及多文体融通的问题。”借用吴先生这个说法,苏州大学举办的这次多学科国际研讨会,或许可以说就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大融通”吧。
二是论文的高质量。会议收到的四十多篇论文中,大批属于质量较高、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的学术论文。暂且搁下有关林传甲、黄人《中国文学史》的多篇论文不说,像杨义先生的《再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就以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角度和新的见解来阐释中国文学史,它不但绘制着新的文学地图,而且考察和研究着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作者用“中心凝聚力”这个概念说明着汉族文学,用“活力”这个概念说明着少数民族文学,还将少数民族的《格萨尔》《江格尔》等几部史诗和世界各国的史诗从规模上做了比较,来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让人很开眼界。像陈平原先生的论文《被遗忘的文学史》,谈到他从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那里发现了吴梅“五四”前夕在北京大学印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的唐宋至明代部分,弄清了不少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即使在中国文学史若干重要环节、重要段落、重要专题的理解上,一些论文也表现出了新意。例如,台湾东吴大学许清云教授的《元竞调声三术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根据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中的资料加以钩沉并作阐述,恢复了元竞这位在唐诗发展上很有贡献的声律学家的地位。罗时进教授的《“前李杜”时代与“后李杜”时代》一文,打破学术界通常将唐代诗歌史区分为“初、盛、中、晚”四段的说法,改用“前李杜”和“后李杜”两个时代去代替。这绝不是要单纯在文字上花样翻新,而是基于对唐代诗歌发展内在转折关键的深入研究之后才得出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白)杜(甫)在开(元)天(宝)之际出现,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次登峰造极,其最重要的意义是诗歌回到民间状态以后对宫廷创作的全面超越。”文章引用大量史料对此做了较细致的论述,足以引人思考。另外,台湾佛光大学前校长龚鹏程教授的论文《冯梦龙的春秋学》也对学术界通行的晚明文化观提出了不同意见。龚教授由文学和思想二途,详细考察冯梦龙的春秋学,认为冯“根本不反礼教,因为他最重春秋大义”,“他只不过是位畅销书的编辑人或出版商,科举用书与俚俗小说、淫艳曲子一样,都是适应市场流俗之需的”。对龚鹏程先生的见解,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必须认真对待和细心钻研才能回答。可以说,这篇有分量的论文将把晚明文化性质到底是否属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大大引向深入。至于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范围内,有一批论文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如:朱栋霖教授的《国家级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的编写》(以“人”的发现与“人”的观念演变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范伯群教授的《谈中国文学史研究现在进行时》,俞兆平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胡小伟研究员的《形式逻辑的输入与公案小说的嬗变》,于洪笙教授的《侦探小说在中国百年考》,刘卫国先生的《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嬗变》等,它们都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可供人思考的见解。虽然我得到的论文并不齐全,很可能将一部分重要的论文遗漏了,但据此管窥全豹,也足见这次会议论文内容之丰富和质量之齐整了。
三是切入学术议题之快速与深入。大会从一、二场起,便先后请几位教授就林传甲、黄人两种《中国文学史》作很有学术内容的发言: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报告了《国人自撰文学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学术史意义》,香港科技大学陈国球教授报告了《“文学史”的名与实:论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苏州大学王永健教授报告了《先驱的启示——纪念黄人〈中国文学史〉撰著一百周年》。他们都对百年前的两种文学史做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正如王水照等先生所说,林传甲的文学史在时间上略早于黄人,但时间的第一并不等于素质的第一,林著在内容、见解上问题较多,名不甚符其实,倒是黄人的文学史,确实在当时条件下较好地尽到了开拓者的责任。正是从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的回顾这个核心课题出发,会议的议题辐射到了各个方面,与会人员才能不断聆听诸如黄维梁教授的《中国最早的文学史:〈文心雕龙·时序〉》,程章灿教授的《一个英国汉学家眼中的中国文学史》,陈松雄教授的《六朝丽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王锺陵教授的《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袁进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当有旧体文学的地位》等重要发言。
切入学术议题之快与深,这不仅反映了大会拟定的议题之适当,而且也反映出中国文学史研究经过最近二十年左右的酝酿与推进,已经到了一个即将发生学术上重大变革的时期。在这样一个转折性关头,我们抓住纪念南北两种文学史著作诞生百年的机遇,开了一次成功而又紧凑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与反思了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必将对整个文学史学科的今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此,与会者都要深深感谢直接策划了这次会议并付出了巨大劳动的苏州大学文学院和朱栋霖先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敬意!
趁此机会,我还想就近、现、当代文学史问题说点个人的看法。
我曾经部分地翻阅了最近几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等六七种文学史教材。因为只是抽取某些部分翻看,不是从头到尾全部阅读,所以不具有全面评估的资格。就书的体例和局部翻看的章节而言,可以感到这些教材与过去的教材相比,有几个明显的长处:一是时间上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地域上打通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不但有抗战时期的国统区、解放区文学,而且还包括了若干沦陷区的作家。二是学术思想上比较实事求是,不但长期蒙冤的一批革命作家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对长期遭轻视的通俗文学以及张恨水、刘云若、秦瘦鸥、金庸、梁羽生等作家给予应有的评价,还对林纾、学衡派、战国策派、徐訏、无名氏等历来被放在对立面位置上的作家作品重新作了论述,而且对台湾或海外一批有成就的作家像张爱玲、白先勇、余光中等敢于给以应有的肯定。三是对妨碍我们做出科学评价的若干思想障碍和“左”的思潮有所清理,对恩格斯所讲的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由一种“合力”的科学论断有了新的体会。应该说,这是继80年代初解放思想以来文学史学科领域内再次取得的很大进步。
但是,目前这批教材还带有明显的急就章的痕迹。同一本书内部的质量很不平衡。参加每本书写作的队伍非常宏大,人员往往多到三十名左右。前后的见解也不尽一致。特别在文学史如何保持作品原有的审美风貌和审美特性方面,似乎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复述作品也是一种艺术,经过复述以后,应该让读者感到很有味道,感到它和平庸的作品不一样,很想去读原著。因此,落笔之前,撰写者应该重新去读一遍作品,感受和把握原作的审美风貌,将它的精彩处、深刻处在笔下很好地保存下来,传达出来。而现在的一些文学史,在这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距离。包括鲁迅的作品,一经复述和概括,也变得平淡无奇了,一般化了,丧失了原有的深刻性,让人不想读了。这样就很容易回到过去的庸俗社会学的道路上去。此外,知识性差错太多,落笔太随便。根源在于不是读原始材料,不是读第一手材料。有的书中引述的文字是1915年《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但引号之内居然提到“五四”如何如何,这本来是一眼就可以望穿的错误,却在教科书中出现了。再有,责备陈独秀“打倒古典文学”的话,以及认为“五四”有“打倒孔家店”口号的,也不止在一本书中出现。像文学研究会丛书有多少种,这是查一查就可以弄清的,却还是弄错了。有的教材吸取美国华人学者林毓生教授的研究成果,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并且带来了几十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说法靠得住吗?有什么根据?我们身在大陆、经历过“文革”、又研究过“五四”的人都知道:“文革”和“五四”恰恰是反方向的运动。“文革”在上面是由于个人专制,中共党内民主生活受到破坏;在下面是由于对某个领袖的个人迷信非常盛行;上下两个条件的结合,才会发生“文革”。而这两个方面,正是“五四”所要反对的。“五四”提倡民主,就是为了要反对封建专制;“五四”提倡科学,就是为了要反对愚昧迷信。“文革”正是“五四”所要反对的那些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我们怎么能把“文革”归因于“五四”呢?“五四”确实有偏激的东西,但这种偏激和形式主义,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就作过批评和否定。而且当时的毛泽东还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当年肯定孔夫子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可见与1974年所谓“批林批孔”的闹剧也是不相同的。林毓生先生在美国不知道这些,我们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是知道的。我们怎么能把“五四影响后来的文革”这类说法写进教科书呢?!
总之,文学史打通近代、现代、当代这个方向是对的,但20世纪文学史要写得好,有赖于作者较高明的史识(包括掌握第一手资料,不人云亦云)和独到的审美眼光。百年前,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之所以高出一头,就在于史识和审美眼光之超越。他论《史记》时说:“古文学,以盲史、漆园、楚骚及《史记》为极作。然三家各树一帜,而不能相兼;兼之者,迁也。”他认为《左传》、《庄子》、楚骚各有所长,然而到司马迁的《史记》才融汇了这些长处,达到新的高度。这个见解可以说十分精当。直到今天,我们都应该学习黄人的这种史识和审美眼光。
原载《韶关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