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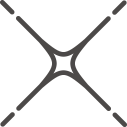
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正在到来。它将逐渐影响并改变过去工业时代建立的经济基础,并将冲击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因而在包括文化界在内的各界人士中引起忧虑、兴奋、困惑等种种不同的反响。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提出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问题,他认为由于科技和新媒体的发展,文学、哲学、精神分析都将消亡,文学研究当然更不复存在。反对者则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类情感的,只要人们有表现感情的需要,文学与文学研究仍将永远生存。这类争论现在方兴未艾。
我对全球化时代给予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也有忧虑,但不那么悲观。我相信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不仅不会带来文学的毁灭,还可以给文学和文学研究带来新的上升的动力。它是利大于弊的。由于电脑技术和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大量文学作品、学术成果得以存入光盘和搬上网络,学者们用于查找资料、阅读原著、交流信息的时间可以大大缩短,效率可以大大提高。许多原先孤立于各地的图书馆、资料室也能够突破地理格局的限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使“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说法近于美梦成真。学术上封闭、垄断的情况也有可能进一步得以打破。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将促使我们从深层次上改变过去遗留的某些褊狭观念。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人与人之间长期对立的战争环境和政治环境,给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蒙上不少非学术的特殊阴影,使学术本身在一些重要方面失去了客观性,从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科学性。最近二十多年来情况当然有了很大改观,但这方面的影响却不能说已经完全扫除,尤其是某些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出发的狭隘观念似乎尚未完全消解。举例来说,台湾百岁女作家苏雪林生前颇为得意的一部话剧作品——30年代发表在《文学》月刊上的《鸠那罗的眼睛》,长期以来就没有受到过注意。新时期内出版的各种现代剧作选没有选它,连1991年专为“补遗”而出版的十四卷本《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孔范今主编)也没有收它。原因何在?是因为苏雪林从法国跑到了中国台湾吗?是因为她几次攻击过鲁迅吗?再不就因为这个戏本身就具有唯美主义的色彩?还是干脆由于我们大家根本不知道这个作品呢?我至今还说不清楚。如果就文学成就而言,《鸠那罗的眼睛》称得上是个较好的戏。欧洲汉学家M.卡利克(M.Calik)最近说:他赞成解志熙的看法,认为苏雪林的《鸠那罗的眼睛》在艺术上超过了英国王尔德(Oscar Wilde)的《莎乐美》,甚至可以说不亚于曹禺的《雷雨》。后面这句话或许可以讨论,因为《鸠那罗的眼睛》似乎缺少《雷雨》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缺少《雷雨》的震撼力。但在唯美主义戏剧中,《鸠那罗的眼睛》比王尔德的《莎乐美》更强烈,更合理,这却是完全可以说的。所以解志熙和M.卡利克的意见,确实有值得中国大陆学者深思的地方。
再举一个例子。金庸、梁羽生、古龙等的新派武侠小说,无论在香港、台湾地区或海外的读者中,尽管有喜欢、不喜欢之分或者在评价高低方面意见有所不同,但从来没有像在中国大陆那样出现有些人要搞大批判、要根本否定、要一棍子打死这类轩然大波。缘由何在?根子恐怕仍在于“左”的影响很深。大陆从30年代起就把武侠小说当成“阻碍群众革命觉悟”的有毒之物。瞿秋白认为,武侠小说教人相信“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后果是不好的。因此,1949年起对武侠小说禁止了三十年。直到90年代,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金庸小说是“精神鸦片烟”,自己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却写文章大声疾呼要清除这些“精神麻醉品”。有位先生还写了《破“新武侠小说”之新》的文章,为不读就搞批判公然辩护道:“没有读过,怎么能凭空批评?这道理似乎很过硬,但也未必置之四海而皆准。打个比方,没有吸过毒、贩过毒的人就不能批评贩毒吸毒?没有卖过淫嫖过娼的人就不能批评卖淫嫖娼?除非谁能对这样的问题作否定的答复,那我就服他。”这类明显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误导,在经济与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将势必受到强烈的抵制和遏止。张恨水早在五十多年前就说过,武侠小说给予中国民众的是英雄主义和见义勇为精神,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侠客来拯救的奴才思想。今天,由于传媒形式从报纸、刊物、书籍扩大到磁碟、光盘和网络,读者增加了无数倍,千千万万读者直接参与到和市场相关的阅读和评论活动中,更将自然地大大淡化与消解政治及意识形态的色彩,使一切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事物愈加显得荒唐可笑。
全球化时代这一大的背景,也促使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若干薄弱环节有可能得到加强和突破,若干“悬案”有可能得到深入探究和解决。以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为例,较长时期内人们很少注意研究。由于“五四”时期倡导科学、民主并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文学创作中也出现过以萧乾为代表的反基督教的倾向,因而遮蔽了学者们的视线,使部分研究者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宗教对现代文学没有多少影响。加上经典性论断“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存在,使人即便接触到作品中某些宗教内容,也往往采取回避或严格批判的态度。其实,20世纪中国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绝不是疏远或无足轻重的。像苏曼殊、李叔同、丰子恺、夏丏尊、废名、赵朴初之于佛教,冰心、林语堂、张晓风之于基督教,苏雪林之于天主教,马宗融、张承志之于伊斯兰教,许地山之先与佛教后与基督教的关系,都说明文学与宗教是互相渗透的。但与历史上文学与宗教关系有所不同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基本上剔除了宗教的迷信愚妄成分,主要吸取有关宗教的人生哲理内容,将宗教的消极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发扬了宗教哲学中有意义的积极部分,从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文化内涵。正如樊骏先生所说:“像许地山着力刻画的春桃那种超然于重重劫难又超越了世俗偏见的倔强性格,就浸透了宗教所宣扬的历尽苦难、达天知命的精神境界——宗教决不只是使人软弱、屈从,也会教人沉着坚定;宗教诚然伴随着太多的迷妄和盲从,却也不乏高于俗世的清醒和明智。”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人前年去世时,用诗句写下这样的遗嘱: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人前年去世时,用诗句写下这样的遗嘱: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花开,水流不断。
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读了这样的遗嘱,我们的精神境界难道不会提升一步?我们的心灵难道不会为之净化?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学术界在文学与宗教方面的这些进展,实际上正显示出:随着信息高度发达、参照系大为增多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学研究工作正在获得一些令人注目的新成果。
这里再说一桩过去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中常常提到,却至今尚无定论的“悬案”:上海外滩公园门口究竟有没有一块“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前两年上海报刊上曾就此事发生过争论。否定者认为,过去的一些说法考查下来都不可靠,连解放后用作展览的一块牌子也是后来做成的。肯定者则举出一些文章中的引述,尤其列举出周作人日记中的记载作为依据。我知道此事,最初是从德国学者瓦格纳教授口中。他说:“过去人们所谓上海的公园门口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现在证明是根本没有的,用来展览的那块牌子也是假的。”这件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旧事,到底是不是子虚乌有的“反帝宣传”呢?我个人不大敢相信。我记得蒋梦麟回忆录《西潮》中,就提到他1899年到上海时,在外滩公园门口看到了“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他还发议论说:“犬居华人之上,这就很够人受的。”后来蒋梦麟留学美国十年,到1917年回国时,发现上海变化很大,外滩公园门口那块牌子改变为“只准高等华人入内”了。如果按蒋梦麟这个回忆,那么,禁止华人与狗进入外滩公园的牌子确实存在过,而且连这块牌子存在的时间段都是明确具体的。周作人1903年7月20日日记则以《公园之感情》为题,记载道: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铺。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围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原文无标点,此新式标点为引者所加——严注)
看来周作人还真动了感情,批判了国人的愚昧冷血,可见此事之不假。至于究竟是七个字还是八个字,这种细节上的出入或疏忽,虽也应该重视,毕竟无碍大体。至今,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老上海》一书所收当年外滩公园英文牌子的照片,也是一个证据(英文牌上第一句话是“这是外国人的公园”,第二句是“狗不能带进去”。想来,因为一般华人并不懂英文,必须另有中文字牌,于是就有了将两句合为一句的“犬与华人不得入内”)。我相信,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弄清真相,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来探究并解决这类“悬案”。双赢是全球化时代的特征。1997年香港回归,是中英通过和平谈判而实现双赢。去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废弃一千多种法律、法规,也是通过公平竞争而实现双赢。在文学和文化方面,客观地不带成见地实事求是地探究并解决上述这类“悬案”,同样也是一种双赢。
全球化时代也将促使我们更好地确立大中华文化乃至全人类文化的宽广视角,改变旧有的中国文学资源只存在于中国本土的观念,树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意识。一系列事实证明:不但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收藏有重要的中国古籍,欧洲的英国、法国、俄国也都藏有敦煌文献(俄还有《红楼梦》重要抄本),甚至连西班牙、葡萄牙也都藏有宋、元、明代的不少契约和文书,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学有好处。越南、韩国还保存着大量汉文小说和诗歌,证明中国文学与周边地区曾经存在过极密切的关系。我在20世纪50年代曾读到过一篇文章,说芬兰和匈牙利有些地方的民歌从曲调到内容都和中国西北部的民歌极其相像,好像是同一个祖先流传下来的。这引起我很大兴趣,使我想到古代匈奴人有一支迁入欧洲的史实,不知两者之间有无关联。总之,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并注意利用各国、各地区储藏的有关中国文学的种种资源。据我的同事、古典文献专家严绍璗教授介绍,仅日本一个国家,就收藏了明代和明代以前的中文善本七千多种,其中有“唐人别集”三百七十四种,“宋人别集”六百八十三种,“明人别集”七百四十八种。如果与我国各图书馆联合善本目录相对照,大约有两千七百多种是中国国内善本目录所没有的。此外,还有不少目录虽然相同而实际内容却不一样的“异本”典籍。像日本大须观音真福寺收藏有唐人手写本《翰林学士诗集》一卷,录载了李世民、许敬宗、郑元璹、褚遂良、长孙无忌、上官仪等十八人的六十首诗,全部不见于《全唐诗》,也不见于《全唐诗补逸》,可能是国内专家还不知道的一种本子。日本三菱财团还藏有宋刊大字本《三苏先生文粹》,在苏洵文后有诗作二十首,是国内各种《三苏先生文粹》所没有的。北大中文系七十多册《全宋诗》的整理出版,当然为国家文化事业做出很大贡献,但如果当初能注意运用日本收藏的宋刊善本,则还可以发现和补充进许多至今未收的诗作,避免遗珠之憾。因此,改变过去那种中国文学资源好像只存在于中国本土的看法,密切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使重要成果能迅速及时地为人们所共同享用,定能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学的研究水平。
全球化时代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过去那些用外文来写作,并且在所在国发生较大影响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作品到底应不应该进入中国文学史?
举例来说,像19世纪末期的陈季同,他是清朝派驻法国的外交官。他在法国期间,从1884年到1904年,以Tcheng Ki-Tong这个名字,出版了用法文写的文学创作和翻译著作至少有八部,如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独幕喜剧《英勇的爱》,散文随笔《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的娱乐》《一个中国人笔下的巴黎人》,还有将《聊斋》译成法文的《中国故事集》等。这些著作当时被译成英、德、意、西、丹麦等多种文字,在欧美广为传播。他的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出版于1890年,虽然取材于《霍小玉传》,却是一部长达三百多页的现代意义上的欧式小说。陈季同是中国第一位用西方方式写长篇的作家。
出现得较晚而情况与陈季同相似的,则是林语堂。他是用英文来创作他的长篇小说的,从20世纪30年代起,写有《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等七部长篇,风行美国,其中《京华烟云》则有不止一种中译本。1975年林语堂还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像这样的作家,法国文学史或美国文学史当然都不会写,那么,是不是应该由中国文学史来承担这一任务呢——如果他们的文学成就是值得入史的话?这也是今天全球化时代促使我们思考的。
以上说的这“四个促进”,也就是全球化给中国文学研究带来的“四重动力”。
诚然,和其他所有领域一样,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也必然给文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我个人认为,负面影响不是来自有的学者所论断的那样“全球化时代根本消灭文学”,恰恰相反,文学可能空前“发达”,出现“疯长”,“网上文学”“美女文学”之类成批出现。“作家”也成批成批地批发出世,其实他们中有不少只是“玩文学”而缺少责任感的。这种情况如果长期下去,文学的实际水准就会大大滑坡,语言“垃圾”就会丛生,文化生态就会失去平衡,真正富有文学韵味的精品,就可能成为绝响。看来,经济的全球化必须同时加强文坛的“环保”;信息的公开化,也不等于个人隐私可以毫无顾忌地公之于众;文学批评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否定“真、善、美”的共同价值标准。信息越是方便,文学创作、文学研究越是需要加强精品意识。全球化进程不仅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同时也赋予我们重要使命,那就是努力捍卫文学的尊严和纯洁,实现中国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2002年3月12日写毕
原载《东方论坛》2003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