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和五四时代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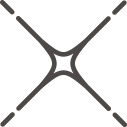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女神之再生》
在中国新诗的黎明时刻,寂静的诗林中还只有不多几声啼鸣。能在当时就感受到五四新时代的“晨钟在响”,并与之相应和,奏出一支支活泼、欢乐、雄浑、动听的时代乐章的,只有郭沫若的《女神》。可以说,《女神》本身就是新诗中的声声“晨钟”。
《女神》是诗人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出版于1921年。它深刻地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是五四时代诗歌的最强音,也是我国新诗的第一块界碑和基石。
诗集中大部分作品写于1919年至1920年。这正是五四爱国运动高涨的年代。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古老神州,我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新兴力量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反帝反封建浪潮在全国各地汹涌澎湃。诗人虽因远在日本,未能亲身参加国内的五四运动,但时代的浪潮同样冲击着他,振奋着他。诗人自己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在五四以后的国内青年……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我处在国外的人却苦于知识的桎梏,想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我爱人的怀里。”
 这段话有助于我们对《女神》的理解。
这段话有助于我们对《女神》的理解。
在《女神》中,我们首先强烈地感受到的是诗人燃烧着的爱国热情。《炉中煤》就是诗人对祖国的“恋歌”。诗人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把自己“眷念祖国的情绪”比作“炉中煤”;由于对祖国的热烈思念,诗人的内心燃烧得像炉火一样炽烈。这种比喻,只有爱国热情达到沸点的人才想象得出。当帝国主义国家的记者诬蔑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的时候,诗人不禁怀着满腔义愤拍案而起,写出了著名诗篇《匪徒颂》。诗人对祖国的思念有时也用“怀古”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电火光中》里,诗人从自己在异国的处境联想到贝加尔湖畔牧羊的苏武,“想象他向着东行,遥遥地正望南翘首;眼眸中含蓄着无限的悲哀,又好象燃着希望一缕”。当然,诗人跟苏武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完全不同,因而他的“乡思”也就没有苏武式的凄凉哀婉,而是充满希望,具有无限宏伟奔放的时代气势。看《晨安》中的一段:
晨安!我年青的祖国呀!
晨安!我新生的同胞呀!
晨安!我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呀!
晨安!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呀!
黄河呀!我望你胸中的冰块早早融化呀!
晨安!万里长城呀!
啊啊!雪的旷野呀!
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动人图景:诗人在祖国上空展翅高翔,飞吻大地,热情呼唤。而全诗中像这样热情奔放的“晨安”,接连道出二十七个。如果没有满怀的爱国激情,那是不可能一气呵成而没有刀斧痕的。
但是,诗人所怀念的祖国,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苍生久涂炭,十室无一完。既遭屠戮苦,又有饥馑患。”——《棠棣之花》中这些诗句,实际上也正是军阀连年混战的旧中国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对于这种黑暗现实,诗人在三个诗剧中给予强烈的诅咒。如《女神之再生》就“是在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颛顼是象征北方”
 。诗剧写双方争夺帝位的结果是,天崩地裂,胜利者与失败者同归于尽。诗人借此谴责了历代统治者疯狂的自杀行为,显示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另一方面,在当时上海这类由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大都市中,有的是另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诗人在《上海印象》中这样写他初归国时的感受:
。诗剧写双方争夺帝位的结果是,天崩地裂,胜利者与失败者同归于尽。诗人借此谴责了历代统治者疯狂的自杀行为,显示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另一方面,在当时上海这类由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大都市中,有的是另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诗人在《上海印象》中这样写他初归国时的感受:
游闲的尸,
淫嚣的肉,
长的男袍,
短的女袖,
满目都是骷髅,
满街都是灵柩,
乱闯,
乱走。
我的眼儿泪流,
我的心儿作呕。
这里表现了对罪恶生活的强烈憎恨。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现实,为了把祖国和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诗人借聂嫈之口唱出了自己的心愿:“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不惜付出血的代价,让自己“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棠棣之花》)
《女神》中特别值得珍贵的,正是破坏旧中国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再造新中国的乐观主义态度。它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的特色。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以《凤凰涅槃》和《女神之再生》为代表的《女神》整部诗集正集中地表现了这种精神。《凤凰涅槃》是一首庄严的时代的乐章,诗人说它“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以《凤凰涅槃》和《女神之再生》为代表的《女神》整部诗集正集中地表现了这种精神。《凤凰涅槃》是一首庄严的时代的乐章,诗人说它“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诗中这样控诉和诅咒黑暗的现实:
。诗中这样控诉和诅咒黑暗的现实: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我们飞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场。
我们飞向东方,
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们飞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们飞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狱。
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
只好学着海洋哀哭。
在这里,诗人对旧世界的态度岂止是怒目横眉、咬牙切齿而已,简直是要一口咬住不放,与之同归于尽!这是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式的憎恨,充满着誓不两立的革命气势。“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只好学着海洋哀哭”——这是诗人对旧世界毫无留恋、完全绝望的表示,绝不是悲观。民族的深重苦难,个人的悲愤郁积,使诗人在凰歌中唱出:“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流不尽的眼泪中,洗不尽的污浊,浇不熄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这正是千百年来古老祖国所经受的苦难的诗的倾诉。这种苦难和羞辱只有用彻底革命的烈火才能消除。凤凰自焚旧体,求得新生,正体现这种和旧世界一刀两断的革命精神,也象征着我们民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乐观自信。不破不立,不止不行,没有对旧事物的彻底破坏,新事物就很难生长起来。破坏、焚毁是痛苦的,但只有经历这种痛苦才能换来真正新生和创造的欢乐。凤凰更生后,变得那样“新鲜”“净朗”“华美”“芬芳”,它们上下翱翔,反复欢唱,正是这样一种新生的欢乐精神的表现。这里,革命精神与乐观主义是同时俱在的。凤凰特别赞颂“火”,就因为“火”是革命精神与乐观主义态度的集中体现,它焚毁了旧的,也熔炼出新的。五四时代需要的就是这把革命的“火”。
毁坏旧的,创造新的,这是贯穿于《女神》中的基本精神,也是《女神》里许多诗篇需要塑造出巨人般的抒情形象的根本原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容易理解: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诗人何以要把“不断的毁坏”和“不断的创造”同时加以歌颂;何以会想象出“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何以要赞美“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比较容易理解:在《天狗》中,诗人何以会想象自己吞掉了日月,吞掉了一切星球和宇宙;何以要把自己变成全宇宙一切“能”的总量;何以会写出“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会比较深刻地理解:在《女神之再生》中,女神们何以在天崩地裂后不肯再去修修补补,而要叫出:“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彻底的革命精神和乐观主义,并不是五四时期写新诗的人都有的。当时有些写新诗的人连“浅薄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不多。胡适的《尝试集》中,就有不少“牛油面包颇新鲜,家乡茶叶不费钱,吃饱喝胀活神仙,唱个《蝴蝶飞上天》”之类庸俗的东西。只有像郭沫若这样的革命诗人,才站在时代的前列,敲着雄壮的战鼓,吹起响亮的号角。闻一多很早就说过:“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
 这就是《女神》最可贵之处。
这就是《女神》最可贵之处。
《女神》之所以充满这种革命精神,是跟诗人接受了当时最进步的思潮有关的。我们可以从《女神》的许多地方明显地看到诗人所受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匪徒颂》中,诗人赞颂了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内的一切“革命匪徒”。在《巨炮之教训》中,就有对列宁“为正义而战”的热烈歌颂。而在《棠棣之花》中,诗人借聂嫈之口道出了自己的社会观:“井田制废,土地私有;已经种下了永恒争战底根本。根本坏了,只在枝叶上稍事剪除,怎么能够济事呢?”《序诗》中更有“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的表示。从诗人对劳动和劳动人民所具有的真挚感情上,也可看出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痕迹: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
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
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当诗人在雷峰塔下看到“一个锄地的老人”的“慈和的眼光”“筋脉隆起的金手”时,他这样叙述自己的心情: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西湖纪游》
甚至当诗人歌颂泛神论者的时候,也是因为他们是些“打草鞋”“磨镜片”“编渔网”的劳动者(《三个泛神论者》)。上述这些当然不能证明诗人当时已经是个社会主义者,也不能说这些思想都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但作为一个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写出《女神》这样强烈地表现五四时代精神的作品,这是毫不足怪、完全可以理解的。
五四时期在中国流行的新思潮有各种各样,相当复杂;诗人在五四时期所受的思想影响也绝不是单一的,除了社会主义思想外,西欧的其他各种思潮——特别是泛神论,对他也起过很大作用。他曾经一再称自己为泛神论者。但是我们应当具体分析。泛神论在当时究竟对郭沫若起了怎样的作用呢?我看,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第一,泛神论否认自然界之外另有什么至高无上的神,这种观念帮助他反对权威和偶像,敢于打倒它。诗人叫出:“我不相信那缥缈的天上,还有位什么父亲”(《地球,我的母亲!》),“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梅花树下醉歌》)这就有很大的反封建意义。第二,泛神论使诗人的“我”与万物结合起来,借此吸取巨大的精神力量。诗人的“我”,在这里正如周扬同志说的,“不但包含我,也包含你,也包含他。这是‘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我”
 。诗人赞颂自然,是因为他觉得自然界具有雄伟、恣肆、常动不息的气势,这正好跟诗人自我的浩瀚奔放的情感和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战斗要求合拍,因而也就加强了诗中的积极乐观精神。最后,泛神论赋予诗人心目中的万物以诗意的生命,把万物拟人化,使之成为抒情对象,因此达到了古代抒情诗中常见的那种“物我合一”的境地。这也许就是《女神》作者之所以赞同“诗人的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
。诗人赞颂自然,是因为他觉得自然界具有雄伟、恣肆、常动不息的气势,这正好跟诗人自我的浩瀚奔放的情感和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战斗要求合拍,因而也就加强了诗中的积极乐观精神。最后,泛神论赋予诗人心目中的万物以诗意的生命,把万物拟人化,使之成为抒情对象,因此达到了古代抒情诗中常见的那种“物我合一”的境地。这也许就是《女神》作者之所以赞同“诗人的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
 的缘由。当然,《女神》中偶尔也有泛神论的消极作用:诗人苦于社会的黑暗,有时把情思和希望寄托在对自然的冥想中。但这个消极面并不占重要的地位。
的缘由。当然,《女神》中偶尔也有泛神论的消极作用:诗人苦于社会的黑暗,有时把情思和希望寄托在对自然的冥想中。但这个消极面并不占重要的地位。
总之,《女神》是时代的产物。它出现于“五四”这样一个中国历史转折点的时候,绝不是偶然的。“五四”是新兴阶级觉醒和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的时代,是几千年封建制度受到空前猛烈冲击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借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文艺复兴时代的话)。觉醒了的中国人民跟新思潮的结合,迸发出异彩夺目的火花,产生出令人震惊的力量。《女神》就是这样一朵时代的花,它充满着海涛怒啸,火山喷发般的雄伟气势,充满着“初生犊儿不怕虎”的精神。“五四”之前,沉闷禁锢的社会固然不会产生这样的诗;“五四”以后,革命深化了,斗争残酷了,需要的是思想上进一步向前发展、艺术上也更深沉的作品,因此也不会有《女神》这种“初生犊儿”的姿态。《女神》中所具有的雄浑宏大的气魄,烈火般炽热的感情,神话和传奇的色彩,不受拘束的自由体式,循回反复而又昂扬激越的节奏旋律,——如果把这些都看作与革命浪漫主义有关的创作特色的话,它们确实是《女神》所特有的东西,但同时又都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1959年2月
原载《语文学习》1959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