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蔡文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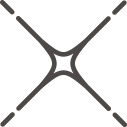
一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谈到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曾经说过:“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斗争;是为了提高某一任务在想象中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亡灵重行游荡起来。”可以说,马克思在这里概括出了历代革命者活动的一条规律:他们援引古代历史事件,目的无非是“古为今用”,无非是借用“古代的神圣服装”,“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对于革命文艺家来说,情况大致是相同的。一个真正革命的作家,绝不会为写历史题材而写历史题材,总要通过处理历史题材而表现时代精神,使之为当代现实斗争服务。当然,这里所说的表现时代精神,丝毫也不意味着作者可以任意改变历史面目,根据现实需要涂饰历史;而是指作家用今天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处理昨天的事件,使历史题材担负起用唯物史观教育现代人的使命。“五四”以来的许多革命作家,正是力图这样做的。
郭沫若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剧作家。他从开始写历史剧的时候起,就明确地以服务于现实斗争为指导思想。三十六年前的第一个历史剧《卓文君》,就是为了要“做翻案文章”(《卓文君》后记),向旧道德开火。而随着作家世界观的逐步变化和革命实践的加深,后来的历史剧就更能紧密地配合现实斗争。众所周知,抗战期间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等作品,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中,起过极好的作用。虽然从创作方法上看,郭沫若同志前后期历史剧有很大不同:早期《三个叛逆的女性》主要是革命浪漫主义,而后期作品除了保有这一特点外,则程度不同地增强了现实主义的成分;然而,从他作品饱含时代精神这一点来说,无论前期或后期,显然都是一贯的。用郭老自己的说法,是都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孤竹君之二子》序)这正是郭老历史剧的鲜明特色。
《蔡文姬》是郭老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新戏。同产生《屈原》的环境相比,这是翻天覆地的两个时代,两个世界。时代的这种变化,不能不为同一个作家的作品,打上不同的烙印,使作品在体现时代精神方面,带有新的特点。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或许是很有意味的:以写历史悲剧著称的郭老,今天却完成了这部“五幕历史喜剧”;而且向来被认为富有悲剧性的蔡文姬这个故事,现在却被按大团圆结局来处理了。这恐怕不能简单地视为偶然的巧合。在过去国统区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为了巧妙机智地同反动派做斗争,作家不但需要善于将时代精神熔铸到历史形象中去,而且往往需要以表现历史悲剧的方式对顽固派做出有力的揭露和控诉。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历史悲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一时的。而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日子里,人们欢欣鼓舞的心情,通常更便于也更需要以喜剧或正剧的方式表现出来(自然,不能说今天这时代就不需要悲剧)。可见,不同的时代赋予作品以不同的色彩。当然,历史剧为现实服务,体现时代的要求,根本途径应该是通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处理有关题材,给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而不应采取其他简单化的方法。正是在这一方面,《蔡文姬》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剧作家在深入把握和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文姬归汉题材的艺术处理,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曹操,为蒙冤受屈的曹操翻案,恢复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意图。《蔡文姬》中的曹操,不是宋元以后被歪曲丑化了的那个奸诈小人,而是个有雄才大略的贤明丞相。他统一北方,平定乌桓,恢复生产,发展文化,在文治武功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赎回蔡文姬,就是剧中的曹操在兴办文化事业方面采取的一项措施。剧作通过董祀之口,赞颂曹操“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从新呈现出太平景象”。剧作还表现了曹操俭朴的生活,平易的作风,诙谐风趣的谈吐,知过能改的豪爽性格。这些都是有充分史实根据的。如果说,在旧时代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特定条件下,郭老曾在历史剧中联系现实作了某些颇具战斗性的发挥,那么,在《蔡文姬》诞生的新时代,这种方法就再也不必要而且简直是很不可取的了。作者在序中特意声明:“我没有丝毫意识,企图把蔡文姬的时代和现代联系起来。那样就是反历史主义,违背历史真实性了。”可见,作者在《蔡文姬》怎样体现时代精神方面,采取了谨严科学的态度。这正是剧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蔡文姬》的强烈时代气息还集中表现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在历史题材作品中,按照全新的观点去评价和处理民族问题,宣传兄弟民族间的团结友好,这是过去时代所难以实现的,而在今天却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我以为,郭老在这方面作了虽然不无缺点但却是成功的尝试。说它是成功的,并不是指《蔡文姬》中有意略去了原诗中若干刺激民族关系的词意,如“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之类;也不是说作品中有了“匈奴人和汉人本来就是兄弟嘛”这类话就算很好。《蔡文姬》中民族团结的精神是贯穿全剧的,它不是依靠外加的简单说教,而是依靠有血肉的人物形象及其行动来体现的。作家圆熟的艺术技巧和较高的思想水平,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作品不仅批判了“有大国主义臭味”的汉副使周近,也借单于之口批评了匈奴族去卑的某些有失民族自尊心的表现。左贤王这个兄弟民族英雄,写得浑厚有力,在过去我们的文学中,这样的形象尚属不多。而单于的塑造,尤其显出作家之高人一头。虽然整个说来单于还不是一个十分丰满的形象,但从正确表现民族关系这个角度来看,却异常出色。作家写他一方面主张汉、匈应该和平共处,甚至当误解左贤王破坏了这种关系时,盛怒之下,竟欲杀之;但另一方面又有民族气派,维护民族自尊心,责备右贤王去卑这一段,写得极有分寸,真不失为匈奴明主形象。塑造人物而要达到这种高度,作家本身必须有相当高的思想水平和较为丰富的政治生活经验,绝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作家并没有抄近路,采取简单化的回避和掩饰民族矛盾的做法,而是在历史上复杂的民族关系面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给予正确的处理,从而鲜明地体现了时代要求。
二
目前,对《蔡文姬》是有着争论的。看法的分歧,似乎集中在替曹操翻案的方法和效果上。用张艾丁同志《谈蔡文姬》
 一文中的话来说:“现在的问题是:第一,选取‘文姬归汉’这件事来替曹操翻案,是否合适?第二,从剧本上来看,是否已经达到替曹操翻案的目的?”而对于这两个根本问题,张艾丁同志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尽管他文章首尾都有几句对《蔡文姬》抽象肯定的话,但实际上通过这两个根本问题,已经达到了对全剧的根本否定。这里,我想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来跟张艾丁同志商榷。
一文中的话来说:“现在的问题是:第一,选取‘文姬归汉’这件事来替曹操翻案,是否合适?第二,从剧本上来看,是否已经达到替曹操翻案的目的?”而对于这两个根本问题,张艾丁同志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尽管他文章首尾都有几句对《蔡文姬》抽象肯定的话,但实际上通过这两个根本问题,已经达到了对全剧的根本否定。这里,我想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来跟张艾丁同志商榷。
文学作品要颂扬一个历史人物,最好自然是选取他一生中的主要功绩。譬如对于曹操,最好通过他兴屯田,平乌桓,统一北方,融合各族以及发展文化等诸方面。但是,应该看到,文学作品不同于历史科学论文,它们分别服从于艺术和科学这两套不同的规律。对于一篇替曹操翻案的科学论文来说,正面指出这些主要功业是必需的。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作家就有必要选择一些适当的有较多文学意味的事件,不能只以事件本身的历史重要性来定其取舍。有些历史事件可能很重要,但因受许多条件限制,未必宜于做创作素材。所以在表现历史人物的时候,作家完全有选择故事、选择素材的自由;作家可以正面颂扬一个历史人物,甚至表现一个伟大人物的一生始末,但也可以通过某些事件或若干片断,侧面表现一个历史人物的品格风度。批评家在这方面给作家以过多限制,显然是不适当的。我们既需要《李时珍》《宋景诗》这样一些正面表现历史人物的作品,同时也不该排斥《蔡文姬》这一类表现人物时较多地从侧面下手的作品。像张艾丁同志那样反对选取“文姬归汉”来替曹操翻案,并且找出一条理论根据:“所谓替曹操翻案,就是要通过历史上的一些典型事件来表扬曹操。”这未免机械了一些。这种理论之所以并不正确,是在于它把文学艺术与历史科学两种不同的方法混为一谈了。
退一步说,“文姬归汉”有没有典型意义呢?这也得看人们从什么地方着眼。其实,文姬归汉这件事,标志着曹操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胜利,实际意义远非要回一个蔡文姬所能包括得了的。在中国历史上,曹操是能够比较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的杰出人物;他对北方各族采取威柔并用、交欢融合的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对于进扰北部的乌桓,曹操曾在文姬归汉的前一年(建安十二年)发兵征讨。而接着对南匈奴,又采取了和好政策。文姬归汉不是孤立的事。没有曹操的文治武功和正确的民族政策作为背景,没有“两国交欢兮罢兵戈,羌胡蹈舞兮共讴歌”作为基础,蔡文姬是回不来的。由此可见,作家通过这件事,不仅表现了曹操对蔡文姬才干的赏识和发展文化的贡献,而且表现了曹操这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气概风度,这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
那么,剧本和演出的实际效果怎样?究竟达到为曹操翻案的目的没有?很多读了剧本和看了演出的同志,都认为已经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的。但是,张艾丁同志的感受竟如此异乎寻常,不免令人吃惊。在他看来,剧中曹操形象是一个残忍的“让人家骨肉分离,抱恨终生”的罪人,“不但不值得歌颂,反而觉得应该诅咒”。据说,文姬诗中的“新怨”,“正是曹操亲手造成的母子分离”。而曹操“对于亲手造成的罪恶,不仅不自谴责,反而对罪恶所产生的后果,采取了旁观、欣赏的态度——这和那亲手杀了人,却称赞那殷红的鲜血,说是美丽的;亲手放了火,却欣赏那腾空的火焰,说是伟大的,又有什么分别呢?”
文姬一家骨肉分离,这是事实,毋庸置辩。但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得出这是曹操罪恶地逼出来的结论。剧中这一点是表现得非常清楚的:文姬归汉,首先出于她自己的故国之思。早在曹操派人接她之前,她就想回汉扫墓、收集遗书,而且早就以“狐死首丘”的故事教育孩子;可见她尽管跟左贤王夫妇关系很好,却仍有浓重的民族感情。因此,她的归汉,首先出于内因;曹操派人去接,虽然对事件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然终究只是外因而已,更说不上有什么强迫成分。从开幕时起,文姬就自言自语地反复考虑:“怎么办呢?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可见事情完全取决于她本人。后来,通过单于之口,我们还听到这样异常明确的话:“曹丞相还再三嘱咐过,蔡文姬回不回去决不勉强。”如果像张艾丁同志那样把文姬内心的民族思想和母子感情的矛盾痛苦,一股脑儿推在曹操身上,认为这是曹操的不容宽恕的“罪恶”,蔡文姬泉下有知,恐怕一定会替曹操叫冤的。
需要说明,我这里并不认为剧本对文姬归汉的必要性已经表现得足够充分的了。从创作的角度看,似乎还可以把上述归汉的内因更多写一些。多写文姬对故土的怀念和归心的迫切,丝毫不会掩盖曹操赎回她的功绩,相反,倒可能更好地映照出曹操处理这件事的正确,赎回文姬的根据将会显得更充分。故国之思,异族之苦,这些原来在《胡笳十八拍》中描写得很多,如“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冰霜凛凛兮身苦寒,饥对肉酪兮不能餐”。现在郭老略去这些,不在剧中加以表现,我猜想大概是考虑到民族关系,同时也为了把蔡文姬形象写得更高一些(不计较物质生活条件)。但如果实事求是地考虑这个问题,恐怕就会觉得,古代一个青年女子孤苦伶仃地生活在异域,即使夫妇恩爱、母子团聚,悲苦哀愁其实仍是很难避免的。而且这种感情无可非议,在剧中也用不着回避。这样写,也许使文姬这个形象更令人觉得真实可信(当然,也不应该把这点写为文姬思汉的主要原因)。我甚至这样想:曹操在赎回文姬之前,一定有机会对她在匈奴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了解得比较清楚,因而对她不仅爱其才,也同情其遭遇。《悲愤诗》中写到文姬在“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之前,亦即被接回之前,早已发生过这样的事:“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曹操是完全有可能从匈奴归客那里知道文姬的详细情况的。《后汉书·董祀妻传》中所谓“曹操素与蔡邕善,痛其无嗣”,这个“痛”,可以说就是曹操了解文姬情况之后产生的同情。因此,曹操迎回文姬,不仅为了让她继承父业,协助撰修《续汉书》,同时也有对世侄女的同情怜惜在内。把这点写进去,丝毫无损于曹操的杰出,反可使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和作为通达人情的平实可亲的曹操,更为统一起来。
这是一段插叙,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蔡文姬》中曹操形象的完成,有几段情节是很重要的。特别可以提出其中的两段:一是误听周近的话,几乎错杀董祀;另一是权充月下老人撮合董蔡婚姻。前者突出了曹操性格的一面:疾恶如仇而失之偏听偏信,当机立断而偏于暴怒轻率,但他又知过能改,毕竟不失英雄风度。后者突出曹操性格的另一面:识风知趣,通情达理,平易近人,亲切热情。前一方面不免令人生畏,后一方面却又惹人喜爱。这当然远非曹操性格的全部,但的确合上了周近所说的“大家真是又爱他,又怕他”的主要之点。但对于这两段情节,张艾丁同志全予否定,认为均不足以用来表现曹操,甚至认为起了反作用。这也是令人难以同意的。
关于曹操听信周近一面之词几乎误杀董祀这一段,张艾丁同志把它跟《捉放曹》和《群英会》做了比较,断定曹操的性格不会那么“鲁莽”,因而认为写得不真实。其实,《蔡文姬》中的曹操是根本不能跟传统剧目中的曹操相比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传统剧目中的曹操是个“奸雄”,将错就错杀死吕伯奢一家的故事,尤其突出了他那种“无毒不丈夫”的本质。而《蔡文姬》中的曹操,却是个全新的形象。用《捉放曹》来反证《蔡文姬》之失真,这犹如用英尺来责备米达一样,逻辑上就站不住脚。我看《捉放曹》和《蔡文姬》,谁也用不着否定谁,都有存在的理由,来个“和平共处”好了。但要说接近历史真实,当然还该数郭老创造的曹操形象。人们所批评的“过于鲁莽”之处,其实正是真曹操性格的一部分。《武帝诔》就说曹操“怒过雷霆,喜逾春日”,可见他确有暴躁轻率的一面。如果《蔡文姬》中的曹操没有这点所谓“鲁莽”,那么偏信和改过都无从发生,新曹操形象也就没有了。
再说撮合蔡董婚姻这件事。剧中曹操自己说是“替天行道”,我们尽可以不去为此大唱赞歌,但好像也不必凭这一点说曹操“擅作威福”,甚至“感到万分愤慨”的吧。我以为,至少可肯定,曹操在这里做的是件好事,即使这婚姻是包办的,也包办得好。蔡董结婚这事肯定是喜剧,而绝不是什么“听人摆布,形同傀儡”的悲剧。以蔡董这样的至亲,从小在一起长大,相互有较深了解,又都有临危相救之恩,最后能够结合,读者和观众为之产生同情,也增加了对曹操的喜爱,这完全是正常的。可是张艾丁同志用自由恋爱的铁尺把这一切打得稀烂。固然,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这正当得无可非议;但如果不问婚姻的具体内容,一味以是否“包办”为准,因此而攻击起一千八百年前当了月下老、又兼主婚人的曹操,指之为千古罪人,这不是过分勇猛、过分危险了一些么?听说还有些读者观众,要求作家让蔡董“多接触一些,培养他们的感情”。此心可谓善矣。但以文姬这样一个名门出身、受过教育的女性,离夫别子不久,就要她跟人随意去谈恋爱,这与其说是在那里塑造文姬形象,毋宁说是糟蹋文姬形象。郭老采用现在的方法来处理,既写好了蔡文姬,也赞扬了曹操,应该说正是苦心孤诣、高人一着的地方。
拉拉杂杂说了一顿,目的无非是保卫《蔡文姬》不让它受到非分的责难而已,并没有意思证明它是完美无缺的。有些同志从有戏没有戏的角度出发,表示不像喜爱《屈原》那样喜爱这部作品,这未始没有道理。作为一个剧本,没有贯穿到底的中心矛盾,虽能以气势、以诗情胜,但终不免令人觉得单薄一些。这大概是看《蔡文姬》而感到尚不满足的最主要的原因了。
1959年7月
原载《北京文艺》1959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