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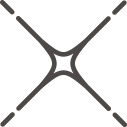
五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资本主义后备军变成社会主义的可靠同盟军,这在历史上是了不起的大事。艺术地、生动地反映这个伟大事件,乃是我国文学的光荣任务。《创业史》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因为它在反映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比同类题材的作品有了很大的进展。尽管作品第一部还只写了互助组阶段的农村的情形,却已经相当明晰和深刻地揭示出了当时整个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生活动向。处于土改和合作化运动这两个高潮之间的农村生活,表面看来似乎是波平浪静的。但是,作家却透过表面上平静细微的波纹,生动地表现了生活河流底部那种潜在的阶级斗争的激流。不仅如此,作家更以异常精细的手笔,成功地描画了潜在于广大农民心灵深处的激流——他们从资本主义后备军向社会主义可靠同盟军转变中的精神状态及其变化历程。《创业史》在这方面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
单独提出梁三老汉形象来谈,并不意味着认为其他人物都写得不好。《创业史》中绝大多数人物的艺术塑造都可以说是在水平线以上的,并且,跟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在革命农民形象的塑造方面有它独特的成就。但是,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一年来关于梁生宝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在个别文章中,这一形象被推崇到了过分的、与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的程度;相对地,梁三老汉的形象则被注意得这样少,这恐怕不能认为是文艺批评上的公正的现象。梁生宝在作品中诚然思想上最先进,但是,作品里的思想上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人,而是梁三老汉。这样说,我以为并不是降低了《创业史》的成就,而正是为了正确地肯定它的成就。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作品对土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生活面貌揭示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形象的完成。而从艺术上来说,梁三老汉也正是第一部中充分地完成了的、具有完整独立意义的形象。
梁三老汉在作品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我们知道,《创业史》里的人物,在土改后新的阶级斗争风浪中,结成了两个队伍。一个是以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为首,其中也包括了互助组的“挂名组员”梁大老汉和生禄父子俩。另一个则是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欢喜、任老四等革命农民。他们之间的斗争暂时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但双方都在暗中使着劲,正像拔河比赛一样,每个方面都用力拉引着,想叫对方服输。然而,这两队人暂时都还只占农村人口的少数。双方都在争夺群众,而不少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着。因此,梁三老汉的形象,就有了很大的意义。梁三老汉在互助合作初期所表现的那种精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这种代表性的。从许多单干农民,到郭锁这样的互助组员,一直到任老四这样的积极分子身上,我们都可以程度不同地发现不少本质上相同于梁三老汉思想的因素。梁三老汉这样的农民走向哪一方面,被哪一种力量拉引过去,就会影响着两条道路斗争的胜负。当然,梁三老汉最终走向哪一方面,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曲折,这些都不是由谁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它归根结底取决于梁三老汉本身的经济地位,取决于党对农民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贯彻。柳青同志塑造梁三老汉形象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按照生活实有的样子,充分写出了他作为个体农民在互助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的苦恼、怀疑、摇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又从环境对人物的制约关系中充分发掘和表现了梁三老汉那种由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终于要走新道路的必然性,从而相当深刻和全面地揭示了生活发展的辩证法。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即使在斗争还不十分尖锐的初期,也是一场比土地改革远为复杂、深刻得多的革命。它之所以复杂、深刻,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会遇到几千年旧制度旧传统所形成的习惯势力的抵制。而尤其困难之处,在于这种阻力大量地来自政治上作为党的基本群众的广大农民方面。梁三老汉,当土地证往墙上一钉的时候,立即跪下给毛主席像磕头;在处理女儿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受伤的女婿的婚姻关系上,他也表现得“贤明、不迟疑、识大体”,有强烈的爱国感情;可是对党领导的互助组,却在一个时期内自发地表示了反对。儿子的热心互助合作事业,竟使他一时变得心灰意懒,不吃饭也不觉得饥饿,躺在麦地里半天不想动弹,以致老鹰们竟误以为他是可以啄食的东西。为了阻止生宝借钱给互助组作进山的资金,老汉不惜对家人有意“寻衅”,竟然宣布要索钱“下馆子”“买汗褂”,而且还要把五只母鸡下的蛋“早起冲得喝,晌午炒得吃,黑间煮得吃”。这些行为,读来诚然令人失笑,但同时也隐隐显示了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和老汉身上旧习惯力量的顽固性。这种顽固性,特别由于得到了农民祖辈相传的那种“发家”理想的支撑,而更其显得严重。老汉自己对生宝所发的牢骚:“我不吃做啥?还想发家吗?发不成家哕!我也帮着你踢蹬吧!”便道破了他跟生宝这样认真赌气的全部秘密。
人们常说:农民最讲究实际。这自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就此以为可以忽视或低估理想在庄稼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那恐怕就是对农民的很大误解。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实际和自己的理想,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各自在特有的生活天地中按照特有的方式来驰骋自己的理想罢了。梁三老汉不仅有理想,而且已经热烈到了“梦寐以求”的地步:他梦见自己当了“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穿着很厚实的棉衣裳”(按老汉想,这是儿子和媳妇“出于一片孝心”特意为他老人家做的),满院子是“猪、鸡、鸭、马、牛”,“加上孩子们的吵闹声”……简直是一幅极乐图!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高度来看,这理想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于个体农民,它却是极为迷人的。正是这个理想,给了梁三老汉以力量,支持着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一日地苦熬着,不吃盐,不点灯,拼命干,死了两回牛也不消极,落个气喘病、罗锅腰也不抱怨。他失败了,连父亲留下的三间瓦房也没有保住,但却始终不曾放弃这个理想。土地改革,对于梁三老汉来说,正好给他加了油,使他这个快要熄灭了的“发家”理想重又燃烧起来。他以郭世富为榜样,相信共产党的到来为他实现理想开辟了道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小农理想的反动性(就终极意义来讲)。如果农民“务实”的一面使党有可能通过实际生活的教育引导他们走上集体道路,那么,农民热衷于发家理想的一面就只能阻碍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使他们易于接受剥削阶级的影响,跟社会主义背道而驰。曾经表示“不赞成残酷剥削”的梁三老汉,就在作了这个诚恳声明之后的第二天,竟又怂恿生宝去“取他们(任老四等)几个利息”,这就是一个极好的明证。
帮助梁三老汉彻底打破“发家”理想,在这里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做到这一点,也恰恰是最困难的。梁三老汉眼里的现实和梦想,恰好都是颠倒过来的。他那种“发家”的空想,尽管在旧社会里已经令他碰得头破血流,在新社会里也早已被根本堵塞了通路,却还是被他顽固地看成可行的现实;反过来,生宝所宣传的集体富足的新道路,却被老汉讥笑为“不着边际的空谈”。土改中,他把分得土地的现实当做梦,“老是觉着不是真的”;土改后,又把个体劳动发家致富的梦当成现实,仿佛自己真的成为“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了。现实和梦想被如此颠倒,是很可笑的,带有很大的喜剧成分。然而在喜剧背后,又隐藏着很深的悲剧内容:农民本身提不出也看不到新的社会制度和历史道路,他们的挣扎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因而不可避免地遭致悲惨的命运。柳青同志正是通过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对旧社会里农民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厚同情,并且站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度,含着微笑批评了他们的弱点,指出他们在新社会中坚持这种空想的危险的后果。梁三老汉的这些表现,形象地揭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著名论断的深刻意义。如果连梁三老汉这样贫苦、勤劳的“党的基本群众”,也会在土改后如此自发地热切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不就有力地证明了党把革命由民主主义阶段不停顿地推向社会主义阶段的必要么!
但是到这里,梁三老汉的形象还仅仅完成了一半,而且是许多作品都曾不同程度地表现过的那一半。《创业史》塑造梁三老汉之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作家精细地看到了并准确地表现了另一面:由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跟党跟社会主义有着潜在的感情联系的一面。这是更重要的一面。梁三老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毕竟是不自觉的;当他意识到取利息本身就是“剥削”这一点时,甚至自己也感到“吃惊”。梁三老汉绝不像有的评论文章所判断的那样,属于“批判形象”之列。

如前所述,梁三老汉有热切的“发家”幻想,这种幻想在终极意义上带有反动的性质。但是,任何人都必须生活在现实中,不能只是生活在幻想中。而现实生活,常常铁面无情地击碎人们的幻想,把他们从云端里拉到地面上来,逼着他们走比较现实的道路。梁三老汉在自己的幻想中是个受人尊敬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草棚院里贫困的屈辱者。他和他爹两辈子创业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血泪、辛酸的历史;“实在说,那不算创业史,那是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一翻开作品就见到的那幅惨苦的流民图,正是梁三老汉和他千千万万农民兄弟旧生活的缩影。老汉活了五十多岁,却连本来的名字也不被世人所知(人们只称他为梁三,至于“梁永清”这个“官名”,如果没有那张他和宝娃妈结婚时的“婚书”,谁也无从得知)。随着贫困而来的,更有屈辱。尽管在年龄和辈分上,老汉高出许多人,但他仍不免受人欺负。孙水嘴当众嘲弄他,有个中年人拨动他头上戴着的旧毡帽来侮辱他,甚至连自己的侄儿梁生禄都能凭富裕中农的地位气势汹汹地教训他。贫富悬殊,就使一切都颠倒过来,仿佛生禄等人成了长者,而老汉倒是他们的晚辈。这一切,作品都揭示得极为深刻。正是这一切,使他有可能清楚地知道“他自己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卢支书、生宝他们挨近着哩!”也使他在保留对环境压迫逆来顺受的习性的同时,产生了对富农姚士杰的憎恶和戒备,又“用很讨厌的眼光,盯着梁生禄家”。严酷的生活,逼得梁三老汉非变不可!而当他在媳妇坟上“想起过去的凄惶日子”流泪时,这里面就包孕了一种转变的契机。
困难的是小生产地位限制了他的眼光,使他一时看不清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光明前途,对新生活缺乏必要的信赖,常常为生宝的“不稳当”而感到“寒心”,甚至“看不惯”生宝的行动。这自然是梁三老汉作为个体农民的一种根本弱点。但是,这个弱点并不可怕。连任老四这样的积极农民,当互助组搞水稻密植时,也还流露了小农的怕经风险的动摇情绪,经过了很大一阵斗争。在这里,重要的倒不是这种一时的动摇情绪,重要的是他们最终所得到的可喜的进步。像梁三老汉这种“对于历史的一切变革都要战战兢兢”的农民,在一定时期内对新生活将信将疑,疑信参半,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他们前进得确实不快,有时甚至趑趄不前,但他们跨一步是一步,每步都很落实。正像生宝所说,“我爹他一天吃饭、干活、咄呐,三件事。咄呐是咄呐,心眼可正。今年他和咱们不一心,明年他就是咱们里头的人了”。人物的实际发展状况正是这样。梁三老汉最初是对旧道路坚信而对新道路根本怀疑的,他跟家人吵闹不休,即使听信了郭二老汉的劝说,声明“咱啥啥也不管”之后,也还会时而憋不住气,发泄自己的不满。但随着互助组活动的进展,老汉身上便逐渐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由对旧道路的自信到失去自信。“从前,梁三老汉只是在村人面前感到自卑,现在他在生宝面前也感到自卑了。”跟卢支书谈话后,他形成了一种想法:“只要给我吃上、穿上,你生宝看怎弄怎弄去!世事是你的世事!”从对旧道路失去自信到承认“世事是你的世事”,这里又进了一步:开始有了信赖新生力量的因素。到了最后,“梁三老汉,经过了买稻种的事实,进山割扫帚的事实,面对着两户退组而不动摇的事实,他对儿子服气了”。这样写是令人信服的。虽然我们知道老汉要真正克服小生产地位所赋予的弱点,还须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他的思想发展还会有波折(吸收白占魁入组一事,就超出了他的想象力);但到小说第一部结束的时候,梁三老汉“最替儿子担心害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就是说,他终究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新事物的巨大生命力,并且对它有了相当的信赖。
然而,对于社会主义,梁三老汉绝不只限于消极的适应和转变。在他身上有一种更可贵、更带积极意义的东西,这就是一种以曲折方式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的热忱。还当梁三老汉采取观望态度的时候,他对生宝互助组的命运也远非漠不关心;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关心并不亚于组内那些实心实意的组员。跟“阴阳人”梁生禄等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情况相反,梁三老汉尽管在一个时期里跟生宝及互助组行动上采取不合作态度,但他的大半颗心却在组内。他注视着组员们的一切,看出了组内潜伏着矛盾,为互助组的成败担心,因而主动向卢支书反映情况:“贫农也有不实心的,我注意看他们的容颜举动哩。”生宝进山后,农技员韩培生几次发现老汉偷偷去看互助组的“扁蒲秧”,生宝妈告诉农技员说:“土改的时候,对分得的土地,也是这神气!”此后,梁生禄和王瞎子两户退出了互助组。在这个事件的考验面前,梁三老汉也有可喜的进展:对互助组表示了更大的同情(虽然同时也保留了某些疑虑),“对梁大老汉和王瞎子没有好感”。他以默默的劳动,证明了进一步靠拢互助合作事业。如果说,梁三老汉对生宝互助组这些关心出于父子感情的话,那么它确是纯朴的真正劳动人民的父子感情。但这一切显然不能只用父子感情所解释和包括得了的。它实际上是老农身上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另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现形态。所以说“特殊”,是因为老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这种关切,常常跟他对新生事物因缺乏足够信赖而产生的过分担忧联结在一起的。而且,即使在这种对集体事业的关切中,也还打有小私有者的思想烙印。他总怕儿子“太傻”,“看不透人的心思”,而他自己所用的正是一种小私有者的逻辑。老汉的关切又常常是和赌气相伴随的。他一方面认真地生儿子的气:“你小子不喜愿对我说嘛,我也不喜愿问你!”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替互助组做了许多谁也没有要他做的事。所有这些,都使老汉的举动蒙上一层很重的喜剧色彩。(顺便说说,梁三老汉身上的喜剧色彩,在前半部中大致可以看作作家对人物的善意讽刺,后半部中则主要成为对人物的进步所做的颇带风趣的赞扬)透过这层喜剧色彩,他那种摆脱穷困生活的强烈要求和背负的沉重精神包袱,以及他特有的那种忠厚、天真、脾气倔强的个性,都得到了极为传神、极为准确的表现。
在有些反映互助合作运动的作品中,老一代贫农形象常常只被强调了保守、顽固的一面,仿佛连他们最后走上合作化道路都没有丝毫的内在要求,而完全是消极地迫于客观形势似的。这便难免会模糊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历史必然性。而《创业史》则在正面表现“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个主题方面,有了很大进展。它不仅写了年轻农民中成批的社会主义闯将,同时也写了老一代跟党走合作化道路的农民。在老一代农民中,又不止于从任老四身上发掘表现了穷庄稼人对互助合作如饥似渴的要求,而且还探索了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有一块“死肉疙瘩”的梁三老汉,毫不放松地抓住他潜藏的哪怕是些微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准确地加以表现。这样,作品不仅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当时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过程,而且向读者清楚有力地预示了未来合作化运动的磅礴气势。
这个主题方面,有了很大进展。它不仅写了年轻农民中成批的社会主义闯将,同时也写了老一代跟党走合作化道路的农民。在老一代农民中,又不止于从任老四身上发掘表现了穷庄稼人对互助合作如饥似渴的要求,而且还探索了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有一块“死肉疙瘩”的梁三老汉,毫不放松地抓住他潜藏的哪怕是些微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准确地加以表现。这样,作品不仅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当时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过程,而且向读者清楚有力地预示了未来合作化运动的磅礴气势。
《创业史》第一部只写到互助组转为初级合作社时就结束了,书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内容,都有待于以后几部来进一步发展。但在第一部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却肯定是已经独立地完成了的。虽然整个农村距离高级合作化尚有一段过程,但梁三老汉却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走完了一个历史阶段(当然不是说以后可以不再继续发展了)。从“题叙”到“结局”,梁三老汉作为老一代贫苦农民的代表,经历了恰好成为鲜明对照的两个时代、两种生活的巨大变化。这是新旧两个世界——不仅是客观世界,也包括主观世界——的巨大变化!只要回想一下作品开头两章中所写到的老汉那种生活贫困、地位屈辱、情绪抵触的状况,再对比一下结尾时老汉穿起整套新棉衣,在黄堡集上受人尊敬地、以“生活主人的神气”“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这种情景,谁能不为之深深激动。社会主义跟我国农民的那种鱼水不可分的命运,在这里得到了多么有力的证明!也许从作家的主观上说,梁三老汉并不是他所最要着力刻画的人物。但在实际上,由于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谐趣,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诚挚感情,因而它不仅深刻,而且浑厚,不仅丰满,而且坚实,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
1961年2月
原载《文学评论》1961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