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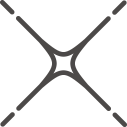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近年。实际上,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我就根据当时掌握的部分史料,已向有关方面的领导提出过。
记得那是1962年秋天,在前门饭店连续举行三天审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有十五六万字)会议上,我曾利用一次休息的机会,向当时与会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提了一个问题:“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中,已经提出了‘言文一致’、倡导‘俗语’(白话)的主张,这跟胡适三十年后的主张是一样的,我们的文学史可不可以直接从黄遵宪这里讲起呢?”林默涵摇摇头,回答得很干脆:“不合适。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从‘五四’讲起,因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划了界线:‘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以后才是新民主主义。黄遵宪那些‘言文一致’的主张,你在文学史《绪论》里简单回溯一下就可以了。”我当然只能遵照林默涵的指示去做,这就是“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绪论》里的写法。它简单提到了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提到了黄的“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语文改革主张,以及“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理想,但打头用来定性的话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产物”。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状况,一方面是政治结论框住了文学历史的实际,另一方面又跟当时学术界对文学史料的具体发掘还很不充分也有相当的关系。
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指主体由新式白话文写成,具有现代性特征并与“世界的文学”(歌德、马克思语)相沟通的最近一百二十年中国文学的历史。换句话说,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古代文学,是由于内涵着这三种特质:一是其主体由新式白话文所构成,而非由文言所主宰;二是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并且这种现代性是与深厚的民族性相交融的;三是大背景上与“世界的文学”相互交流、相互参照。理解这些根本特点,或许有助于我们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分界线之所在。
中国现代文学的开辟和建立,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的最初的起点,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史料,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就是甲午的前夕。
根据何在?我想在这里提出三个方面的史实来进行讨论。
黄遵宪早于胡适提倡“言文合一”,以俗语文学取代古语文学
首先,“五四”倡导白话文学所依据的“言文合一”(书面语与口头语相一致)说,早在黄遵宪(1848—1905)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类论述,足足早了三十年。“言文合一”这一思想,导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西各国,他们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改变古拉丁文所造成的言文分离状态,以各自的方言土语(就是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等)为基础,实现了书面语与口头语的统一。黄遵宪作为参赞自1877年派驻日本,后来又当过驻美国旧金山领事等职务,可能由多种途径得知这一思想,并用来观察、分析日本和中国的言文状况。我们如果打开《日本国志》卷三十三的《学术志二》文学条,就可读到作者记述日本文学的发展演变之后,用“外史氏曰”口吻所发的这样一段相当长的议论:
外史氏曰:文字者,语言之所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划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居今之日,读古人书,徒以父兄师长,递相授受,章而晋焉,不知其艰。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哉。
余观天下万国,文字言语之不相合者莫如日本。……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
 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乎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乎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标点符号为引者所加——严注)
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乎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乎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标点符号为引者所加——严注)
胡适在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大概只读过黄遵宪的诗而没有读过《日本国志》中这段文字,如果读了,他一定会大加引述,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这段文字所包含的见解确实很了不起。首先,黄遵宪找到了问题的根子:“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这可能是西欧各国文艺复兴后社会进步很快,国势趋于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谈到白话文学运动时曾说:“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
 可黄遵宪恰恰就在“满清时代”主张撇开古文而采用白话文,这难道不需要一点勇气么?胡适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可黄遵宪恰恰就在“满清时代”主张撇开古文而采用白话文,这难道不需要一点勇气么?胡适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可是黄遵宪恰恰就在胡适、陈独秀之前三十年,早早预言了口语若成为书面语就会让“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局面,这难道就不需要一点胆识么?黄遵宪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书面语不能死守古人定下的“文言”这种规矩,应该从今人的实际出发进行变革,让它“明白晓畅”,与口头语接近乃至合一。事实上,黄遵宪所关心的日本“文字语言之不相合”问题,也已在1885—1887年间由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发动的文学革命
可是黄遵宪恰恰就在胡适、陈独秀之前三十年,早早预言了口语若成为书面语就会让“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局面,这难道就不需要一点胆识么?黄遵宪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书面语不能死守古人定下的“文言”这种规矩,应该从今人的实际出发进行变革,让它“明白晓畅”,与口头语接近乃至合一。事实上,黄遵宪所关心的日本“文字语言之不相合”问题,也已在1885—1887年间由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发动的文学革命
 倡导以口语写文学作品,真正实行“言文一致”所解决;只是黄遵宪写定《日本国志》时,早已离开了日本,因而可能不知道罢了。应该说,黄遵宪所谓“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这种文体其实就是白话文。不过,由于黄遵宪毕竟由科举考试中举进入仕途,而且是位诗人,自己又未能通晓一两种欧洲语(只是通晓日语),这些局限终于使黄遵宪未能发动一场“白话文学运动”以践行其主张。虽然如此,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所鼓吹的“言文一致”的思想依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当清廷甲午战败,人们纷纷思考对手何以由一个小国突然变强,都希望从《日本国志》中寻找答案的时候,“言文合一”“办白话报”等措施也就成了变法维新的组成部分,声势猛然增大。只要考察不同版本就可知道:该书自1890年起就交羊城(广州)富文斋刊刻(版首有光绪十六年刻板字样),却由于请人作序或报送相关衙门等原因,直到甲午战争那年才正式发行。驻英法大使薛福成在1894年写的《序》中,已称《日本国志》为“数百年来少有”之“奇作”。到战败后第二年的改刻本印出(1897),又增补了梁启超在1896年写的《后序》。梁序对此书评价极高,称赞黄遵宪之考察深入精细:“上自道术,中及国政,下逮文辞,冥冥乎入于渊微”,令读者“知所戒备,因以为治”。可见,包括黄遵宪“言文一致”的文学主张在内,都曾引起梁启超的深思。梁启超后来在《小说丛话》中能够说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其中就有黄遵宪最初对他的启发和影响。至于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上刊发《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倡导“崇白话而废文言”,更是直接受了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的启迪,这从他提出的某些论据和论证方法亦可看出。到戊戌变法那年,《日本国志》除广州最早的富文斋刻本外,竟还有杭州浙江书局的刻印本、上海图文集成印书局的铅印本共三种版本争相印刷,到1901年又有上海的第四种版本,真可谓风行一时了。黄遵宪本人晚年的诗作,较之早年“我手写我口”突出“我”字的主张,也更有新的发展,不但视野开阔,还大量吸收俗语与民歌的成分,明白晓畅,活泼自然,又有韵味,力求朝“言文合一”的方向努力。总之,黄遵宪在中国应该变法维新方面始终是坚定的,一直到百日维新失败、被放归乡里的1899年,他还对其同乡、原驻日大使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并预言说:“三十年后,其言必验。”
倡导以口语写文学作品,真正实行“言文一致”所解决;只是黄遵宪写定《日本国志》时,早已离开了日本,因而可能不知道罢了。应该说,黄遵宪所谓“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这种文体其实就是白话文。不过,由于黄遵宪毕竟由科举考试中举进入仕途,而且是位诗人,自己又未能通晓一两种欧洲语(只是通晓日语),这些局限终于使黄遵宪未能发动一场“白话文学运动”以践行其主张。虽然如此,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所鼓吹的“言文一致”的思想依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当清廷甲午战败,人们纷纷思考对手何以由一个小国突然变强,都希望从《日本国志》中寻找答案的时候,“言文合一”“办白话报”等措施也就成了变法维新的组成部分,声势猛然增大。只要考察不同版本就可知道:该书自1890年起就交羊城(广州)富文斋刊刻(版首有光绪十六年刻板字样),却由于请人作序或报送相关衙门等原因,直到甲午战争那年才正式发行。驻英法大使薛福成在1894年写的《序》中,已称《日本国志》为“数百年来少有”之“奇作”。到战败后第二年的改刻本印出(1897),又增补了梁启超在1896年写的《后序》。梁序对此书评价极高,称赞黄遵宪之考察深入精细:“上自道术,中及国政,下逮文辞,冥冥乎入于渊微”,令读者“知所戒备,因以为治”。可见,包括黄遵宪“言文一致”的文学主张在内,都曾引起梁启超的深思。梁启超后来在《小说丛话》中能够说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其中就有黄遵宪最初对他的启发和影响。至于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上刊发《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倡导“崇白话而废文言”,更是直接受了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的启迪,这从他提出的某些论据和论证方法亦可看出。到戊戌变法那年,《日本国志》除广州最早的富文斋刻本外,竟还有杭州浙江书局的刻印本、上海图文集成印书局的铅印本共三种版本争相印刷,到1901年又有上海的第四种版本,真可谓风行一时了。黄遵宪本人晚年的诗作,较之早年“我手写我口”突出“我”字的主张,也更有新的发展,不但视野开阔,还大量吸收俗语与民歌的成分,明白晓畅,活泼自然,又有韵味,力求朝“言文合一”的方向努力。总之,黄遵宪在中国应该变法维新方面始终是坚定的,一直到百日维新失败、被放归乡里的1899年,他还对其同乡、原驻日大使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并预言说:“三十年后,其言必验。”
 虽然他自己在1905年就因病去世,早已看不到了。
虽然他自己在1905年就因病去世,早已看不到了。
黄遵宪的局限,却由同时代的另一位外交家兼文学家来突破了,此人就是陈季同。下面我们的讨论也就逐渐转向第二个方面。
陈季同向欧洲读者积极介绍中国文学,同时又在国内倡导中国文学与“世界的文学”接轨
陈季同(1852—1907)和黄遵宪不一样,他不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进入仕途的。他读的是福州船政学堂,进的是造船专业,老师是从法国聘请来的,许多教材也是法文的。他必须先读八年法语,还要学高等数学、物理、机械学、透视绘图学等理工科的课程。而为了学好法国语文,老师要求学生陆续读一些法国小说以及其他法国文学作品。出身书香门第的陈季同十六岁进船政学堂之前,已经受过良好的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的传统教育,根基相当厚实。据《福建通志》列传卷三十四记载:“时举人王葆辰为所中文案。一日,论《汉书》某事,忘其文,季同曰:‘出某传,能背诵之。’”
 可见他的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和求知欲的旺盛。西学、国学两方面条件的很好结合,就使他成为相当了不起的奇才。他先后在法国十六年,虽然身份是驻法大使馆的武官,人们称他为陈季同将军,但他又从事大量文学写作和文化研究活动,是个地道的“法国通”。他在巴黎曾不止一次地操流利的法语作学术演讲,倾倒了许多法国听众。罗曼·罗兰在1889年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可见他的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和求知欲的旺盛。西学、国学两方面条件的很好结合,就使他成为相当了不起的奇才。他先后在法国十六年,虽然身份是驻法大使馆的武官,人们称他为陈季同将军,但他又从事大量文学写作和文化研究活动,是个地道的“法国通”。他在巴黎曾不止一次地操流利的法语作学术演讲,倾倒了许多法国听众。罗曼·罗兰在1889年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在阿里昂斯法语学校的课堂上,一位中国将军——陈季同在讲演。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声音洪亮,低沉而清晰。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透过那些微笑和恭维话,我感受到的却是一颗轻蔑之心:他自觉高于我们,将法国公众视作孩童……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缩小地球两端的差距,缩小世上两个最文明的民族间的差距……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

可见陈季同法语讲演之成功。他还用法文写了七本书,有介绍中国人的戏剧的著作,有介绍中国文化和风俗的著作,有小品随笔,有《聊斋志异》法译,主要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这些书在法国销路相当好,有的还被译成意大利文、英文、德文等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七本书中竟有四本都与小说和戏剧有关,占了半数以上,可见陈季同早已突破中国传统的陈腐观念,在他的心目中小说戏剧早已是文学的正宗了。尤应重视的是,陈季同用西式叙事风格,创作了篇幅达三百多页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成为由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1890年出版)。他的学生曾朴(《孽海花》作者)曾说:“陈季同将军在法国最久,……尤其精通法国文学。他的法文著作,如《支那童话》(Contes Chinois)
 ,《黄衫客》悲剧(L'homme de la Robe Jaune)等,都很受巴黎人士的欢迎。他晚年生活费,还靠他作品的版税和剧场的酬金。”曾朴把法文版的《黄衫客传奇》称为“悲剧”,可见他确是读过这本书的。陈季同更早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国人的戏剧》(1886年),则在中西两类戏剧的比较中准确阐述了中国戏剧的特点。“作者认为中国戏剧是大众化的平民艺术,不是西方那种达官显贵附庸风雅的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中国戏剧是‘虚化’的,能给观众以极大的幻想空间,西方戏剧则较为写实。在布景上,中国戏剧非常简单,甚至没有固定的剧场,西方戏剧布景则尽力追求真实,舞台相当豪华,剧院规模很大。作者的分析触及中西戏剧中一些较本质的问题,议论切中肯綮,相当精当。”
,《黄衫客》悲剧(L'homme de la Robe Jaune)等,都很受巴黎人士的欢迎。他晚年生活费,还靠他作品的版税和剧场的酬金。”曾朴把法文版的《黄衫客传奇》称为“悲剧”,可见他确是读过这本书的。陈季同更早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国人的戏剧》(1886年),则在中西两类戏剧的比较中准确阐述了中国戏剧的特点。“作者认为中国戏剧是大众化的平民艺术,不是西方那种达官显贵附庸风雅的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中国戏剧是‘虚化’的,能给观众以极大的幻想空间,西方戏剧则较为写实。在布景上,中国戏剧非常简单,甚至没有固定的剧场,西方戏剧布景则尽力追求真实,舞台相当豪华,剧院规模很大。作者的分析触及中西戏剧中一些较本质的问题,议论切中肯綮,相当精当。”
 可以说,陈季同是中法比较文学最早的一位祖师爷。后来,陈季同回到国内还采用不同于传统戏曲而完全是西方话剧的方式,创作了剧本《英勇的爱》(1904年由东方出版社在上海出版),虽然它也由法文写成,却无疑是出自中国作家笔下的最早一部话剧作品,把中国的话剧史向前推进了好几年。陈季同所有这些写作实践活动,不但在法国和欧洲产生了影响,而且都足以改写中国的现代文学史。
可以说,陈季同是中法比较文学最早的一位祖师爷。后来,陈季同回到国内还采用不同于传统戏曲而完全是西方话剧的方式,创作了剧本《英勇的爱》(1904年由东方出版社在上海出版),虽然它也由法文写成,却无疑是出自中国作家笔下的最早一部话剧作品,把中国的话剧史向前推进了好几年。陈季同所有这些写作实践活动,不但在法国和欧洲产生了影响,而且都足以改写中国的现代文学史。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陈季同的更大贡献,在于当历史的时针仅仅指在19世纪80年代、90年代,他就已经形成或接受了“世界的文学”这样的观念。他真是超前,真是有眼光啊!下面请看他的学生曾朴在戊戌年间所记下的他老师的一段谈话:
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但科学,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
就是文学
,
也不可妄自尊大
,
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
;殊不知人家的进步,和别的学问一样的一日千里,论到文学的统系来,就没有拿我们算在数内,比日本都不如哩。我在法国最久,法国人也接触得最多,往往听到他们对中国的论调,活活把你气死。除外几个特别的:如阿培尔·娄密沙(Abel Rémusat),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字的学者,他做的《支那语言及文学论》,态度还公平;瞿亚姆·波底爱(M.Guillaume Pauthier)是崇拜中国哲学的,翻译了《四子书》(Confucius et Menfucius)和《诗经》(Ch'iking)、《老子》(Lao Tseu),他认孔孟是政治道德的哲学家,《老子》是最高理性的书。又瞿约·大西(Guillard d' Arcy),是译中国神话的(Contes Chinois);司塔尼斯拉·许连(Stanislus Julien)译了《两女才子》(Les Deux Jeune Filles Lettrée)、《玉娇李》(Les Deux Cousines);唐德雷·古尔(P. d' Entre-Colles)译了《扇坟》(Histoire de La Dame a L' éventail blanc),都是翻译中国小说的,议论是半赞赏半玩笑。其余大部分,不是轻蔑,便是厌恶。就是和中国最表同情的服尔德(Voltaire),他在十四世纪哈尔达编的《支那悲剧集》(La Tragédie Chinoise, Par le Pére du Halde)里,采取元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创造了《支那孤儿》五折悲剧(L'orphelin de la Chine),他在卷头献给李希骝公爵的书翰中,赞叹我们发明诗剧艺术的早,差不多在三千年前(此语有误,怕是误把剧中故事的年代,当作剧的年代),却怪诧我们进步的迟,至今还守着三千年前的态度。至于现代文豪佛朗士就老实不客气的谩骂了。他批评我们的小说,说:不论散文还是韵文,总归是满面礼文满腹凶恶一种可恶民族的思想;批评神话,又道:大半叫人读了不喜欢,笨重而不像真,描写悲惨,使我们觉到是一种扮鬼脸,总而言之,支那的文学是不堪的。这种话都是在报纸上公表的。我想弄成这种现状,实出于两种原因:一是我们太不注意宣传,文学的作品,译出去的很少,译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译得不好,因此生出重重隔膜;二是我们文学注重的范围,和他们不同,我们只守定诗古文词几种体格,做发抒思想情绪的正鹄,领域很狭,而他们重视的如
小说戏曲
,
我们又鄙夷不屑
,所以彼此易生误会。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
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
,嚣然自足,
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
。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
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
,
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
,
我们的重要作品
,
也须全译出去
。要免误会,
非把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改革不可
,不但成见要破除,连方式都要变换,以求一致。然要实现这两种主意的总关键,却全在乎多读他们的书。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严注)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严注)
这是陈季同长期在法国所感受到的痛彻肺腑的体会。作为中国的文学家和外交家,他付出了许多痛苦的代价,才得到这样一些极宝贵的看法。他发现,首先该责怪的是中国的“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不求进步,老是对小说戏曲这些很有生命力的文学品种“鄙夷不屑”。其次,陈季同也谴责西方一些文学家的不公平,他们没有读过几本好的中国文学作品甚至连中文都不太懂,就对中国文学说三道四,轻率粗暴地否定,真要“活活把你气死”,这同样是一种傲慢、偏见加无知。陈季同在这里进行了双重的反抗:既反抗西方某些人那种看不起中国文学、认为中国除了诗就没有文学的偏见,也反抗中国士大夫历来鄙视小说戏曲、认为它们“不登大雅之堂”的陈腐观念。陈季同所以要用法文写那么多著作,就是为了消除佛郎士这类作家对中国文学的误解。他提醒中国同行们一定要看到大时代在一日千里地飞速发展,一定要追踪“世界的文学”,参加到“世界的文学”中去,要“提倡大规模的翻译”,而且是双向的翻译:“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这样才能真正去除隔膜和避免误会,才能取得进步。正是在陈季同的传授和指点下,曾朴在后来的二三十年中才先后译出了五十多部法国文学作品,成为郁达夫所说的“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这一道大桥梁”(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事实上,当《红楼梦》经过著名翻译家李治华和他的法国夫人雅歌,再加上法国汉学家安德烈·铎尔孟,三个人合作翻译了整整二十七年(1954—1981)终于译成法文,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陈季同这篇谈话意义的深刻和正确。可以说,陈季同作为先驱者,正是在参与文学上的维新运动,并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预先扫清道路。他远远高于当时国内的文学同行,真正站到了时代的巅峰上指明着方向,引导中国文学走上与世界文学交流的轨道。稍后,伍光建、周桂笙、徐念慈、周瘦鹃的新体白话,也正是在翻译西方文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几部标志性的文学作品
这里再说第三个方面,就是当时有无标志性的文学作品可供人们研究讨论。答案是肯定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黄遵宪的“新派诗”之外,陈季同1890年在法国出版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就是很重要的一部。
 这部小说当时很受法国读者的欢迎,不久还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1890年的《法国图书年鉴》就有一段专门的文字介绍《黄衫客传奇》:“这是一本既充满想象力,又具有独特文学色彩的小说。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中国,作者以一种清晰而富于想象力的方式描绘了他的同胞的生活习俗。”《黄衫客传奇》虽然只是一部爱情题材的作品,艺术上却很具震撼力,并显露出鲜明的现代意义。早在“五四”之前三十年,它就已对家长包办儿女婚姻的旧制度以及“门当户对”等旧观念、旧习俗提出了质疑。小说通过新科状元李益与霍小玉的自主而美满的婚姻受到摧残所导致的悲剧,振聋发聩地进行了控诉,促使读者去思考。书中李益那位守寡母亲严酷专制的形象,刻画尤为深刻。两年之后的1892年,韩邦庆(1856—1894)的《海上花列传》也开始在上海《申报》附出的刊物《海上奇书》上连载。《海上花列传》可以说是首部有规模地反映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生活的作品。如果说《黄衫客传奇》借助新颖的小说结构、成功的心理分析、亲切的风俗描绘与神秘的梦幻氛围,构织了一出感人的浪漫主义爱情悲剧,控诉了专制包办婚姻的残忍;那么《海上花列传》则以逼真鲜明的城市人物、“穿插藏闪”的多头叙事与灵动传神的吴语对白,突现了“平淡而自然”(鲁迅语)的写实主义特色,显示了作者对受压迫、受欺凌的女性的真挚同情。它们各自显示了现代意义上的成就,同属晚清小说中的上乘作品。虽然甲午前后小说阅读的风气未开,人们对韩邦庆这位“不屑傍人门户”
这部小说当时很受法国读者的欢迎,不久还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1890年的《法国图书年鉴》就有一段专门的文字介绍《黄衫客传奇》:“这是一本既充满想象力,又具有独特文学色彩的小说。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中国,作者以一种清晰而富于想象力的方式描绘了他的同胞的生活习俗。”《黄衫客传奇》虽然只是一部爱情题材的作品,艺术上却很具震撼力,并显露出鲜明的现代意义。早在“五四”之前三十年,它就已对家长包办儿女婚姻的旧制度以及“门当户对”等旧观念、旧习俗提出了质疑。小说通过新科状元李益与霍小玉的自主而美满的婚姻受到摧残所导致的悲剧,振聋发聩地进行了控诉,促使读者去思考。书中李益那位守寡母亲严酷专制的形象,刻画尤为深刻。两年之后的1892年,韩邦庆(1856—1894)的《海上花列传》也开始在上海《申报》附出的刊物《海上奇书》上连载。《海上花列传》可以说是首部有规模地反映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生活的作品。如果说《黄衫客传奇》借助新颖的小说结构、成功的心理分析、亲切的风俗描绘与神秘的梦幻氛围,构织了一出感人的浪漫主义爱情悲剧,控诉了专制包办婚姻的残忍;那么《海上花列传》则以逼真鲜明的城市人物、“穿插藏闪”的多头叙事与灵动传神的吴语对白,突现了“平淡而自然”(鲁迅语)的写实主义特色,显示了作者对受压迫、受欺凌的女性的真挚同情。它们各自显示了现代意义上的成就,同属晚清小说中的上乘作品。虽然甲午前后小说阅读的风气未开,人们对韩邦庆这位“不屑傍人门户”
 、有独到见地的作家未必理解,因而《海上花》当时的市场反应只是销路平平(颠公:《懒窝随笔》)。但不久情况就有所改变。尤其到“五四”文学革命兴起之后,那时的倡导者鲁迅、刘半农、胡适,各自用自己的慧眼发现了《海上花列传》的重要价值。胡适在《〈海上花〉序》中甚至称韩邦庆这部小说为一场“文学革命”。近几年上海几位学者如栾梅健、范伯群、袁进等更纷纷撰文探讨这部小说的里程碑意义,为学界所瞩目,我个人也很赞同。所有这些,都从各方面证明:《黄衫客传奇》与《海上花列传》的意义确实属于现代。
、有独到见地的作家未必理解,因而《海上花》当时的市场反应只是销路平平(颠公:《懒窝随笔》)。但不久情况就有所改变。尤其到“五四”文学革命兴起之后,那时的倡导者鲁迅、刘半农、胡适,各自用自己的慧眼发现了《海上花列传》的重要价值。胡适在《〈海上花〉序》中甚至称韩邦庆这部小说为一场“文学革命”。近几年上海几位学者如栾梅健、范伯群、袁进等更纷纷撰文探讨这部小说的里程碑意义,为学界所瞩目,我个人也很赞同。所有这些,都从各方面证明:《黄衫客传奇》与《海上花列传》的意义确实属于现代。
如果还要继续列举标志性作品,我想用鲁迅称作“谴责小说”的《老残游记》和《孽海花》两部来讨论。刘鹗(1857—1909)的《老残游记》是文学史上较好的一部。它采用游记结构,正便于实写清末社会而又兼具象征寓意,对《海上花列传》也有所借鉴(如全书开头均由“一梦而起”)。作者阅世甚深,忧国忧民,笔致锋利,文字则含蓄简洁。在第一回自评中,刘鹗就说:“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法治。”这就是老残到处走江湖、摇串铃,行医“启蒙”“醒世”的根由。书中所写治理黄河、揭露酷吏等篇章,亦均极有见地。曾朴(1872—1935)的《孽海花》,其实是历史小说,语言已经是相当纯熟的白话,艺术上比其他被称作“谴责小说”的三本都要高出一筹。鲁迅自己就称赞它“结构工巧,文采斐然”,还夸誉其人物刻画“亦极淋漓”。用杨联芬著作中的话来说:“曾朴的《孽海花》因为深入和生动地描绘了傅彩云、金雯青这样一类历史进程中的‘俗人俗物’,描绘了他们真实的人性和他们很难用‘善’‘恶’进行衡量的道德行为,以及由他们的生活所联系起来的千姿百态的世态人生,使这部小说显得那样元气淋漓。”
 在这点上,曾朴和他的老师陈季同一样,都受了法国小说很深的影响。郁达夫则更由此推崇曾朴是“中国20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家中”“一位最大的先驱者”。可见在郁达夫的心目中,新文学的起点是在晚清。
在这点上,曾朴和他的老师陈季同一样,都受了法国小说很深的影响。郁达夫则更由此推崇曾朴是“中国20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家中”“一位最大的先驱者”。可见在郁达夫的心目中,新文学的起点是在晚清。
以上我们分别从理论主张、国际交流、创作成就三种角度,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起点时的状况。可以归结起来说,甲午前后的文学已经形成了这样三座标志性的界碑:一是文学理论上提出了以白话(俗语)取代文言的重要主张,并且付诸实践;二是开始了与“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既将外国的好作品翻译介绍进来,也将中国的好作品向西方推介出去;三是伴随着小说戏剧由边缘向中心移位,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倡导人本身已经开始具有世界性的眼光。这些事例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看起来似乎只是文学海洋上零星地浮现出的若干新的岛屿,但却预兆了文学地壳不久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动。它们不但与稍后的“诗界”“文界”“小说界”的“革命”相传承,而且与二三十年后的“五四”新文学革命相呼应,为这场大变革做着准备。尽管道路有曲折:戊戌变法被扼杀,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国家也几乎到了被瓜分、宰割的边缘,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彻底废止,留学运动的大规模兴起,清朝政府的完全被推翻,文学革命的条件也终于逐渐走向成熟。
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许多文学史实证明:如果说1890年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有了起点,那么,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个高潮,其间经过了三十年的酝酿和发展,两三代人的共同参与。黄遵宪、陈季同当然是第一代,梁启超、裘廷梁、曾朴以及其他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的伍光建、周桂笙、徐念慈、周瘦鹃等都是第二代,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沈雁冰、郑振铎、郭沫若、郁达夫等则是第三代,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可以说二代、三代的活动都参加过。他们各自创建出不少标志性的业绩,最后在诸多条件比较成熟的情况下,才取得了圆满成功。“五四”文学高潮能够在几年时间内迅速获得胜利,与许多条件都有关系,而“五四”前夕中国留学生已达到近五万人之多,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2013年9月改定
原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