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生宝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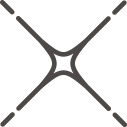
自有社会主义文学的时候起,新英雄人物的创造,便成为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课题。社会主义文学要以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这就要求作家必须用无产阶级观点去观察、反映社会生活,并且特别努力去创造真实动人的体现无产阶级美学理想的正面形象。从这点出发,我们根本反对那种向作家去提倡写“中间人物”、低估英雄人物思想教育意义的主张,反对创作上庸俗低级的“无思想性”的倾向。也是从这点出发,我们又主张对于作品中所写的新英雄形象,在热情欢迎的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给以评价,总结其成功的经验,研究其存在的弱点和问题,借以不断推进新英雄人物形象的创造工作。在这里,热情鼓励和严格要求——评论工作上对待新英雄人物形象创造的这两个不同方面,看来似乎矛盾,实际上却是必须统一而且完全可以得到统一的。片面地只取其中的一端,那就有可能使评论工作只是成为所谓“喷香水”或者“泼冷水”,都会不利于新英雄人物形象的创造,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不利于文学更好、更有成效地发挥教育人民的作用。
但是,从评论工作的实际状况看,热情鼓励和严格要求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或结合,并不是时时都能掌握得很好的。我们往往看到一些同志在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宣传了一种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在他们看来,仿佛对新英雄人物形象既需要热情,就可以不必从艺术实际出发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仿佛探讨新英雄人物创造上的某些弱点,跟热情对待是不能并存的,或者简直就是不热情的表现;仿佛人物形象的思想教育意义,可以跟艺术表现的实际成就无关。他们甚至把评价一个作品里各类人物形象的实际成就,跟在整个文学创作上提倡写哪一类人物这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例如,不久以前就有一篇题为《英雄人物的力量》
 的文章。在那里面,文章作者首先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崇高使命和革命英雄人物在现实斗争中的伟大作用”作了论述,这方面无疑是正确而必要的;可是随后即对拙作《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
的文章。在那里面,文章作者首先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崇高使命和革命英雄人物在现实斗争中的伟大作用”作了论述,这方面无疑是正确而必要的;可是随后即对拙作《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
 提出了严重的批评。据他断定:我的观点跟他论述的正确道理是有原则分歧的,我“为了强调梁三老汉这一人物的创造意义,而贬低英雄人物梁生宝”,“把英雄人物的创造和非英雄人物的创造对立起来”,“把两者的思想意义、社会价值和对现实的推动作用等量齐观”,等等。错误真是够严重的!然而该文作者在这里似乎忘记了一些本来是非常简单、非常明显的道理:第一,对一部具体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达到的客观成就的评价,跟在文学创作上提倡写哪一类人物、贬低写哪一类人物的意义,本来并不是一回事。其次,谁也不能绝对保证,在一部写了众多的人物的长篇小说里,最成功的定然是正面英雄形象而不会是其他人物形象。为什么从作品实际出发,指出梁三老汉是全书中最成功的形象,就一定是对于英雄人物的“贬低”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有趣的是,这位作者虽然口口声声不同意梁三老汉是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艺术上高出于梁生宝的形象,可是临了又改了口,承认了“在同一作品中,写先进人物有相当水平,但还不及中间性人物写得丰富生动”那种情况的存在。其实,按照他的逻辑,应该是能够坚持到底,完全用不着改口的。否则,岂非在同一篇文章中就会使自己陷于前后矛盾的境地么!?
提出了严重的批评。据他断定:我的观点跟他论述的正确道理是有原则分歧的,我“为了强调梁三老汉这一人物的创造意义,而贬低英雄人物梁生宝”,“把英雄人物的创造和非英雄人物的创造对立起来”,“把两者的思想意义、社会价值和对现实的推动作用等量齐观”,等等。错误真是够严重的!然而该文作者在这里似乎忘记了一些本来是非常简单、非常明显的道理:第一,对一部具体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达到的客观成就的评价,跟在文学创作上提倡写哪一类人物、贬低写哪一类人物的意义,本来并不是一回事。其次,谁也不能绝对保证,在一部写了众多的人物的长篇小说里,最成功的定然是正面英雄形象而不会是其他人物形象。为什么从作品实际出发,指出梁三老汉是全书中最成功的形象,就一定是对于英雄人物的“贬低”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有趣的是,这位作者虽然口口声声不同意梁三老汉是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艺术上高出于梁生宝的形象,可是临了又改了口,承认了“在同一作品中,写先进人物有相当水平,但还不及中间性人物写得丰富生动”那种情况的存在。其实,按照他的逻辑,应该是能够坚持到底,完全用不着改口的。否则,岂非在同一篇文章中就会使自己陷于前后矛盾的境地么!?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以为自己对梁生宝、梁三老汉等形象的理解、评价是没有毛病的。相反,如果具体分析研究起来,我倒是相信偏颇的地方一定不少——只是它们恐怕并不能成为判定我“贬低英雄人物”的根据罢了。至于具体说到梁生宝形象,我其实还不曾稍为系统地谈过自己的看法。虽然在上面提到的那篇专谈梁三老汉形象的文章中,我曾经表示过梁生宝形象已在一般水平线以上却还不如梁三老汉写得深厚丰满,而在另一篇叫作《〈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
 的文章中,我也说过“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某些可商榷之处,它不是《创业史》中最出色最深厚的艺术形象,但在第一部中,无疑已得到了一定的成功,并且还为以后几部中进一步的发展留下了很宽的余地……”,然而这些毕竟都是十分简略而零散的意见。现在既然已经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根据片言只语对我提出了颇为严重的批评,那么,我很愿意索性趁此机会在这里说出对这一形象的若干具体看法,诚恳地希望得到《创业史》作者和读者同志们的指正。
的文章中,我也说过“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某些可商榷之处,它不是《创业史》中最出色最深厚的艺术形象,但在第一部中,无疑已得到了一定的成功,并且还为以后几部中进一步的发展留下了很宽的余地……”,然而这些毕竟都是十分简略而零散的意见。现在既然已经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根据片言只语对我提出了颇为严重的批评,那么,我很愿意索性趁此机会在这里说出对这一形象的若干具体看法,诚恳地希望得到《创业史》作者和读者同志们的指正。
《创业史》第一部发表后,梁生宝形象跟整部作品一起,在读者和评论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可以说是热烈的反响。仅就笔者所知,两三年来,各地报刊所登载的专谈这一人物或以此为主要内容的评论文章,即不下数十篇。这种状况绝不是出于偶然的。至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作解释。从作品本身说,梁生宝形象确实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农村新人的光辉品质,不仅概括了一定的时代内容,而且艺术上也能站得起来,比同类题材作品中那些较为单薄而只有某些性格侧面(如急躁或爱钻研技术)的青年革命农民形象有了很大进展。从读者方面说,则早就迫切希望看到一部比较完整地表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作品,尤其渴望那些从“群众中涌出”的“大批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
 能够成功地得到艺术的再现。《创业史》和梁生宝形象的出现,正是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这种要求,它之受到广泛重视,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能够成功地得到艺术的再现。《创业史》和梁生宝形象的出现,正是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这种要求,它之受到广泛重视,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觉得,近两三年的不少评论文章,在对《创业史》和梁生宝形象做出正确评价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尽恰当的意见。很多评论者几乎都是只从梁生宝形象的角度来肯定《创业史》。他们认为,梁生宝形象代表了《创业史》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在第一部中已经成为异常“高大”“丰满”的典型,可以与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最成功的艺术形象(如阿Q)相媲美。有些同志还据此进而推断《创业史》已有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完满的结合”。这些评论文章差不多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程度不同地离开艺术本身(形象实际成就的高低)去抽象评价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
很难认为,这类意见是符合于作品实际的。固然,梁生宝在作品中处于思想最先进的地位。但思想上最先进并不等于艺术上最成功;人物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并不就能决定形象本身的艺术价值。艺术典型之所以为典型,不仅在于深广的社会内容,同时在于丰富的性格特征,在于宏深的思想意义和丰满的艺术形象的统一,否则它就无法根本区别于概念化的人物。而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中真正成功地把精神状态从发展中显现得那么惟妙惟肖、令人禁不住要拍案叫绝的,我以为应该是梁三老汉而不是别人。《创业史》本身的最大成就,恐怕也还是在它所独有的反映土改后农村生活和斗争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虽然它在塑造革命农民形象上比同类题材作品也有着突出的进展。至于梁生宝形象,尽管作家着力去表现他的精神面貌,而且部分章节写得相当感人(主要是这样几个部分,即:生宝买稻种和分稻种,处理同继父的关系,从山里回家时通过韩培生眼睛看到的生宝的形象,吸收白占魁入组的前前后后),但由于不少地方把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限于平面描述,因而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充分以其形象的高大丰满和内容的深厚而令人深深激动和久久不忘。跟梁三老汉,甚至跟高增福相比,梁生宝的形象倒是在不少地方显出了自己的弱点和破绽的。
毋庸置疑,作家在塑造梁生宝形象时,曾经力图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把人物写得高大。只要对农村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土改后互助合作事业的初期,实际生活中梁生宝式的新人还只是萌芽,而像他这样成熟的尤其少。从好些事件和经历看,如有些同志已经指出的,梁生宝都像作家在散文特写中所写的王家斌。然而较之这个生活原型,艺术形象的梁生宝有了许多变动和提高,政治上显然成熟和坚定得多。王家斌想买地,这点在小说中被不留痕迹地删去;生宝被处理成未婚者,这大概也是为了便于安排恋爱线索而从多方面突现其精神面貌;如此等等。除了从长安县亲身经历的生活中作这些发掘、加高外,作家还研究和利用了全国各地先后涌现的大量新人新事材料: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的王国藩“穷棒子”社,三户贫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成为五亿农民方向的王玉坤英雄合作社,……加以概括提高,突出了一些在后来历史发展中逐渐普遍成长起来的新因素、新品质,从而塑造了梁生宝这个相当理想的正面形象。这个方向不能不说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也正是在实践这个方向时,方法上发生了问题:是紧紧扣住作为先进农民的王家斌那种农民的气质,即使在加高时也不离开这个基础呢,还是可以忽视这个基础?是让人物的先进思想和行为紧紧跟本身的个性特征相结合呢,还是可以忽视其个性特征?是按照生活和艺术本身的要求,让人物的思想光辉通过活生生的行动和尖锐的矛盾冲突来展现呢,还是离开(哪怕只是某种程度上的离开)这个规律,让人物思想面貌在比较静止的状态中来显示呢?
就我读《创业史》所得的印象,作家在塑造梁生宝形象方面似乎并不是时刻都紧紧抓住人物的性格和气质特点的。为了显示人物的高大、成熟、有理想,作品中大量写了他这样的理念活动:从原则出发,由理念指导一切。但如果仔细推敲,这些理念活动又 很难说都是当时条件下人物性格的必然表现 。就以所写的生宝处理和改霞爱情关系中的一些理念活动来说,恐怕不仅不能有助于展示双方性格矛盾,实际上有损人物性格的统一。生宝本已长期热恋着改霞,早在进山以前就迫切期望跟她“揭宝”,而且他的性格又一贯稳重,并不狭隘;可是到了黄堡镇上他竟一反常态地因一句话的误会(还很难说真是误会)而立即对她冷淡(显得很狭隘),后来又在晚间因“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而再次拒绝了改霞的爱情要求。这里,经过煞费苦心的安排之后,主人公原则性强,公而忘私的品质当然是突出了,但同时,生活和性格的逻辑却模糊了,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个性“消溶到原则里”的情形也就多少出现了。尽管作家可以用梁生宝“忙得顾不上”去作他不谈恋爱的解释,但读者未尝不可以引县委杨书记对生宝打趣地说的话来回答:“把它当成副业嘛!不要专门谈恋爱嘛!哎哎,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刻板吧!我说可以公私兼顾……”
自然,爱情线索方面的弱点(如果说是弱点的话)对于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也许是无关宏旨的。作家把更多篇幅用在写梁生宝能够处处从小事情看出大意义上,这是为了显示人物思想上的成熟。他从农民争要稻种的行动中,想到“党就是根据这一点,提出互助合作道路来的吧?”从某村哥俩吵架中,立即看到了“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从进山的行动中,看出了这是“集蓄着力量,准备推翻私有财产制度”的革命;从有人说“梁生禄互助组组长没进山来,打发他叔伯兄弟领进来了”这句话,立即体会到“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头,富裕中农是受人敬重的人物”;从山中的劳动,看到了“改造农民的主要方式,恐怕就是集体劳动吧?不能等改造好了才组织起来吧?要组织起来改造吧?”从贫苦农民在山中的团结一致,体会到“这贫雇农恐怕就是乡下的领导阶级吧?要不然你在乡下哪里去找工人阶级呢?”……总之,哪怕是生活中一件极为平凡的事,梁生宝也能一眼就发现它的深刻意义,而且非常明快地把它总结提高到哲学的、理论的高度,抓得那么敏锐,总结得那么准确。这种本领,我看,简直是一般参加革命若干年的干部都很难得如此成熟、如此完整地具备的。无怪乎有的读者会觉得梁生宝的思想政治水平比区干部还高,而有的评论文章则更是称颂他“具有思想家的风貌”了。诚然,只要人们“一心一意为我们的事业奋斗,他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就和马克思、列宁相通了。他们心里想的,正是毛主席要说的和要写的话”。(这是书中县委杨书记的谈话,显然也代表了作者自己的看法。)但这段话的正确性也是有条件的,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私利心的人,就能自发地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灵敏的政治眼光与一定的理论水平,总是跟比较丰富的政治生活经验相联系的,它们只能是较长期的政治斗争的产物。梁生宝经过党几年教育,逐渐形成了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光辉品质,这从他的经历出身来看是完全可信的;然而,光辉的思想品质跟较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头脑,仍然不是一回事,尽管两者之间确也有着联系。显然,在许多地方,是作家把他自己从生活中得来的对党的思想和政策的体会(这些体会,即使以柳青同志的水平,恐怕也是经年累月地观察和消化生活之后才得到的),加到了梁生宝的身上。梁生宝某些思想活动(从内容到思维的方式)之如此细微,也证明了它们终究在气质上不完全是属于农民的东西。
应当说明,我不是说不要写人物的理念活动和政治眼光。既然理念活动在人们实际生活中必不可少,文学中反对写它将是十分荒谬的。具体到梁生宝这个未来的合作社重要领导干部身上,理念活动和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成熟都是必须加以表现的。但是,第一,理念活动不是以革命理想主义方法塑造人物的主要标志;人物要高大、有理想,并不意味着必须大量地写他的理念活动。第二,更重要的,写理念活动应该有助于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深度,它必须是个性化的,符合于人物的性格、身份、思想、文化等条件的,最好是富于动作性的。如果没有这两条,那么,本意要通过理念活动来把人物写得高大的,结果却很可能是写得苍白而显得缺少立体感了。在《创业史》里,并不乏写理念活动很成功的好例子。比方说,让高增福“带着要建立丰功伟绩的气概”,向大自然宣布:“等俺才才长大了看吧,到那时,看咱中国是啥社会!”这里所表达的理想,本来也许有点空泛,而且似乎不符合于高增福平时那种老成、沉默的个性。但作家却把这件事安排在特定的环境中:高增福因工作顺利、“心里畅快”而去喝酒,在半醉状态的“酒兴冲冲”的归途中,说了这番豪言壮语。这就令人可信地加高了人物,也突出了性格。在梁生宝方面,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写理念活动很精彩的例子。如,当生宝到郭县买稻种时,作家对于他的阶级责任感、克己奉公的思想活动除正面加以表现外,主要通过了这样的描写:
他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抱着被窝卷儿,高兴得满脸笑容,走进了一家小饭铺里。他要了五分钱的一碗汤面,喝了两碗面汤,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他打着饱嗝,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他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红布小包,又打开他妹子秀兰写过大字的一层纸,才取出那些七凑八凑起来的,用指头捅鸡屁股、锥鞋底子挣来的人民币来。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尽管饭铺的堂倌和管账先生一直嘲笑地盯他,他毫不局促,……相反,他在脑子里时刻警惕自己:出了门要拿稳,甭慌,免得差错和丢失东西。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
这是地道的梁生宝式的行动和心理状态,读来特别动人。“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这种想法发生在此情此景之下,就亲切地传达出了质朴的农民气质和鲜明的个性。另如,生宝和两个书记的一场谈话,其内容有许多是纯理论的,但却写得很生动,突现了三个人物的性格。尤其是生宝“忍不住要替他继父鸣不平”那一段,读完之后,仿佛觉得梁生宝形象一下子变得深厚和高大起来。由此可见,倒不怕人物想道理和讲道理,问题在于这些道理是否真出于有血有肉的人物心里和口里。不过这样的描写,对于梁生宝形象来说,毕竟还嫌少了些。
与上述多写理念而放松性格刻画的情况相联系,作品从矛盾冲突中去对主人公展开具体描绘也嫌不足。为了突出主人公形象的高大,作家特意安排了梁生宝少年时代的一些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生活故事,这是十分必要的。还当小伙子十几岁时,就有了自己不凡的见地,买回了一头小牛犊,并且充满自信地批评继父的保守多虑:“爹!你那是个没出息的过法!”(解放后当继父劝阻他入党时,生宝再次说了这句话,但已有着完全不同的新内容。)此其一。其二,欢喜的父亲任老三临死时硬是不肯闭上眼睛,直到从终南山里找回生宝托孤后才瞑目,于此可见年轻的生宝在老一辈农民眼中早已被信赖到了何等地步。其三,生宝幼年为富农管桃时,私下卖桃所得的铜板,他分文不取地交回给主人,这件事弄得富农惊怕地说:“啊呀!这小子,你长大做啥呀?……”作家通过这三个多少带点传奇性的故事,烘托了生宝幼年时代的良好品性和宏大志气,目的就是在人物周围布置一个光圈,为人物的发展准备好历史的根据,证明他后来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新英雄之完全可信。比起多少有点生硬地插进几个红军故事来说明梁生宝所受的革命传统教育,我以为这些地方是写得更为成功的,出色的。但是,外围的历史的交代毕竟不能代替对主人公现实行动的描绘;不仅不能代替,反而由于外围烘托的成功,对作家在形象描绘上相应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创业史》第一部中的梁生宝形象,恰恰在这方面没有很好跟上去。
按照我的也许是极为机械的理解,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在小说、戏剧领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作家在矛盾冲突——当然不是人为地故意制造出来的矛盾冲突——中写出英雄人物性格化的行动和内心生活,展示其革命理想光辉照耀下的崇高的灵魂美。离开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也就没有了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也就会失去必要的基础。少年时代故事的抒写,外围的烘托,虽然可以增染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但还不是两结合这种艺术方法的最本质的要求。英雄人物总是从生活所充满着的各种矛盾斗争中涌现出来、经受考验、让自己的品格闪现出动人的火花的。如同电流通过的电阻越大,就越能发出强烈的光和热一样,英雄人物的高大和光彩,也总是在斗争尖端才更能充分地显示的。某些日常的较为平凡一点的生活内容,对于从多方面揭示并补充、丰富人物的精神面貌来说,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但这毕竟不能代替更为主要的对生活中重大矛盾冲突的表现。梁生宝考虑处理白占魁入组问题那一章之所以读来特别动人,就因为作家让主人公在尖锐的内外冲突中,自然地表现了他那种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的革命气概。应该说,这段笔墨是异常出色的,它不仅动人地突现了人物的非凡气概,而且也集中地显示了作家的艺术魄力。完全可以料想,白占魁这种人加入互助组,将来不可能不在重要关头引出一些意外的岔子,使矛盾复杂化,逼得主人公非走上斗争尖端不可。热心的读者,在这里不能不因此而为未来的合作社领导人梁生宝担心;也正是在这里,作家为梁生宝在以后几部中的发展留下了宽阔的余地。但是,这类笔墨在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中也占得太少了。从矛盾冲突中展开具体描绘不够,成为这个形象艺术上的一个弱点。我们当然不能说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道路的代表和先锋战士,处于跟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旋涡之外;但是,作家 并没有在现有故事范围内充分利用梁生宝这种处在斗争第一线上的已有条件来展开正面描写 ,这点却是难以讳言的。当几个较为重要的战斗回合进行时,我们的主人公恰好都“另有任用”:村里搞活跃借贷,生宝出外买稻种去了;试用新法栽稻,生宝进了山;甚至搞粮食统购统销那样的大事,作家也安排生宝上县里受训去了。如果说这些写法都为了恰恰证明生宝有远见,处处能比别人早走一步,我看这是不足以服人的。在作家,这样安排也许是出于对自己主人公的爱惜;不轻易使用他,有意替他留了一手,好让他在以后几部中有发展余地。但从实际效果上看,让梁生宝这样一个在全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英雄人物,不在跟资本主义势力面对面搏斗中露锋芒(当然,面对面斗争并不意味着必须是脸红脖子粗的争吵),某些方面反不如高增福那样有声有色,这总不免令人惋惜。即使单纯从情节结构上看,也不免有姚士杰等的活动和梁生宝的活动这两条线索各不相扰、孤立发展之嫌。也许有人说,当时活跃借贷并不是生宝面前最重要的任务。那么,就看“进山”这章吧。这里只是对山里劳动生活摄下了一两个匆忙的镜头;除拴拴因偶然原因受伤外,和自然的斗争几乎被写得意外地顺利;跟书中其他出色的章节比较,这一曾被有些评论文章称为“充满诗情画意”的部分,其实却缺乏动人的生活光彩。此外,在处理跟郭振山的关系方面,亦即处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方面,梁生宝似也显得过于无力。生宝两次受过郭振山精神上的侮辱,两次都有揭开矛盾、展开斗争的机会,但是都没有展开(也许这正是作者审慎考虑了主人公年龄、身份、思想、性格后有意做出的颇有分寸的安排)。以作品所描写的生宝在各方面的成熟,比较他在郭振山面前那种几乎掉下眼泪的近于软弱的态度,显得十分不相称。或者是作家把生宝的有些理念活动写得过于成熟(这种可能性最大),或者是作家把生宝在郭振山面前写得过于软弱,或者可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能得出的结论,似乎不得不是这样。
《创业史》塑造形象时还常常插入一些抒情议论。作为作家个人风格上的一种尝试,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应该受到欢迎。但一般说来,作家主观抒情议论最好是画龙点睛式的,是以充分的客观描绘做基础的;如果使用过多,效果反而未必好。而现在所写的梁生宝,若干地方给人的感觉是客观的形象描绘尚未到达,主观的抒情赞扬却远远超过,显得不很协调。这就转过来成为一种弱点了。
把以上意见归纳起来,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也许可以说是“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三多”未必是弱点(有时还是长处),“三不足”却是艺术上的瑕疵。当然,这并不是指梁生宝形象艺术塑造的全部而言的,如前所述,这个形象也有很多写得好的地方,有成功的一面。但是,这里毕竟提出了一个需要探讨的属于文学创作如何加高人物、如何塑造新人形象的艺术方法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又是和作家生活基础有关的:作家生活根基到底丰厚到什么程度?对新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的了解和把握是否已经达到了在塑造形象时可以得心应手的地步?柳青同志长期踏实地在农村工作,有着固定的生活根据地,其积累之丰富是无可怀疑的。但从《创业史》描画人物精神状态的情形来看,作家对于各类人物了解的深度显然是并不平衡的。如果说梁三老汉这类老农是作家最能洞察肺腑因而虽然着墨不多却能入木三分、显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话,那么,梁生宝这类英雄形象虽也不乏若干生动描写、显得可敬可爱,但却总令人有墨穷气短、精神状态刻画嫌浅、欲显高大而反失之平面的感觉。这种情况毫不足怪,正说明了对新人了解和描写的不易。新人既“新”,变化复速,在生活中看到其闪光较易,真正对其性格和心灵了如指掌就较难。一百多年前的屠格涅夫,为了写好当时的新人——《父与子》中巴扎洛夫的形象,努力摸索主人公的习性爱好,特意采用为巴扎洛夫写日记的办法,每碰到一件具体事情,作家就想:这件事如果是巴扎洛夫,他会怎样对待、怎样处理呢?……如是者将近两年。屠格涅夫的事例当然是不能拿来跟我们的作家类比的。但是,它也可以使我们得到启示:旧时代作家塑造一个新人形象,尚且要从生活上和艺术上作许多艰苦的准备;处于今天瞬息万变的社会主义时代,要想成功地创造飞速成长中的新英雄人物,虽然有着马克思主义为指路明灯,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客观条件要求作家从生活上扎下特别深厚的根子,对英雄人物灵魂、脾性、气质的把握真正达到异常透彻的程度。《创业史》的作者已经努力这样去做了,因而取得了同类题材作品所没有取得的成绩;但又因为作者所做到的毕竟跟形象塑造所要求的还有距离,故而又显出了某些弱点。梁生宝形象的出现对我们文学创作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它在艺术塑造上的成就和不足,我以为,都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1963年2月
原载《文学评论》1963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