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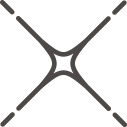
有关梁生宝形象艺术塑造问题的讨论,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讨论是有意义的。新英雄人物的创造,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它直接关系到文学能否更好地完成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促进人们思想革命化的使命。在文艺批评上,就这些年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比较成功的新英雄形象进行研究,从艺术塑造的得失中总结经验,无疑会对今后创造更多更成功的新英雄人物形象有促进作用。梁生宝是近几年长篇小说中出现的有显著成就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具体探讨有关它的一些经验,更能直接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新人形象的创造。
关于梁生宝形象的争议,应当说并不是去年才开始的。早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之后不久,人们在一致赞赏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互助合作初期农村的阶级斗争、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包括革命农民)形象的同时,已经对梁生宝形象在书中是不是最丰满、最出色以及在艺术塑造方面是否还有某些问题值得探讨,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在当时发表的关于《创业史》的评论文章中也有反映。一些评论者认为梁生宝是异常高大、丰满的典型,代表了《创业史》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已成为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的典范。也有一些评论者主要赞扬作品通过不同阶层人物形象的塑造所达到的反映农村生活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他们肯定梁生宝形象,重视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但并不把它看作是第一部中艺术描写上最成功的。尽管并未出现形诸笔墨的正面论辩,但这些情况说明,从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角度出发,读者评论者已经得出了不完全相同的估价。
我去年为了答复有的同志批评而写的《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正是就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所表示的“若干具体看法”。文章意在说明,梁生宝形象一方面在第一部中已经获得相当的成功,比之其他作品里的革命农民形象更有突出的进展,另一方面在艺术塑造的具体方法上也还有某些不足之处(即所谓“三不足”
 ),尚未成为书中最成功、最深厚的艺术形象。这篇文章是与我过去写的两篇有关《创业史》的评论(特别是《〈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一文)相承接的,又受了所要说明的课题本身(梁生宝在书中为什么不算艺术上最成功)的影响,因此以较多的篇幅论证了后一方面,而对前一方面,即梁生宝形象的成就和意义方面,则未能给予充分估计和论述;这可以说是文章结构和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缺陷。此外,文中一些地方意思说得不够清楚,有引起误解的可能;有些句子和措辞欠斟酌,分寸不够准确;这些也都是文章的缺点。至于我的一些具体论点是否正确或者正确到什么程度,当然更是完全可以讨论的。我自己就说过:“如果具体分析研究起来,我倒是相信偏颇的地方一定不少。”我衷心欢迎不同意见的商讨。柳青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撰文对我进行批评,有的还联系到我过去写的那两篇文章一起作了分析,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并没有正确理解我的原意,但他们所做的正面论述和说明,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来比较全面地考虑问题,包含了不少正确的见解。我相信,学术讨论的双方如果都从关心和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这个共同立场出发,并且能够实事求是,面向真理,平心静气,以理服人,不去曲解对方的意见,不把不同的问题搅混起来,那总是越讨论越有好处,意见也会越来越接近的。为使目前已经展开的讨论更为深入,我趁最近工作刚刚告一段落之暇,写下这篇文字,想从艺术方法的角度说明自己对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的一些看法,以补充我原先文章的未尽之意,改正原先说得不清楚和不妥当之处,也算是对批评文章的一部分答复。匆匆写成,限于自己目前的认识水平,错误一定很多,切望进一步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尚未成为书中最成功、最深厚的艺术形象。这篇文章是与我过去写的两篇有关《创业史》的评论(特别是《〈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一文)相承接的,又受了所要说明的课题本身(梁生宝在书中为什么不算艺术上最成功)的影响,因此以较多的篇幅论证了后一方面,而对前一方面,即梁生宝形象的成就和意义方面,则未能给予充分估计和论述;这可以说是文章结构和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缺陷。此外,文中一些地方意思说得不够清楚,有引起误解的可能;有些句子和措辞欠斟酌,分寸不够准确;这些也都是文章的缺点。至于我的一些具体论点是否正确或者正确到什么程度,当然更是完全可以讨论的。我自己就说过:“如果具体分析研究起来,我倒是相信偏颇的地方一定不少。”我衷心欢迎不同意见的商讨。柳青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撰文对我进行批评,有的还联系到我过去写的那两篇文章一起作了分析,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并没有正确理解我的原意,但他们所做的正面论述和说明,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来比较全面地考虑问题,包含了不少正确的见解。我相信,学术讨论的双方如果都从关心和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这个共同立场出发,并且能够实事求是,面向真理,平心静气,以理服人,不去曲解对方的意见,不把不同的问题搅混起来,那总是越讨论越有好处,意见也会越来越接近的。为使目前已经展开的讨论更为深入,我趁最近工作刚刚告一段落之暇,写下这篇文字,想从艺术方法的角度说明自己对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的一些看法,以补充我原先文章的未尽之意,改正原先说得不清楚和不妥当之处,也算是对批评文章的一部分答复。匆匆写成,限于自己目前的认识水平,错误一定很多,切望进一步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概括、集中、提炼和提高
目前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上的许多争议,归结起来,大多同如何理解以及在实践中如何把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有关。这是不奇怪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不仅在理论上提出的时间较短,而且本身就是对过去时代各种艺术方法的一个大革新。它要求发扬历史上一切进步方法之长而弃其短,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基础上使现实和理想得到统一,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得到统一,把艺术方法推向前所未有的新的境界。这在艺术实践上自然会面临一些前所未遇的课题,在理论上也可能产生对某些具体问题理解的差异。当前围绕着新英雄人物创造而提出的要不要在生活基础上提高和如何正确地提高(亦即我在《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中所说的“方向”和“方法”),便可以说是这许多新的课题和问题中两个重要的方面。
创造新英雄人物形象要不要在现实基础上加以提高?对这个问题,我以为必须给予完全肯定的回答。社会主义文学的使命和两结合的艺术方法,都要求我们塑造的新英雄人物能够强烈地体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给读者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巨大鼓舞,这就不仅需要对生活素材做概括、集中、提炼,而且需要循着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去提高,充分显示出人物的理想主义光彩。这完全不是什么“拔高”。事实上,历来一些优秀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也都是经过了某种提高的,且不说《西游记》这部浪漫主义作品里的孙悟空形象,即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也还有不同阶级的理想色彩相当明显的武松、李逵、诸葛亮等曾经脍炙人口的英雄形象。今天要表现我们这个英雄的时代和时代的英雄,而且有过去时代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想的照耀,为什么不可以提高并且在这一方面做得更好呢?仅仅凭借生活中已经看到的而排除可能出现、可能看到的,必然会大大限制作家的艺术视野,捆住作家艺术想象的翅膀,影响作品更充分地反映今天高昂的时代精神,这对艺术创作来说无论如何是很大的缺陷。只是根据已有的事物来概括、集中、提炼,一般现实主义者也能做到。两结合之所以为两结合,之所以高出于历史上一切艺术方法,就在于它以新世界观为基础所要求的典型化过程不仅有对生活素材的概括、集中、提炼,而且有提高和赋予理想色彩,就在于它不仅有革命现实主义,而且有革命浪漫主义。梁生宝之所以为梁生宝,之所以比同类题材作品中的革命农民形象获得很大的进展,照我想来,也在于作家不仅以敏锐的眼光发现和概括了当时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就是说他观察、研究了王家斌这样的先进人物,概括、集中了其他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许多先进人物和事迹),而且还用时代理想照耀了自己的人物,加以提高,从而使形象更有光彩,具有了比较深广的内容。梁生宝身上体现的艰苦奋斗、踏实苦干的精神,使我们不仅联想起当年领导“穷棒子”们“从山上取来”大批生产资料的王国藩,也联想起今天大寨的陈永贵和南柳的周明山,联想起难以数计的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把困难踩在脚下终于战胜了它、做出了惊天动地事业的英雄人民。如果作家不理解毛主席在讲到王国藩合作社时所说“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的意义,不在梁生宝形象塑造过程中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使人物先进的精神面貌得到充分发掘和提高,恐怕是很难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的。我在《〈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一文中曾说:包括梁生宝形象在内的“《创业史》这些成就,是作者在思想高度、生活深度和艺术能力几方面得到较好的结合的结果。……作者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对党的理论政策所做的刻苦钻研,更大大有助于思想水平的提高,保证了作者具有洞察生活本质并展望未来的眼力。……作者虽然深入到一个‘点’,但视野却是开阔的,在创作中,能充分吸取全国各地发掘出来的典型材料,加以集中概括和提高,使之转化为有血有肉的形象”。这些话正是对作家运用两结合的艺术方法所做的肯定。虽然我们有时觉得梁生宝形象从自身行动的具体描绘中来显示的“穷棒子”精神还不够充分、不够强烈,但这个形象已经获得的成功方面,有力地证明了通过英雄人物来表现时代精神的必要,证明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的强大生命力。
的意义,不在梁生宝形象塑造过程中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使人物先进的精神面貌得到充分发掘和提高,恐怕是很难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的。我在《〈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一文中曾说:包括梁生宝形象在内的“《创业史》这些成就,是作者在思想高度、生活深度和艺术能力几方面得到较好的结合的结果。……作者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对党的理论政策所做的刻苦钻研,更大大有助于思想水平的提高,保证了作者具有洞察生活本质并展望未来的眼力。……作者虽然深入到一个‘点’,但视野却是开阔的,在创作中,能充分吸取全国各地发掘出来的典型材料,加以集中概括和提高,使之转化为有血有肉的形象”。这些话正是对作家运用两结合的艺术方法所做的肯定。虽然我们有时觉得梁生宝形象从自身行动的具体描绘中来显示的“穷棒子”精神还不够充分、不够强烈,但这个形象已经获得的成功方面,有力地证明了通过英雄人物来表现时代精神的必要,证明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的强大生命力。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不难分辨某些生活素材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例如,王家斌曾有过想买地的念头,这无论从革命现实主义的概括、集中、提炼的角度,还是从革命浪漫主义的提高和赋予理想光彩的角度来考虑,都是可以不写的;具体到《创业史》所写的梁生宝这样的人物身上,写他想买地更会破坏人物性格的统一。艺术不能照抄生活,艺术形象不应照搬真人真事。我是完全赞同柳青同志现在的处理方式的。在《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中,我这样说:
毋庸置疑,作家在塑造梁生宝形象时,曾经力图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把人物写得高大。只要对农村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土改后互助合作事业的初期,实际生活中梁生宝式的新人还只是萌芽,而像他这样成熟的尤其少。从好些事件和经历看,如有些同志已经指出的,梁生宝都像作家在散文特写中所写的王家斌。然而较之这个生活原型,艺术形象的梁生宝有了许多变动和提高,政治上显然成熟和坚定得多。王家斌想买地,这点在小说中被不留痕迹地删去;生宝被处理成未婚者,这大概也是为了便于安排恋爱线索而从多方面突现其精神面貌;如此等等。除了从长安县亲身经历的生活中作这些发掘、加高外,作家还研究和利用了全国各地先后涌现的大量新人新事材料: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的王国藩“穷棒子”社,三户贫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成为五亿农民方向的王玉坤英雄合作社,……加以概括提高,突出了一些在后来历史发展中逐渐普遍成长起来的新因素、新品质,从而塑造了梁生宝这个相当理想的正面形象。这个方向不能不说是完全正确的。
梁生宝没有小私有者思想而能令人信服、而能“不留痕迹”,他的思想面貌从多方面被表现出来,这些在我看来正是作家写得正确、安排得好的地方。这里的“删”字确实用得不当,但整段文字的意思十分明白:乃是对作家做法和意图的肯定。令人吃惊的是,批评我的同志竟然可以不顾这整段文字的精神,只从中孤零零地摘取一句半句话,根据自己不正确的理解,就得出同我原意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把许多批评建筑在认为我要求作家写梁生宝想买地这个武断之上,硬说我主张照抄生活,反对人物形象的提高,反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特别欣赏”农民想买地的自发思想和落后面,鼓吹写人物“精神品质上的缺陷”,表现了“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的习惯偏见”,等等。甚至还因为我说过“只要对农村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土改后互助合作事业的初期,实际生活中梁生宝式的新人还只是萌芽,而像他这样成熟的尤其少”,就推断出我把梁生宝形象看作根本“不真实”的结论。这样一种根据虚构出来的分歧而作的成段的批评,实在很难说有多少积极意义。
真正对人物形象的提高有分歧意见的,倒是在批评我的一些同志当中。例如李士文同志在他那篇《关于梁生宝的性格特征》
 的文章里,就认为作家只要把握住生活中已经看到的新事物就足够了。他说:“作家的生活基础,可以使他在创造理想的农民英雄形象的时候,不用去‘加高’,而只需要提炼、概括、集中。”李士文同志也许仅仅是不赞成我所说的“提高”或“加高”这个词语的用法。但只强调提炼、概括、集中,而不同时强调按照生活可能性更充分地体现时代理想,这实际上是说梁生宝形象的塑造,只要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就够了,不必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种说法,我以为理论上既不对头,于创作实际恐怕也未必符合。
的文章里,就认为作家只要把握住生活中已经看到的新事物就足够了。他说:“作家的生活基础,可以使他在创造理想的农民英雄形象的时候,不用去‘加高’,而只需要提炼、概括、集中。”李士文同志也许仅仅是不赞成我所说的“提高”或“加高”这个词语的用法。但只强调提炼、概括、集中,而不同时强调按照生活可能性更充分地体现时代理想,这实际上是说梁生宝形象的塑造,只要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就够了,不必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种说法,我以为理论上既不对头,于创作实际恐怕也未必符合。
提高而不脱离基础
新英雄人物的塑造可以提高和需要提高,这自然并不是说提高可以无规律地随意进行。主观任意、随心所欲的“提高”,是会破坏艺术的规律,招致创作的失败的。包括梁生宝形象在内的许多新英雄人物塑造的成功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提高,而又不脱离基础,这是不容忽视的规律。扩大开来说,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个艺术方法所包含的两个对立面之中,革命浪漫主义的主导不应脱离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
那么,所谓“不脱离基础”,又该作怎样的理解呢?我以为,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人物形象的提高不违反生活可能性。也就是要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作品描写的“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不过仅仅这一点还不够。因此,第二,提高必须在广泛概括生活原型及其同类人的基础上,严格遵循人物思想性格的逻辑,不但符合人物的气质、个性,而且成为性格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达到“非如此不可”的地步。这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更积极、更进一层的要求。作家只有充分熟悉生活中和自己要写的作品中的人物,心贴心地了解他们,确切地把握人物的内在特征,甚至能够准确无误地测知人物在各种不同条件下会产生的各种特有的哪怕是极为微细的反应——一句话,作家只有具备深厚扎实的生活底子,才能胜任愉快地完成加高人物的任务,使形象真正焕发出理想主义的光彩。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是和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度相关联的。
。不过仅仅这一点还不够。因此,第二,提高必须在广泛概括生活原型及其同类人的基础上,严格遵循人物思想性格的逻辑,不但符合人物的气质、个性,而且成为性格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达到“非如此不可”的地步。这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更积极、更进一层的要求。作家只有充分熟悉生活中和自己要写的作品中的人物,心贴心地了解他们,确切地把握人物的内在特征,甚至能够准确无误地测知人物在各种不同条件下会产生的各种特有的哪怕是极为微细的反应——一句话,作家只有具备深厚扎实的生活底子,才能胜任愉快地完成加高人物的任务,使形象真正焕发出理想主义的光彩。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是和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度相关联的。
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形象的途径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作家可以只用一个人为模特儿,也可以“杂取种种人”。但生活原型之所以为生活原型,同艺术形象总得有某些带根本性的共同点,至少他们都属于同一类人,例如,都是工人,或者都是农民,或者都是先进工人,或者都是革命农民,等等。不大可能原型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据以创造出的艺术形象却是个先进工人;或者艺术形象是个先进农民,而原型却既有工人,也有知识分子。把不属同一类的人硬拉扯在一起,结果恐怕只会弄出工不工,农不农,四不像的角色。不能把鲁迅所说的“杂取种种人”误解为可以使生活原型跨许多类,可以从许多不同类的人身上东取一点,西取一点地拼凑。“杂取种种人”,主要意思就是高尔基说过多次的:把“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身上”的特点分别“综合在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身上”
 ,这是以同类人为条件的。有时,作家也可能从不同类的人那里移用某点东西,例如鲁迅写阿Q,据说借用过一个败落的大家子弟桐少爷的“恋爱悲剧”;但这仅仅是在某一情节或细节上的借用(而且借用时要注意贴合于人物的身份、气质、性格),并不意味着桐少爷就成了劳动农民阿Q的原型。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作家在生活中观察了许多同类人物,尚未孕育出形象,后来只是由于一个偶然遇到的人物或事件的启发,使形象一下子到了呼之即出的地步。这个偶然遇到的人物是否就可算艺术形象的原型了呢?确切一点说,我以为也还只是触媒或引动作家灵感的契机,并不就是原型。
,这是以同类人为条件的。有时,作家也可能从不同类的人那里移用某点东西,例如鲁迅写阿Q,据说借用过一个败落的大家子弟桐少爷的“恋爱悲剧”;但这仅仅是在某一情节或细节上的借用(而且借用时要注意贴合于人物的身份、气质、性格),并不意味着桐少爷就成了劳动农民阿Q的原型。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作家在生活中观察了许多同类人物,尚未孕育出形象,后来只是由于一个偶然遇到的人物或事件的启发,使形象一下子到了呼之即出的地步。这个偶然遇到的人物是否就可算艺术形象的原型了呢?确切一点说,我以为也还只是触媒或引动作家灵感的契机,并不就是原型。
艺术形象既然要以生活原型所属的一类人为基础,作家在生活和创作的过程中,除了注意这类人的思想和性格特点之外,对他们由于特有的生活环境、职业和文化等条件所长期形成的某些素质——我称之为气质特点,也就不能放松。无论是概括、集中、提炼,还是提高,都需要准确地把握这种气质特点,这是创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创业史》不少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也是和作家对各类人物气质把握得准、把握得深有关系的)。作家可以改造生活素材,可以更动某个生活原型的事件、情节而从其他原型身上或经过艺术想象加以补充,可以使人物的光辉品质更集中、更鲜明,觉悟更高,可以承取原型的一些性格侧面而改变其另一些性格侧面,但在气质特点方面仍须不脱离这类人的基础,也就是说,不能写得不像这类人。我在《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中所说的“紧紧扣住作为先进农民的王家斌那种农民的气质,即使加高时也不离开这个基础”,便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一点意见。这里说得诚然不够清楚。所谓“作为先进农民的王家斌那种农民的气质”,其实当然不局限于王家斌个人,而是指王家斌、王国藩、王玉坤……这类互助合作初期就涌现出来的有社会主义觉悟、坚决走集体化道路的先进农民所共有的东西。它是怎么也不能跟想买地的“自发思想”牵扯起来甚至等同起来的(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把“气质”和“自发思想”联系在一起,从我的文章中也根本找不出这种痕迹)。在《创业史》第一部中,柳青同志也曾多次使用过“气质”这个词,例如初版第121页写冯有万:“当到他懂事的年龄,这‘恨’已经渗入他的气质,变成暴躁的性格了。”第135页写一群贫苦农民:“尽管父母的血液和童年的环境,给了他们不同的气质和性格,但贫穷给了他们同一个思想、感情和气度。”这些地方所用的“气质”一词,虽然和我所用的含义有点不同,意思也是指某种心理学上的素质。为什么这个词在其他同志的著作中可以用,而一到我的文章中,就忽然变成了鼓吹“想买地”之类错误思想的同义语了呢?这里根据的不知是一种什么逻辑!何况在我表示赞赏而举出的体现了“质朴的农民气质”的例子中,就包括了梁生宝的“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这类跟自发思想绝无共同之处的想法。批评我的一些同志如果仔细阅读全文,应该是不难发现自己的误解或曲解的。至于梁生宝是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点谁都不怀疑;提出先进农民的“气质”问题并不跟这点抵触,它丝毫不排斥或者降低梁生宝无产阶级的先进品质。道理很简单:生活里没有抽象的无产阶级战士,每个无产阶级战士都是具体的,他或者是工人出身,或者是农民出身,或者是知识分子出身;出身以及经历不同,就使同样是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会有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语言习惯,不同的心理特点,虽然他们作为无产阶级战士首先具有共同的思想品质。比方说,在我们周围的一些参加革命工作较久的同志中间,农民出身的就较多地显示出他们特有的那种淳厚朴实,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不太一样,而工人出身的又带有自己的某些特点。革命较久的一些同志尚且会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表现出这种由于出身不同而具有的不同气质,那么,对于梁生宝这个不脱产的互助组长,提出扣紧先进农民的朴实“气质”的要求恐怕就未必是不妥当的吧!事实上,梁生宝形象之所以相当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作家写这个先进战士的主要方面时并没有脱离他农民的身份和气质,而且有时是深厚地表现出了这种气质的。无论是生宝到郭县买稻种,还是处理与继父的关系,或者对待郭振山与梁大老汉的若干具体情节和细节,以及最后处理白占魁入组问题,都写得颇为出色,使人物那种在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可贵品质、高度觉悟和劳动农民的淳厚气质交融渗合,力透纸背。但是,并不是整个形象在这方面都成功。比方,说解放初期的梁生宝具有“关于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初版第332页),恐怕就不能算是对人物身份、思想和气质的准确把握。和出色的描写相比,梁生宝有一些内心活动写得较为逊色,在心理状态、思维方式方面使人有一般化的感觉,显得缺少气质、性格的深度;有些思维活动所表现的气质特点,则似与韩培生这类农村知识青年尚未明显区别开来。现在且抄一段文字:
人都有爱美之心,追求美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
但生宝心里有两个念头在互相矛盾。有时候他想:改霞人样俊,心性也好,他一定要争取和她成亲。并且,从她看他的表情和眼神判断,他是有把握的。最大的阻碍是改霞她妈的顽固。但这只要他俩相情愿,也不是大的问题。有时候他又想:“算了吧!人家上了三年级啦,恐怕这阵心大了,眼高了。咱庄稼人,本本分分,托人在什么村里瞅个对象,简简单单结个亲算了。”他想:这样更实际些。自己负起了互助组搞丰产的责任,哪里还有空空谈恋爱呢?他这样想的近因,是那天改霞在漉河桥和他说话,不象从前那么热情,脚拨弄着路上的小石头块,心里恐怕有了其他的想法吧?脸上有些捉摸不定的恍惚神情。再没比恋爱的青年人敏感了,对方一丝一毫的变化,都能感受出来。
但改霞白嫩的脸盘,那双扑扇扑扇会说话的大眼睛,总使生宝恋恋难忘。她的俊秀的小手,早先给他坚硬的手掌里,留下了柔软和温热的感觉,总是一再从记忆里,回到他手掌的皮肤上来,怂恿他把她的心夺取过来。(初版第117页)
同样是“爱美”,其实各种人所爱的具体内容和想法是并不一样的。因此,现在这里的有些写法,即使单从叙述语调上说,也多少使人感到与梁生宝这种朴实的青年农民不太调谐。(梁生宝对女方的手有些微妙奇怪的想法,这在1964年《收获》第一期上发表的《梁生宝和徐改霞》里,也有描写。例如他因为看到女互助组长刘淑良的经常劳动的“大手”像男人一样,就“在心理上引起别扭的感觉,虽然他明知这是从小劳动的结果”。梁生宝这种审美观念,简直比继父梁三还要落后。)其次,胸襟比较开阔的主人公内心何以产生如此细微褊狭的疑虑,也不很容易理解。“人家上了三年级啦,恐怕这阵心大了,眼高了”——对改霞的这种怀疑,在第88页上也提到过。但产生这种念头究竟有什么客观根据?是因为改霞在他面前已经有了某些骄傲的表现,还是纯粹出于梁生宝的主观多心?要知道,改霞上的只是村里初小(而不是初中)三年级,比生宝妹子秀兰还低一级呢!她如果在这方面要向没有脱掉半文盲帽子的梁生宝骄傲,未必有多少“资本”(何况改霞丝毫没有这种想法)。生宝通过自己的观察(第103页)和妹子秀兰的告诉(第116页),是应该能够判断改霞对自己有感情的。那么,为什么还会从她“脚拨弄着路上的小石头块”之类的动作,就推断她“心里恐怕有了其他的想法”呢?恋爱期间的青年人诚然“敏感”,但这样来写,恐怕又把人物的气质弄得过敏以至狭隘、纤细了一点吧!(顺便说说,我并不像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非得让生宝同改霞成婚才满意;恰恰相反,我倒觉得这两人从思想性格上看是配不到一起的。作家完全有理由安排一个让两人分手的结局。问题仅仅在于情节的发展必须写得充分令人信服。)
把握住人物气质,实际上是把握人物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家对人物熟悉的程度如何,气质把握得准不准,不仅关系到各类人物写得像不像,而且影响到人物本身表现得深不深。梁生宝形象的成功和某些不足,正好都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表现人物的高度觉悟和理想
比起一些同类题材的作品来,《创业史》在正面表现农村革命力量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作者一方面注意从互助合作初期广大贫苦农民身上充分发掘了哪怕是极为潜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另一方面又注意写出他们当中的先进代表人物(如梁生宝、高增福等)怎样在党的教育下得到成长。这两方面汇合特别是后一方面发展的结果,就使作品在第一部中已能相当令人信服地预示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磅礴气势。
作为解放后出现的一个新人,梁生宝之所以能够走上革命道路,除了自己特定的出身经历之外,决定性的因素是党的教育指引。梁生宝努力吸取党的思想,并且自觉地把它化为行动、化为血肉,这里表现了我们时代许多新人的共同特点和趋向。雷锋这样的英雄最光辉之处就在于努力吸取毛泽东思想并付诸实践,身体力行。梁生宝懂得互助合作意义后踏踏实实地为之全力奋斗,这也令人感动。作品正该把新人这种化党的思想为自身血肉的各自带有特点的过程写出来,而且写得生动,写得有强烈的感染力量。这是一个艺术借鉴还不很多的崭新的课题。《创业史》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包括成功的和不算成功的经验在内,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值得我们思考。
人们的思想,包括品质和思想水平两方面。一个人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坚决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奋斗,大公无私,为群众谋利益而奋不顾身,这些都显示了思想品质的光辉。通常说的“觉悟”,就是指这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人懂得革命、建设的理论,掌握党的思想、政策,能够运用这些去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这些就是通常说的较高的思想水平。思想品质和思想水平这两个方面是有联系的:品质好、觉悟高,一般都建立在懂得一定的革命道理(哪怕只是初步的道理)的基础上;而好的思想品质(由于摒除了个人主义的杂质)又反过来使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党的思想、政策,能够较快地提高自己的水平。但同时,这两方面又是有区别的:具有好的品质的人有时受了种种限制,不一定都能相应地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因为这种水平归根结底是要取决于政治生活的锻炼,政治理论的学习和斗争经验的。冯健男同志所不耐烦地认为“费解得很”“很难说得清”
 的道理,其实是并不“费解”而能够“说得清”的。
的道理,其实是并不“费解”而能够“说得清”的。
注意思想品质和思想水平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在实际创作中是有意义的。文学作品的基本描写点是在人物的思想品质方面,虽然为了真实地表现各种人物(特别是各级领导者),思想水平方面同样也必须生动地写出来。幼时读《三国演义》,对诸葛亮超人的才能和出众的智慧虽也着实钦佩,但真正感动自己的还是他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今天读《红岩》,固然为许云峰、齐晓轩等出色的领导才能、狱中斗争的高度机智以及有关的曲折情节所深深吸引,不过强烈地激动了自己,读着使我流泪并且久久不能平静的,还是那些生动地表现了英雄们共产主义光辉品质的篇章(他们的才能、机智也都和光辉品质紧密联系,甚至成为这种品质的闪光)。梁生宝也是这样。这个形象写得真正动人之处,主要不在思想水平之高,而是在一些比较深入地通过人物自身行动显示了可贵的政治思想品质的地方。也就是我在《〈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一文中所说的:“作者在一个外表上质朴淳厚的青年农民血管里,灌注着十分坚定刚毅的共产主义者的血液。他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不平凡。购买和分配稻种时那种克己奉公,组织领导贫苦农民向山取宝的那种巨大魄力,对继父和拴拴耐心帮助过程中表现的那种至诚感情,考虑处理白占魁入组问题上那种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的革命气概,所有这些,无不异常感人而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是的,文学作品的奥秘和作用就在这里:它通过人物思想品性、道德面貌、精神境界的具体描绘和揭示(而不是通过其他途径),深深地影响着读者的思想感情。毛主席在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感人至深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时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段话曾经教育过多少人,给过多少人以鼓舞和力量!它也能给文艺创作问题以深刻启示,这就是:人物形象的高大和感人主要不在是否具有较高的认识水平和发现生活中新道理的很强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作品自然需要创造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其中包括思想水平高、能力强的英雄形象,但作品只有努力深刻地展示人物的光辉品质,才能真正完成用共产主义精神有力地教育人民的使命。
这段话曾经教育过多少人,给过多少人以鼓舞和力量!它也能给文艺创作问题以深刻启示,这就是:人物形象的高大和感人主要不在是否具有较高的认识水平和发现生活中新道理的很强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作品自然需要创造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其中包括思想水平高、能力强的英雄形象,但作品只有努力深刻地展示人物的光辉品质,才能真正完成用共产主义精神有力地教育人民的使命。
区分思想品质和思想水平,对于创作的另一点意义,是便于根据各种人物的不同身份、不同条件,把人物思想写得更准确、更切合、更有分寸。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努力吸取党的思想并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党的思想,这是广大革命人民特别是英雄人物的共同特点。需要稍加分辨的是:努力运用党的思想,并不一定就善于运用党的思想,这两者中间并不是没有距离的。梁生宝在全国互助合作初期涌现出来的一些青年革命农民中,可以是相当成熟的一个(所谓“成熟”,自然是相对意义上说的),这样写,我并不以为有什么毛病。但是如果像邓牛顿等同志要求的那样,把“今天很多革命干部”“
善于
用党的思想和党的原则来思考问题”
 这点概括到梁生宝身上,那么这种“成熟”就可能过分,因而未必对形象的塑造有好处了。梁生宝形象有时使人感到存在一些弱点,原因之一恐怕就在这里。作品写他通过生活里某些具体事情
这点概括到梁生宝身上,那么这种“成熟”就可能过分,因而未必对形象的塑造有好处了。梁生宝形象有时使人感到存在一些弱点,原因之一恐怕就在这里。作品写他通过生活里某些具体事情
 ,自己形成了对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方针、路线、政策的想法。这些想法,如果都是梁生宝过去听到的党的指示教育或者回忆领导同志的谈话,当然就完全合情合理;但作品的实际描写并非这样,它们大多是梁生宝自己的体会:有些是他独立地得出来的,有些则是借领导同志的谈话来印证自己的体会。例如第352页写他从大伙亲密无间的表现中,领悟出:“改造农民的主要方式,恐怕就是集体劳动吧?不能等改造好了才组织起来吧?要组织起来改造吧?”第354页写他想起书记谈话之后,领悟出:“啊,啊!工人阶级是咱中国的领导阶级!这贫雇农恐怕就是乡下的领导阶级吧?要不然你在乡下到哪里去寻工人阶级呢?”这类道理要从生活中直接领悟出来,显然并不是不需要一定的思想水平的。一些同志认为,梁生宝既然经过整党教育,就不难“自然”地想到这些道理,这未免把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思想的得来看得过于容易了一点。
,自己形成了对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方针、路线、政策的想法。这些想法,如果都是梁生宝过去听到的党的指示教育或者回忆领导同志的谈话,当然就完全合情合理;但作品的实际描写并非这样,它们大多是梁生宝自己的体会:有些是他独立地得出来的,有些则是借领导同志的谈话来印证自己的体会。例如第352页写他从大伙亲密无间的表现中,领悟出:“改造农民的主要方式,恐怕就是集体劳动吧?不能等改造好了才组织起来吧?要组织起来改造吧?”第354页写他想起书记谈话之后,领悟出:“啊,啊!工人阶级是咱中国的领导阶级!这贫雇农恐怕就是乡下的领导阶级吧?要不然你在乡下到哪里去寻工人阶级呢?”这类道理要从生活中直接领悟出来,显然并不是不需要一定的思想水平的。一些同志认为,梁生宝既然经过整党教育,就不难“自然”地想到这些道理,这未免把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思想的得来看得过于容易了一点。
写人物的理念活动,还有个性化和不脱离规定情景的问题。恩格斯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的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做。”
 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说的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说;不仅表现在他想的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想。掌握好在规定情景中“怎么样说”和“怎么样想”,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表现出人物有特点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作家在写人物理念活动时必须突破的困难任务。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干部是会接受党的思想和革命道理的,但他们真正理解之后,往往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想,用自己的语言去说,而且想得、说得是那么生动和富有农民的风趣。即或在生活中也有一些农民干部说的语言带很重的知识分子气,不生动,缺少性格特点,文艺作品的任务仍然是要把生活的真事化为艺术的生动,使人物语言更符合、更能代表农民的身份,使性格特点更为鲜明、更为突出。文艺应该比生活更高、更典型的原则,甚至对人物语言的精选、提炼也都是适用的。至于作家把自己在生活中得来的一些体会放到人物身上,这也并非绝对不许可,只要符合人物身份、性格条件就行,不能由此得出什么“不真实”的结论。总之,关于理念活动,不存在可不可以写的问题,需要讨论的只是如何写才生动。梁生宝的理念活动,有些写得是成功的,除了我过去已经提到的一些之外,还可以举出梁生宝在发家和剥削问题上同继父进行的辩论以及考虑白占魁入组时的一些想法作为例子。这些地方,人物也都在说道理和想道理,却写得很精彩,能够紧紧吸引住读者。其原因就在于这时人物所说或所想的道理,充分符合规定情景,动作性很强,语言、思维方式也较能显示出人物的性格、气质特点。但是,作家写梁生宝时也有部分地方所用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知识分子气较重,个性特点不够鲜明。这不免会削弱形象在读者中的效果。人物的有些理念活动也写得并不都很自然,都很符合当时的规定情景。譬如,第109—110页写生宝处在争要稻种的庄稼人“严严实实”的包围中,“被挤得受不了”,又要忙着捉秤计量,就在这时,却涌起了不少思想活动:从回忆买稻种以前人们的态度,想到眼前,然后懂得了党提出互助合作道路的根据。这就未必很近情理。而且在争要稻种的庄稼人中,也有梁大老汉和郭世富;仅仅根据他们“愿意多打粮食,愿意增加收入”这一点,怎么就一定能得出“互助合作有办法,有希望了”的结论来呢?又如,第345页写一个老乡看到梁生宝带领的进山队伍之后,说了一句:“这是梁生禄互助组组长没进山来,打发他叔伯兄弟领进来。”从这件事里得出这个老乡“多少有点夸夸其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结论,我看已经很够了。梁生宝却想:“在整党学习时王书记说过嘛!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头,富裕中农是受人敬重的人物。……”(第348页)这样写虽能显示生宝对问题看得深,想得远,但因具体过程写得不够周密而未能使人信服。
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说的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说;不仅表现在他想的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想。掌握好在规定情景中“怎么样说”和“怎么样想”,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表现出人物有特点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作家在写人物理念活动时必须突破的困难任务。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干部是会接受党的思想和革命道理的,但他们真正理解之后,往往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想,用自己的语言去说,而且想得、说得是那么生动和富有农民的风趣。即或在生活中也有一些农民干部说的语言带很重的知识分子气,不生动,缺少性格特点,文艺作品的任务仍然是要把生活的真事化为艺术的生动,使人物语言更符合、更能代表农民的身份,使性格特点更为鲜明、更为突出。文艺应该比生活更高、更典型的原则,甚至对人物语言的精选、提炼也都是适用的。至于作家把自己在生活中得来的一些体会放到人物身上,这也并非绝对不许可,只要符合人物身份、性格条件就行,不能由此得出什么“不真实”的结论。总之,关于理念活动,不存在可不可以写的问题,需要讨论的只是如何写才生动。梁生宝的理念活动,有些写得是成功的,除了我过去已经提到的一些之外,还可以举出梁生宝在发家和剥削问题上同继父进行的辩论以及考虑白占魁入组时的一些想法作为例子。这些地方,人物也都在说道理和想道理,却写得很精彩,能够紧紧吸引住读者。其原因就在于这时人物所说或所想的道理,充分符合规定情景,动作性很强,语言、思维方式也较能显示出人物的性格、气质特点。但是,作家写梁生宝时也有部分地方所用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知识分子气较重,个性特点不够鲜明。这不免会削弱形象在读者中的效果。人物的有些理念活动也写得并不都很自然,都很符合当时的规定情景。譬如,第109—110页写生宝处在争要稻种的庄稼人“严严实实”的包围中,“被挤得受不了”,又要忙着捉秤计量,就在这时,却涌起了不少思想活动:从回忆买稻种以前人们的态度,想到眼前,然后懂得了党提出互助合作道路的根据。这就未必很近情理。而且在争要稻种的庄稼人中,也有梁大老汉和郭世富;仅仅根据他们“愿意多打粮食,愿意增加收入”这一点,怎么就一定能得出“互助合作有办法,有希望了”的结论来呢?又如,第345页写一个老乡看到梁生宝带领的进山队伍之后,说了一句:“这是梁生禄互助组组长没进山来,打发他叔伯兄弟领进来。”从这件事里得出这个老乡“多少有点夸夸其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结论,我看已经很够了。梁生宝却想:“在整党学习时王书记说过嘛!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头,富裕中农是受人敬重的人物。……”(第348页)这样写虽能显示生宝对问题看得深,想得远,但因具体过程写得不够周密而未能使人信服。
总的看来,《创业史》在表现梁生宝这类英雄形象的觉悟和理想方面,已经做了可贵的探索,提供了值得重视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还存在着若干尚未解决得很好的问题。如何正确地总结这些经验和问题,更好地表现英雄人物的高度觉悟和远大理想,推进新英雄形象的创造工作,这是作家、读者和批评者的共同任务。
“传统的艺术冲突公式”过时了吗?
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高度觉悟,主要应该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这个原则大家是一致承认的。然而由于对矛盾冲突理解的不同,讨论时在具体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有的同志则发展到认为“表现我们今天这种平凡而伟大的普通劳动人民的英雄形象”,面对面冲突搏斗已经不很适用,再也不该“用旧的传统的关于艺术冲突的公式去要求作家”
 了。
了。
艺术中的矛盾冲突源于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生活本身无论在过去或今天,都是复杂的,都有种种不同的矛盾冲突的形式,与此相应的艺术矛盾冲突也都会千差万别。事实上,过去时代文艺作品里矛盾冲突的具体内容和样式,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因此,把“传统的关于艺术冲突的公式”仅仅归结为面对面搏斗,又把面对面搏斗仅仅看成敌我之间的“刀兵相见”,然后宣布这种“公式”已经过时,这首先就是对艺术冲突作了简单化的狭隘的理解。其次,从理论上说,在今天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否像柳青同志所说的那样,面对面的冲突斗争已经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甚至连恩赐观点也只在民主革命时期才需要强调反对
 呢?我看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像吴中杰、高云同志所说:“就题材范围来看,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条道路的斗争常常是通过日常的生活、工作、劳动表现出来的;但这并不是说日常的生活、工作、劳动就没有正面冲突了。”他们表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似乎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生活斗争的文艺作品就可以不必有正面冲突了”。
呢?我看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像吴中杰、高云同志所说:“就题材范围来看,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条道路的斗争常常是通过日常的生活、工作、劳动表现出来的;但这并不是说日常的生活、工作、劳动就没有正面冲突了。”他们表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似乎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生活斗争的文艺作品就可以不必有正面冲突了”。
 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这个意见。可以补充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尽管大量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但也还有敌我矛盾,有时这方面的斗争还是相当尖锐激烈的,文艺对它的反映不可以放松。否则,将该怎样看待《夺印》《汾水长流》《箭杆河边》等许多作品的出现呢?至于说恩赐观点,我们党不管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强调反对的。《创业史》第一部里区委王书记曾经提到“有个别乡长,在群众会上竟然这样讲话:‘没有共产党,你们怎能分到地?共产党号召互助合作,你们对互助组不热心?还闹自发?把良心拿出来!’”这样的乡干部以讨账方式向群众做教育工作:“我给你分了地,你还不响应我的号召吗?”这其实也就是恩赐观点的一种表现。用这种观点搞互助合作运动,肯定会招致很坏的效果,怎么可以不去强调反对!
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这个意见。可以补充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尽管大量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但也还有敌我矛盾,有时这方面的斗争还是相当尖锐激烈的,文艺对它的反映不可以放松。否则,将该怎样看待《夺印》《汾水长流》《箭杆河边》等许多作品的出现呢?至于说恩赐观点,我们党不管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强调反对的。《创业史》第一部里区委王书记曾经提到“有个别乡长,在群众会上竟然这样讲话:‘没有共产党,你们怎能分到地?共产党号召互助合作,你们对互助组不热心?还闹自发?把良心拿出来!’”这样的乡干部以讨账方式向群众做教育工作:“我给你分了地,你还不响应我的号召吗?”这其实也就是恩赐观点的一种表现。用这种观点搞互助合作运动,肯定会招致很坏的效果,怎么可以不去强调反对!
艺术冲突应该在概括生活的基础上力求集中、尖锐,但它的形式多种多样,它的途径十分宽广。把艺术冲突仅仅划分为面对面和非面对面的两种,然后说某种只适合于过去、某种才适合于今天,这样做的本意是想探讨艺术规律在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和演变,但由于理解得过于狭窄,脱离了生活,反而可能不利于文艺的发展。事实上,且不说远的,单是《创业史》里写到的矛盾冲突就很多种多样。譬如,梁生宝跟继父梁三,这是一种(而且自始至终都写得相当出色);梁生宝跟郭振山,另是一种(这方面如果不同梁生宝一些写得过于成熟的理念活动联系起来看,那么如我以前所说,写得也“颇有分寸”,虽然个别地方仍有弱点);梁生宝跟郭世富,又是一种。要说面对面冲突,也不少,例如高增福同姚士杰,高增福同白占魁(会场上),郭振山同郭世富(在活跃借贷的代表会上),郭振山同姚士杰(统购统销),以及新法育秧时欢喜先后同孙水嘴、郭世富、梁大老汉等的几次冲突,这些都写得很好,合于规定情景,使冲突双方的思想性格大为鲜明突出。特别是第二十章写欢喜在生宝等进山之后,为了新法育秧受到组内外自发势力的嘲笑而进行反击,接连三次,绝不雷同,显得十分动人,准确有力地表现了人物稚气然而坚定、聪明的可爱性格。再进一步分析,在面对面冲突中,情形也各有不同:有的达到了异常尖锐的地步,有的发生了冲突却并未出现脸红脖子粗的争吵(如郭振山同郭世富),也还有像梁三老汉那样趁生宝外出买稻种之机而有意大吵大闹的富有喜剧性的场面(这种“缺席”吵架,在我看来可以说是一种特定条件之下特殊形式的面对面冲突)。此外,有些矛盾冲突相当剧烈,却并不一定有冲突的双方,而主要是在内心进行;我在以前文章中称之为“异常出色”“特别动人”的梁生宝吸收白占魁入组,就属于这种情形。举出这些,足以说明那种认为面对面冲突对于表现“平凡而伟大的普通劳动人民的英雄”已经不很必要的理论,是多么不合事实。也足以说明有些同志断定我认为梁生宝不在矛盾斗争之中,或者硬说我把艺术冲突狭窄化为面对面搏斗,这些指责是多么缺少根据。
诚然,从矛盾冲突的角度来考察梁生宝形象,我跟一些同志在局部描写上看法是有不同的。我在《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中,提出了如何“充分利用梁生宝这种处在斗争第一线上的已有条件来展开正面描写”的问题。梁生宝当然“处于跟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漩涡”中心,他同姚士杰等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且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两种力量势必会达到不能两立的地步;这是谁都承认的。我多少感到惋惜的只是第一部中缺少双方在生活里并非全不可能发生的某些正面交锋(所谓“交锋”,当然远不是使矛盾在作品第一部中都“一一解决”),因而也许失去了刻画人物、表现人物的若干机会。有的同志认为,从情节结构上看,不能说“姚士杰等的活动和梁生宝的活动这两条线索各不相扰”;例证就是姚士杰诱奸素芳并利用了素芳的关系把拴拴一家拉出互助组。但是,且不说素芳进姚家这章使人读来颇有不舒服之感(现在这种写法,是不利于表现素芳作为一个贫农的媳妇受了富农的侮辱的),就拿拴拴家退组这点来说,作品的实际描写和这些同志说的也有距离。不错,初版第334—335页写了富农向素芳布置极为毒辣卑鄙的阴谋,然而根据第340—341页和第431—434页两处的描述,拴拴一家退出互助组并非素芳出了什么主意,而是完全由王瞎子自己作的决定,其直接导火线则是拴拴在山中受伤消息的传出。这里虽然也可以看到姚士杰通过拉拢高增荣(所谓“两家在一块搭犋”)而对互助合作事业起的“示范性”破坏作用,但要说通过素芳的关系使姚士杰已经和梁生宝互助组展开了正面斗争,这点在作品中至少还看不出来。至于梁生宝带人进山的行动,在书中所占地位确是十分重要的,但从艺术上看,由于“山中”一章,正面写主人公在矛盾、困难、斗争中的行动和内心活动较少(拴拴受伤后梁生宝的救助写得好,野兽等就过于一般),写较为平静状态中的思想活动和理念活动较多(又写得不算成功),未能紧紧抓住与大自然的斗争展现人物崇高品质和远大理想,因而给人印象不深,缺少其他出色章节里焕发出的那种动人的生活光彩。我所说的梁生宝形象“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便是指的这些方面。到目前为止,批评的同志至少还没有把我说服。
“画眼睛”和“写灵魂”
把英雄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写,是不是一定就有强烈的感人力量了呢?也还并不都能保证。譬如,让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主人公翻山越岭,穿行于悬崖绝壁之间,做一些对人物具体条件说来多少有点超越人们想象的事情,这虽然便于从严峻考验中写出人物的坚强意志和毅力,但如果对这类传奇性情节过分看重,大加渲染,有时反而可能削弱了给读者的真实感。又如,过去有的作品写英雄人物一再出生入死,冲杀于敌军中间,虽然显示了主人公的勇敢顽强,但矛盾冲突本身只是外在于人物的量的堆积,无助于逐步深入地揭示人物的内在特征,形象仍然显得模糊。这就说明,如果作家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而还不能掌握住他,犹如行驶船艇于惊涛骇浪中而缺少驾驭自如的高度本领,也还是会发生问题的。写矛盾冲突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为了使人物本色特征显示得更为清晰鲜明。创作的根本要求仍在作家对人物充分熟悉并能选取富有特点的言语动作,深刻而准确地揭示出人物的灵魂,以达到强烈地感染人、教育人的目的。
在人物形象的艺术塑造方面,鲁迅有两条相互联系着的重要意见,这就是“画眼睛”和“写灵魂”。他用别人谈绘画的意思做比方,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也就是说,应该以极省俭的笔墨抓住人物最突出的具有内在意义的特点,表现人物最本色的方面。而这样做则是为了深入有力地显示人物的灵魂。在鲁迅看来,“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
。也就是说,应该以极省俭的笔墨抓住人物最突出的具有内在意义的特点,表现人物最本色的方面。而这样做则是为了深入有力地显示人物的灵魂。在鲁迅看来,“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
 这里概括了鲁迅本人阅读中外名著时从切身感受中得来的许多经验,也正好说出了他自己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那样强烈深刻的感人力量、令人经久不忘的艺术方面的重要原因。
这里概括了鲁迅本人阅读中外名著时从切身感受中得来的许多经验,也正好说出了他自己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那样强烈深刻的感人力量、令人经久不忘的艺术方面的重要原因。
文艺创作上的许多事例证明:鲁迅这些意见对包括新英雄形象在内的整个人物形象塑造工作,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作品中的正面形象,笔墨不多而能神情毕现,跃然纸上;也有一些则花去不少篇幅,却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里的根本性原因就在于作家是否真正洞悉人物的灵魂而又抓住了某些最独特的东西来加以体现。塑造人物成功与否,成功的程度怎样,这虽然与一定的篇幅有关,但主要不取决于量,而取决于质。《红岩》里写江姐就义前整容、换衣,这个细节并没有占去多少笔墨,然而却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江姐的这些动作里,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强暴的敌人的极度轻蔑,对死亡的无畏,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信,表现了她作为革命者所特有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和庄严、自豪的感情,也表现了她平日爱整洁的个性,总之,从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到某些日常生活特点,都概括到了这些小小的动作里。因而使一个细节就包含了如此丰富的内容,胜过作家说千言万语。省委书记罗世文只是作品中由别人口里侧面提到的人物,但通过他临刑前向华子良布置任务这个简单情节,使人读后难以忘怀。这个情节不仅显示了烈士就义前的从容,而且显示了革命者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然对党的事业高度关切,显示了人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较高的领导水平和预见性。对于罗世文这样的党的干部,这个情节富于表现力,不一般化,有特点,切合人物身份;它是作家真正从生活中得来的一种发现。《创业史》里也可举出这样的例子。正当梁生宝互助组两户退组、有人动摇的时候,高增福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人却提出了入组的坚决要求,说:“收我,也要入!不收我,也要入!”这个情节像一道来得恰当其时的闪电,照出了高增福这块纯金的光彩。这是真正用在节骨眼上的笔墨,有一笔就很动人。梁生宝在两位书记面前为继父鸣不平一段,也同样有这种作用。生宝对于乡长樊富泰说梁三老汉“忘恩负义”“没良心”,当真生气而且非常激动;这番激动连两位书记都感到“吃惊”。他的态度仿佛“出人意料”,仔细一想却又完全“在人意中”,它正是生宝最本色的表现,确实是人物身上独特而又显示了本质的东西。如果梁生宝没有这番激动,他就不是一个淳厚朴实的农民出身的好党员,他就不成其为梁生宝,而作为艺术形象,也就会深厚不起来。还可以举梁生宝从山里回家时通过韩培生眼睛所看到的人物形象作例子:
韩培生仔细看时,他完全惊呆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人,就是梁生宝吗?出山后解下的毛裹缠夹在腰带里,赤脚穿着麻鞋,浑身上下,衣裳被山里的灌木刺扯得稀烂,完全是一个破了产的山民打扮。生宝的红棠棠的脸盘,消瘦而有精神,被灌木刺和树枝划下的血印,一道一道、横横竖竖散布在额颅上、脸颊上、耳朵上,甚至于眼皮上。韩培生没进过终南山,一下子就象进过一样,可以想象到那里的生活了。
韩培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激动过。他的心在胸腔里蛮翻腾,他的眼睛湿润了。共产党员为了人民事业,就有这大的劲啊!
生宝他妈看了一阵儿子,背过脸去了。老妈妈用手指头抹了泪珠,转过脸说:
“生宝!你为互助组受死受活,人家拴拴家和生禄家退出去了……”
“我早知道了。”生宝平淡地说,“我一起就不想要这两户来,王书记硬叫收下哩。这阵,两个重包袱子卸啦,更好往前干嘛!……”
老妈妈看见儿子快乐的神气,破涕为笑了。韩培生的思绪,现在完全被打乱了。他的心灵和情感,受了这样大的震动,以至于一时间说不出任何的话来。
不但韩培生眼睛湿润,心灵震动,读者的眼睛也湿润了,心灵也随着受到很大震动。这里没有冲突,但却有感情发展的高潮。生宝在两户退组、亲人为他难受、担心的局面下,只平淡地说了一句话,然而这句话一下子使人物形象高大、深厚了起来。这句话只有梁生宝才能坦然说出,这种感情和胸襟只有梁生宝才会有。这一段笔墨不算多,但比起写了一章半的山中活动来,激动人心的力量却远远超过。此中道理,实在很值得我们深深思索。
我曾经长时间在心头留下过一个疑问:为什么《创业史》第一部的许多读者都觉得梁三老汉形象在书中写得最成功、最深厚、最丰满?为什么以较多篇幅写的主人公梁生宝形象,虽然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还使人觉得不十分丰满,比起梁三老汉形象来在精神状态的揭示方面略显得浅些?原因何在?这回再读作品的时候,我渐次得到了这样的答案:关键在于作家能否真正深入洞悉人物的灵魂,并且紧紧抓住人物独特的、确实属于“这一个”的动作和语言来加以表现。凡是做到了这点的,人物描写就会像上述成功的例子那样,显得颇有深度,作家的意图就会在读者中产生应有的效果。反之,就可能缺少深度,显得一般化,作家意图和作品效果就会不一致。如果这个答案能够大体符合实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梁生宝形象的塑造在不少地方是达到了这个要求的,然而比之梁三老汉,作家对于他可能把握得不那样深、那样准,有时还出现了一些同作家已经赋予人物的性格不协调的描写(例如前面举过的“爱美”心理之类)。这也许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看来,作家要真正了解人物的灵魂并善于通过在特定环境中最准确、最有特点的言语、行动表现出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从人物某一有特征的动作看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并发现其中蕴藏的丰富意义,这不仅首先需要高度的思想水平并熟悉生活,而且需要对人物心贴心的了解以及敏锐细致的艺术感受能力,需要这几个方面的密切结合,否则很可能对面相遇而仍交臂失之。这里有一长段艰苦的路程,然而却是一条真正通向典型创造的可靠道路。梁生宝形象以及其他许多新英雄人物形象艺术塑造方面所提供的成功的和不够成功的经验,都使我们深深地相信这一点。
结束前的一些话
梁生宝形象在第一部中艺术方面暂时还赶不上梁三老汉那样完整,那样成功,能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梁三老汉形象比梁生宝形象还重要,说应该提倡写梁三老汉这样的形象?
当然不能。什么形象重要并且应该提倡,这不取决于某个具体作品中人物艺术描写成功的程度。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文学担负的促进人们革命化这个使命出发去考虑问题。英雄形象最能充分地体现我们时代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时代精神,对读者有直接的教育作用和仿效作用,在形成人们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其他人物形象不管多么成功,都不能取代这个地位。还应该考虑到:英雄人物完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人,他们处于飞速发展成长之中,作家充分熟悉和把握他们有较多困难,艺术表现方面的借鉴也少。因此,新英雄形象(尤其是在作品中占中心位置的新英雄形象)尽管写得还不如同书中其他形象成功、丰满,只要不是失败或者基本上失败,仍然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至于像梁生宝这样一个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当然更应该受到热情欢迎。比之于其他同类题材作品中的同类人物,梁生宝确是一个在艺术上有了很大突破、获得了突出进展的形象。如果说,《创业史》的成就在于通过各阶层人物形象的相当成功的塑造,反映了互助合作初期农村的阶级斗争,并且显示了特有的广度和深度;那么,这个成就的取得,固然和梁三老汉形象有关,和郭振山、郭世富等形象有关,更和梁生宝、高增福等形象不能分开。离开了梁生宝形象,当然是不能正确估计《创业史》的成就的。我过去的文章如果使人感到在这方面不够明确、有所模糊,我愿意在这里加以澄清和补正。
到目前为止的这次讨论,加深了对于梁生宝形象的正面探讨和阐释,并且提出和涉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新英雄人物艺术塑造的某些理论性问题,总的说来是有益的。但同时,讨论中发表的有的文章也比较突出地暴露了一些学风的问题。我愿在这里说说我的想法。
在学术讨论中,不能准确恰当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或者误解了对方的意思,这种事情是常有的,甚至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意无意地歪曲对方的意思,把一句半句话从语言环境中孤立出来,然后任意搬家,套到不相干的论题上,得出同原意相距极远的结论,那就不是严肃的批评。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冯健男同志(自然,他文中有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他为了证明我“否定梁生宝形象”,就硬说我讲过梁生宝是个“无法根本区别于概念化的人物”。话上面带着引号,说明是从我文章里引出来的,这当然应该“证据确凿”的了。但一查原文,它原来包括在这样一段文字里:
……思想上最先进并不等于艺术上最成功;人物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并不就能决定形象本身的艺术价值。艺术典型之所以为典型,不仅在于深广的社会内容,同时在于丰富的性格特征,在于宏深的思想意义和丰满的艺术形象的统一,否则它就无法根本区别于概念化的人物。
这里说的,完全是评价一般正面形象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可能有用语不准的地方(所说的“艺术价值”,实际是指艺术成就),我的目的只在于说明“艺术典型”和“概念化人物”之间的区别。冯健男同志对我的意见如果不同意,尽可以批评。但他却居然从中摘出“无法根本区别于概念化的人物”一语,套到梁生宝形象的评价上。这种批评方法,怎不使人感到惊异呢!冯健男同志还说我“在口头上承认‘有成功的一面’”,言外之意就是我心口不一,口是心非。请问冯健男同志:你从何处发现我心底里认为梁生宝根本是个“失败”的艺术形象?说话和写文章总是表现在“口头上”和笔头上的,难道可以离开“口头”和笔头而另找评判的根据吗?
有的同志使用的推理方法也是值得考虑的。例如:说梁生宝并不是全书中最成功的形象,那就是“企图贬低以至否定”这个形象;说梁生宝形象存在“三不足”的弱点,那就是把它看作“失败”“不真实”;不赞成只从梁生宝的角度来肯定《创业史》,那就是“排开梁生宝形象以及他在《创业史》中所处的地位”;说梁生宝的理念活动有时写得同人物身份、性格等条件不尽符合,那就是认为这个形象“用‘理念’的砖头堆砌起来的”;说梁生宝形象有时不能扣紧先进农民的气质,那就是认为它“离开了现实基础”,“被拔高了”;说梁生宝形象放在矛盾冲突中表现得不够,那就是认为“没有矛盾冲突”,“在静止的状态中带着苍白面孔”;说姚士杰的活动和梁生宝的活动从情节结构上看有“各不相扰、孤立发展之嫌”,那就是“不但整个否定了梁生宝,而且全盘推翻了《创业史》”;等等。这种推理的特点,是把对方的意见加以夸张,使它极端化而变为明显荒谬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如果有人不赞成给某事物以“5 + ”的评价,那就意味着这个人只主张给它打“3”或“2”分,好像介乎其间的“5”“5 - ”“4 + ”等级别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简单的不实事求是的推理方法,只能导致主观、武断,不利于对学术问题展开认真、深入的讨论。
辨别学术上的是非,是件细致的事情。这里特别需要实事求是和耐心。讨论的双方都应该仔细看待对方的意见。出现了不同意见,即使有偏颇或不正确的成分,但如果不属于恶意攻击性质,那就应该认真思考对方提出的问题(而不是把问题掩盖或者简单地挡回去),分辨其中的正确和错误,肯定其正确方面,批评其错误方面(而不是一概抹杀或竭力夸大);如果完全不正确,彻底批评当然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使问题越讨论越深入。
1964年7月5日
原载《文学评论》1964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