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的生平和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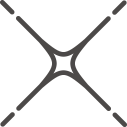
多年前,曾有同志对我说过:“当代作家中,论生活经验之丰富宽广,很少有超过姚雪垠的。”当时,我对这番话未敢认可。后来读到《李自成》第二卷有关相国寺风光的描写,特别在对姚雪垠的生活和创作经历有所了解之后,我终于有点信服了。
姚雪垠,原名姚冠三,1910年10月10日(农历庚戌年九月初八)出生于河南省邓县西乡姚营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上过开封优级师范,但“幼年就抽上烟瘾,象当时一般没落的地主家庭的孩子们一样”(《我的老祖母》)。有兄二人。由于家境窘困,母亲准备在他出生时溺婴,幸为曾祖母所救。
 八岁以前不曾认字,一直在农村生活,爱听外祖母讲故事。后来曾回忆说:“最早启发我的想象能力,培养起我的文学趣味的,不是王尔德,不是安徒生,也不是五四时代的文学先驱者,而是我的外祖母,一个不识字的乡下老婆。”(《外祖母的命运》)
八岁以前不曾认字,一直在农村生活,爱听外祖母讲故事。后来曾回忆说:“最早启发我的想象能力,培养起我的文学趣味的,不是王尔德,不是安徒生,也不是五四时代的文学先驱者,而是我的外祖母,一个不识字的乡下老婆。”(《外祖母的命运》)
邓县地处豫西南,环境闭塞落后,水旱灾害与瘟疫频仍。加上封建军阀压迫,农民无以为生,或外出逃荒,或铤而走险。“五四”前后,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遍地土匪的县份”(《外祖母的命运》)。九岁那年,土匪攻破寨子,姚家房屋和衣物都被烧光,从此随父母逃到邓县城内居住,父亲改以写状纸为生。在县城里,先读了一年多私塾,又上了三年教会办的高等小学,背诵过大量古文并习作文言。暇时爱听艺人说《施公案》《彭公案》《三国演义》等书。
1924年小学毕业后,去信阳进入教会办的信义中学,插班读初中二年级。这年冬天,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学校提前放假。回乡途中,与二哥和其他两名学生一起被李水沫的土匪队伍作为“肉票”抓去,旋又被一个土匪小头目认为义子。到次年春天,因土匪队伍被军队打败溃散,他们才由其义父派人送回邓县。在土匪中生活约一百天的这段特殊经历,就成为他后来创作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
此后四年多,除去樊城鸿文书院读书的几个月外,基本上失学在家。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鲁迅的《呐喊》、叶绍钧的《隔膜》、王统照的《一叶》和《黄昏》等许多作品,也读了耿济之等翻译的一些俄国作家(如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小说,培养了对新文学的兴趣,增强了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实的不满。县城西门外是刑场,他常看到将犯人游街、站笼、砍头、剖心、割势而四周群众一概麻木地叫好的场面。他说:“几年中我看过杀人的次数很多,有一次杀了二十多个人。我看过人被砍头或枪毙后,有的死尸被抬走,有的被抬到附近掩埋,有的被狗吃了。被杀的没有一个有身份的,全都是农民模样的乡下人。”(《渡船上》)这些见闻在少年心灵中留下苦痛难忘的印象。家庭的缺少温暖与社会的黑暗重重,加深了姚雪垠的叛逆性格。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曾两次到具有进步色彩的军队中去当兵:1926年春,参加了刚从广州回来、接受革命政府任命的樊锺秀的“建国军”,前后三个多月,直至樊军被军阀于学忠部队打败而崩溃,才由家里派人接回。次年,又进入冯玉祥麾下孙连仲部队当学兵,两个星期后,因失望而脱离。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出路,滋生了苦闷感伤的情绪。
1929年夏,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与此同时,在《河南日报》副刊用“雪痕”的笔名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和其他作品,这些小说写了下层劳动者受封建势力迫害致死的悲惨故事,表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入学后不久,即参加中国共产党开封地下市委领导的学潮委员会及其组织的活动。次年8月曾以“共党嫌疑”被捕,因查无实据,四天后交保释放。这几年内,读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及其他通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读了清代朴学家、《古史辨》派和郭沫若等唯物史观派的一些代表性论著,关心中国社会史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立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或文学家。1931年暑假,被学校当局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开除。从此结束学生生活,离校逃往北平等地,开始以校稿、教书、编辑为生。到抗战爆发前夕,先后在《文学季刊》、《新小说》、《光明》、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野祭》《碉堡风波》《生死路》《选举志》等十多篇小说,这些作品展现了内地农村在吸血鬼统治下黑暗混乱的现实图景,又写出了被压迫者奋力挣脱枷锁、不屈反抗的斗争画面,得到左翼批评家(如周立波)的好评。此外,编过《大陆文艺》《今日》两种刊物,在《芒种》《申报》上发表《鸟文人》《京派与魔道》《论潇洒》等杂感,还刊出散文、散文诗、文学论文多篇。这些文章同样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关切,有敏锐的时代感。由于受文艺大众化、大众语讨论的影响,1934年患肺结核病回乡休养期间,曾收集家乡口语,编为《南阳语汇》。“从此真正认识了口语的文学美,那美是在它所具有的深刻性、趣味性,以及它的恰当、真切、朴素与生动。”(《我怎样学习文学语言》)
抗战爆发后,从北平辗转来到开封,与嵇文甫、王阑西、范文澜等创办《风雨》周刊,任主编。《风雨》曾被赞为“大江以北最前进的救亡刊物”(《大时代旬刊》),姚在此先后发表论文、杂感数十篇。并曾赴徐州前线采访,随后写作出版了书简体报告文学《战地书简》。
1938年春去武汉,不久应钱俊瑞函邀,参加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日的进步的文化活动。在《自由中国》《文艺阵地》上发表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次年又在《文艺新闻》上刊出气氛悲壮的《红灯笼的故事》。后两篇曾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并被译为英、俄文,选入苏联出版的《中国小说》。《差半车麦秸》(郭沫若、茅盾等均有评论)和稍后的中篇小说《牛全德和红萝卜》之所以受到文学界的重视,是因为作品成功地运用了活泼生动的群众口语写出农民在抗战中的觉醒与变化。李广田认为:《差半车麦秸》所使用的语言,“是真正的最好的活的语言”,“这不是从任何书里边可以找得出来的,更不是任何作家可以从脑子里造得出来或偶然从作者笔尖滑了下来的”
 。自“左联”倡导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以来,至此才开始在创作上见出成绩,这是姚雪垠多年刻苦努力的结果。1939年起,姚雪垠在转辗鄂、皖、蜀等地的过程中,以主要精力创作中长篇小说,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新苗》《重逢》等。这些作品多以抗战初期知识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题材,写出了年轻一代高昂的救国热情,并从侧面触及了国民党军政机构的黑暗腐败与地方封建势力的猖獗,揭示了抗战阵营内部的复杂斗争。笔法转向委婉细腻,语言更为活泼多样,可读性强。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爱情生活方面用了过多的笔墨,冲淡乃至削弱了表现时代的主题。这个时期,他也写了不少文学论文,如《现阶段的文学主题》《通俗文艺短论》《文艺反映论》《屈原的文学遗产》《创作漫谈》《需要批评》《小说结构原理》《论目前小说的创作》等,其中一部分曾集为《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一书出版。此外,还印行了《M站》《春到前线》《差半车麦秸》等短篇集。
。自“左联”倡导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以来,至此才开始在创作上见出成绩,这是姚雪垠多年刻苦努力的结果。1939年起,姚雪垠在转辗鄂、皖、蜀等地的过程中,以主要精力创作中长篇小说,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新苗》《重逢》等。这些作品多以抗战初期知识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题材,写出了年轻一代高昂的救国热情,并从侧面触及了国民党军政机构的黑暗腐败与地方封建势力的猖獗,揭示了抗战阵营内部的复杂斗争。笔法转向委婉细腻,语言更为活泼多样,可读性强。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爱情生活方面用了过多的笔墨,冲淡乃至削弱了表现时代的主题。这个时期,他也写了不少文学论文,如《现阶段的文学主题》《通俗文艺短论》《文艺反映论》《屈原的文学遗产》《创作漫谈》《需要批评》《小说结构原理》《论目前小说的创作》等,其中一部分曾集为《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一书出版。此外,还印行了《M站》《春到前线》《差半车麦秸》等短篇集。
抗战胜利前后,姚雪垠转向故乡与童年的题材,完成了自传性长篇小说《长夜》,并写了《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运》《大嫂》等一组散文。《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像《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不但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中绝无仅有,即使在世界近代文学中也并不多见。无怪乎当《长夜》由《红楼梦》的法文译者李治华译为法文之后,法国读者表现出浓烈的兴趣,姚雪垠因此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作者自述具有“在逆境中不改素志”的顽强性格(《学习追求五十年》之八),他的小说从早年起,也确实在透露出一种强悍的气质:1929年发表的《强儿》就刻画着一种坚强的性格,30年代中期刊出的《野祭》《援兵》《生死路》等写的也都是一些敢作敢为、不怕掉脑袋的人物;不但游民牛全德为抗击日寇英勇献身,连窝窝囊囊的“差半车麦秸”最后也强悍地表示:“我留下换他们几个吧……”可以说,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努力发掘和表现出一种强悍的美,这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的一个独特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姚雪垠在上海还写了记述爱国科学家的传记文学《记卢熔轩》和短篇小说《人性的恢复》等。1948年以后,先在高行农业学校、继在私立大夏大学教书,同时发表了《明代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等学术论著,这为他后来创作《李自成》准备了条件。
鲁迅在《两地书》1926年12月3日信中说:“我觉得教书和创作,是不能并立的。”1951年,姚雪垠与上海各大学的教师同去浙东参加土改,因不懂当地语言,无法了解风土人情,于是萌生离沪返豫之念。这年夏天,他辞去大夏大学副教务长和代理文学院长的职务,回郑州从事专业创作。1953年因中南作协成立,又迁居武汉。除写了少量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杂感外,创作上处于苦闷的时期,只在50年代中期发表了《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一点质疑》《读〈带经堂诗话〉有感》等古典文学论文。别林斯基的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1957年姚雪垠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后,在逆境中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李自成》是“长河式”的小说,从崇祯十一年写起,共写五卷,三百余万言,全面地反映明末李自成起义由困厄转到兴盛,复由胜利走向失败这一历史悲剧的发展过程。第一卷出版于1963年,第二卷出版于1976年,第三卷出版于1981年,最后两卷也已有若干单元(如《崇祯之死》《李自成之死》)陆续发表。已出版的前三卷共八册,以二百三十万字的篇幅,着重展示了李自成从困境中奋斗,达到鼎盛,却又在鼎盛期内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埋下后来失败的种子。作品不仅着力描绘了农民军和明王朝之间这场生死大搏斗,而且写出了当时十分激烈地进行着的民族战争,还写出了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几支义军之间的矛盾,李自成部队内在的矛盾,写出了明末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在农民大起义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人物从帝王、后妃、百官到义军将领、战士、各类市民、穷苦百姓,乃至清方首领与文臣武将;地域从西北高原、中州重镇、北京城内到僻远山村、关外城池;场面从战地厮杀、牢狱交锋、密室定计、边寨平叛到宫廷宴饮、相国风光、元宵灯市、军中婚礼,笔墨无不触及。作者力图对一个时代的生活做出总体式的反映。就所写社会内容的复杂宽广、生活色彩的丰富多样而言,《李自成》达到了当代作品很少企及的地步。
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悲剧性史诗,《李自成》创造了崇祯、李自成、张献忠、郝摇旗、慧梅、洪承畴、杨嗣昌等一系列性格或遭遇都相当复杂的典型形象——其中有许多是悲剧性的人物形象。不但主人公李自成扮演着大悲剧的主要角色,连他手下的一些人物,如李信、宋献策、田见秀等,其经历也都有很深的悲剧意味。慧梅在第三卷中已经完成了一出义薄云天、感人肺腑的悲剧。而开封城内张存仁全家的遭遇,更是明末战乱中普通百姓的令人心碎的惨剧。抗清将领卢象升竟至血洒沙场固然是悲剧,“剿贼”大臣杨嗣昌被逼服毒自尽未尝没有悲剧成分。可以说,整部《李自成》,就是由大大小小许多历史悲剧组成的。大悲剧中套着小悲剧,小悲剧的演进受大悲剧的支配和制约,而小悲剧的完成又有助于大悲剧的推演和发展。它们相互交织,构成明末社会十分壮阔而错综复杂的背景,使整个作品洋溢着悲壮或悲凉的历史气氛,具有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思想艺术力量。姚雪垠长于写悲剧,他较早的一些作品常有不同程度的悲剧色彩,《李自成》是作者进入成熟时期后写作的,在悲剧艺术的运用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和表现内容的广阔、矛盾线索的纷繁相适应,《李自成》不采取通常那种单线发展的结构,更不采取传统的章回体,而是采用了保证主线、兼写各方、多线条复式发展、蛛网式纵横交错、具体归结为若干单元的结构方法。这种结构既宏大复杂,又舒卷自如,吸取了《战争与和平》等外国长篇的经验而有新的创造。同时,《李自成》又注意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在结构上有张有弛、讲究节奏、笔墨多变的长处:时而金戈铁马,愁云惨雾,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时而小桥流水,风和日丽,令人心旷神怡。朱光潜在《谈美书简》中说:“我读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特别欣赏他在戎马仓皇的紧张局面之中穿插些明末宫廷生活之类安逸闲散的配搭,既见出反衬,也见出起伏的节奏。”这是中肯的评价。《李自成》还很重视艺术结构上的完整、对称:整部小说从清兵入关开始,又以清兵入关结束;各卷的开头与结尾,也都互为照应。这些都是长篇小说美学上的重要探索与创新。《李自成》的出现,继《子夜》之后又一次大大提高了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水平。
姚雪垠早在1932年就很感兴趣地读过记载李自成三次进攻开封的《守汴日记》(李光壂)、《大梁守城记》(周在浚)等书。40年代末到50年代后期曾运用唯物史观潜心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他在旧中国有多方面的阅历。创作上经过长期探索,又积累了较丰富的艺术经验。《李自成》正是作者史学准备、生活积累、理论素养、艺术经验各方面集大成的产物,是几十年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正因为这样,《李自成》第一卷在60年代前期出版后深得好评;第二卷曾于1983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这部长篇的第一卷已由陈舜臣等译成日文,荣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与翻译奖。英法文译本或节译本也正在译印中。
《李自成》一书是在近三十年中陆续创作成的,其间难免有文思不属之处,若干笔墨还有失之拖沓或现代化等缺点。作者已表示待全书完成后,将统一再作修改,最后定稿。在艺术创作的马拉松跑道上,姚雪垠还将继续奋进。
1985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