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壮山河的历史大悲剧

——《李自成》一、二、三卷悲剧艺术管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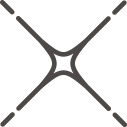
艺术赢得崇高的荣誉,总是与其独特的创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其第二卷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作品具有显著独创性,取得多方面成就的结果。其中悲剧艺术的成功运用与出色创造,则又是《李自成》艺术独创性的鲜明标志,体现了这部作品艺术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李自成》的悲剧艺术,既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作品独到的艺术成就,又能使我们正确地认识李自成起义所包含的实际历史内容,从而科学地探讨和澄清读者与评论者中间提出的若干有争议的问题。
一、悲剧主题独树一帜
《李自成》是一部内容十分复杂的反映明末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的悲剧性史诗。
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是什么?一些同志总以为它是歌颂明末农民大起义,歌颂起义的领导人李自成。他们认为,作者为要实现这种意图,就把主人公理想化了,写得过于高大成熟了。其实,这是一种与作品实际不符的极大的误解。《李自成》作为一部反映明末社会大变动的史诗,包含的主题思想异常复杂丰富,远不是简单地用“歌颂李自成起义”所能概括的。作者为小说规定的主旨艰巨得多,深广得多。小说是要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明朝统治并继而抗清为主线,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生活原貌,揭示明末历史事变的进程及其内在底蕴,通过李自成领导的这场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表现农民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复杂关系,总结农民战争的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整部小说不是把李自成单纯作为英雄人物来歌颂的,作者笔下的李自成是个悲剧人物,是个大悲剧中的英雄。这种悲剧性的英雄,悲剧性的主题,比一般地描绘历史事件的发展,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其主题要深沉得多,意义要宽广得多,它的思想价值与社会影响自然也会长久得多。这正是《李自成》立意上不同凡响的地方。
适应于作品的这一主题,小说以李自成及其起义部队由困厄转到兴盛、复由胜利走向失败这一悲剧过程作为全书情节的主干。作者透过历史表象,通过农民军中众多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深刻地艺术地揭示了李自成及其起义部队何以有此悲剧性发展的内在原因,给予主人公李自成形象以充分的“用武之地”。前三卷着重展示了李自成从困境中奋斗,达到鼎盛,却又在鼎盛期内开始潜伏某种危机,埋下后来失败的种子,从而为整个大悲剧的推演与完成,奠立了无可置疑的坚实基础。
作为悲剧主人公,李自成败而不馁、永不屈服的奋斗精神,与部下同甘共苦的可贵作风,善于总结经验、深思熟虑的睿智头脑,素怀大志、不计私愤的政治家胸襟,以及知人善任、治军极严的统帅才能,等等,这些都是必须表现的。不表现这些,李自成就不成其为令人同情和无限惋惜的悲剧主人公,整部小说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就会大为减色;不表现这些,小说就违背历史事实,失去了基本的历史真实性。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李自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杰出人才。明末清初的官书和野史几乎一致记载,李自成具备一般人难以具备的了不起的品性。专记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史料的《怀陵流寇始终录》,曾这样介绍李自成的为人:
闯……性淡泊,不好酒色,鄙曹、献(按,“曹”指外号“曹操”的罗汝才,“献”指张献忠——引者)多欲,谓非丈夫。粗粝与众共之。妻妾各一,皆老丑。不蓄奴仆(原书批注:此三十三字士大夫不及)。暇则令儒生讲经史。
——第十六卷
可见他是一个胸怀大志、政治上富有朝气的人物。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些领导人中,李自成是最成熟、最受人民拥戴的一位;在众多起义队伍中,李自成所领导的队伍发展规模最宏大,群众影响最深远。即使在极端困难、险恶的情势下,他们也坚持斗争,决不投降,并且善于利用有利形势迅速发展力量,终于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历史性胜利。值得注意的是,李自成起义中还曾出现过某些封建社会前期农民起义不大可能出现的新因素。《明季北略》卷二十说:“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也说:李自成“每有大事,集众各呈其意,不言可否,默取其长者行之”。这些记载表明,李自成具有某种民主作风。崇祯十三年冬进入河南以后,李自成起义军还提出过“均田免赋”这类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口号。所有这些,似乎多少与明中叶以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小说《李自成》从历史生活的实际出发,通过艺术上的精心设计和创造,在前三卷中表现主人公的一些可贵精神,卓异品性,统帅之才,领袖之德,这是极其自然的,基本符合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真实,也完全切合创作多卷本大悲剧的艺术需要。作者摒弃一切轻便的创作路子,决不把李自成写成“超人”,也没有把他领导的起义军写得“完美无缺”。恰恰相反,一卷写了李自成在潼关南原大战指挥上犯了大错误,几乎全军覆没,二卷写了李自成在商洛山保卫战中经受时疫、敌人进攻、杆子叛乱等严峻考验,从而既感人地表现了主人公在革命遭受失败时临危不惧、百折不挠、英勇顽强的可贵品质,也合理地表现了他在风浪里经受磨炼,于挫折中总结教训,逐渐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作者钩沉剔谬,突破某些有关李自成起义的不合理旧说,令人信服地写出农民军获得大发展的内在因素,写出李自成受艰难环境所玉成而将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发挥到了最高度。尽管李自成形象的艺术塑造尚有一些可以斟酌之处,但从创作思想、创作方法上说,这样的形象,实在是与那种所谓“高、大、全”之类的写法并无缘分的。

更为可贵的是,就在浓墨重彩地描绘李自成起义事业达到鼎盛的时候,小说也清晰有力地写了农民革命在大发展中隐伏着的危机,写了李自成身上正在滋长着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为大悲剧的推演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在作者看来,李自成部队之所以进入北京又迅速失败,根本原因仍在他们自身。小说在第二、三卷中,随着情节的发展,就用越来越多的笔墨颇有深度地预示了李自成后来的悲剧结局。李自成战略思想上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不要根据地,不能采纳李信兄弟提出的“据宛、洛以扫荡中原,据中原以夺取天下”的正确主张,而是采取打富豪、吃大户,打到哪里、吃到哪里的流寇主义方针,甚至攻下洛阳这座中原重镇后又轻易放弃。第二卷写到洛阳放弃时,作者不禁用了这种带感情的笔调来点染事件本身的悲剧意味:
洛阳,依然城墙高厚,箭楼巍峨,十分坚固,但是今天夜间就要被闯王放弃了。百姓都不明白李闯王如今兵马众多,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扔掉洛阳,有的在暗中议论,有的准备明天赶快逃出洛阳,免得官军进城来会遭到奸淫和屠戮。把守四门的士兵已经换成了留给邵时昌的新兵。街道上有新兵巡逻,秩序如常。从表面看来,洛阳市面平静,没有任何惊扰,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居民们并没有睡,正在度着一个忧心忡忡的长夜。
——第二卷,第1377—1378页
在洛阳百姓们“忧心忡忡”的背后,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隐藏着作者对李自成事业的惋惜和悲哀吗?
小说写到第三卷,在第三次开封战役前后,随着军情的发展,又通过马夫头目王长顺与高夫人的谈话,王长顺酒后发的牢骚,李岩与宋献策对形势的分析,从多种角度提出了设置州府官吏、建立稳固的立足之地,以保证必需的后勤供应的迫切性,进一步显示了李自成错误决策的悲剧后果。请听听,为供应老营马料所苦的王长顺,是怎样在慧英、慧梅跟前发着牢骚的:
“唉,打个大仗还罢啦。打小仗,攻一座城池,也是几十万人马一起跟着!打到哪里吃到哪里,像一群蝗虫一样。蝗虫啊蝗虫,一群蝗虫!”
“……你看咱们现在三个营合在一起,有几十万人马,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每到一地,都要粮食,要草料,把地方吃光喝光。”
——第三卷,第930页
这个思虑非常切实的老马夫提出的问题是多么尖锐!然而,作品没有把这种情况仅仅归因于李自成个人。它所显示的意义要远为深刻得多。流寇主义是与李自成部队中流民(边兵、饥民)占很大成分有关的。他们中有许多陕西人,不愿以河南为根据地。此外,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即一旦设置州府官吏,李自成担心与他貌合神离的罗汝才会占据相当大一部分,那样未必对自己有利。总之,农民阶级狭隘性,限制了李自成做出正确的决策。其结果,正像李侔所说的:“万一将来受挫,便要退无所据。”这就不可避免地最终要带来悲剧。
另一个悲剧性因素,是李自成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和个人威望的提高,逐渐发生着某种不易觉察的变化:思想中消极成分有所抬头,开始习惯于听奉承话,头脑变得不那么清醒,有时对某些重大隐患麻痹大意,丧失警觉。史载李自成进北京之后,明朝大臣梁兆阳、杨观光之流肉麻地称颂他为“圣主”,说他“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李自成听得飘飘然,将一个封为兵政府侍郎,另一个封为礼政府侍郎(《平寇志》卷九)。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入京后才有的,而是在此之前就慢慢出现了。小说写道:“……自从牛、宋等人来到身边,宋献策献了那个谶记,他又正式称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后,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和义军队伍的壮大,那些‘天命所归’‘救世之主’一类的颂扬话渐渐地听得多了,认为理所当然。”(第三卷,第807—808页)投而复叛的袁时中,正是钻了李自成这个空子。应该说,这个作伪到了家、显得非常“真诚”的人物,实在是小说中的一个出色创造。他第一次见面,就以非常得体的吹捧博得李自成的好感,使李自成“颇为满意”(第三卷,第808页)。就在他决定率众叛逃前,还把李自成大大歌颂了一番。正因为李自成本身的这种弱点,才会幻想将对方收为心腹,拆散了慧梅与张鼐的爱情关系,强制慧梅嫁给袁时中,以致造成慧梅的终身遗憾,最后被逼得自尽,并给李自成本身带来“赔了义女又折兵”的尴尬局面。第三卷所写第三次开封战役时黄河水情险急,王长顺两次想向李自成当面禀告,都被门卫阻拦,致使水淹开封的惨剧未能及时防范,这同样表明李自成随着地位变化而增长了与下情的隔膜。可以预计,到农民军进入北京前后,李自成身上更会滋长“天命所归”、唯我独尊的骄傲自满情绪和麻痹轻敌思想。再加上对清军的兴起和入关所构成的巨大威胁估计失误,这就铸成他致命的大错,终于使江山得而复失!
李自成的悲剧是封建社会晚期农民革命的悲剧。如果说,明宋朝政的惊人黑暗,土地问题与社会危机的空前深重,统治势力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压榨与无情镇压,长期封建社会中农民革命经验的不断积累,这些历史条件造就了李自成这样出众的英雄人物;那么,农民本身的狭隘眼界,乡土观念,经济上单纯“吃大户”的思想,军事上的流寇主义,以及由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农民领袖到头来也只能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影响,这种种条件又决定了李自成起义军的最终失败。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无可避免地会构成“悲剧性的冲突”。小说《李自成》悲剧艺术的突出成就,正在于它不是依靠外在的涂抹渲染,也不是着眼于人物的个别际遇,而是从社会条件与人物性格的深处揭示悲剧产生的内在根据,因而使《李自成》这出历史大悲剧具有了深刻的科学的内涵与巨大的非凡的容量。
二、悲剧类型多姿多彩
许多历史题材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种事变,而《李自成》却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事变,还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生活。这部小说所写的历史悲剧,显示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像历史上的社会生活那样呈现了纷繁多彩的面貌。不但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演出悲剧,即使虚构的人物也同样扮演了有声有色、深沉悲壮的悲剧角色。
《李自成》所写悲剧性质、类型的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绝不是我们用普通的单一色调的眼光所能认清、所能理解的。作者从明末的社会现实出发,忠实于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历史大悲剧的壮丽图画。不但主人公李自成扮演着大悲剧的主要角色,连他手下的一些人物,像世家子弟、颇有战略眼光的李信、李侔兄弟,起着重要作用的军师宋献策,平时以忠厚长者著称的田见秀等,实际上也都演着悲剧,他们的最后结局都有着很深的悲剧意味;至于女英雄慧梅,她在第三卷中则已经完成了一出义薄云天、感人肺腑的出色悲剧。此外,开封城内以张存仁全家为代表的普通百姓,他们的遭遇更是明末战乱中令人心碎的悲剧——甚至是一幕幕惨剧。确实可以这样说:整部《李自成》,就是由大大小小许多历史悲剧组成的。这部小说之所以具有深刻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震撼人心的感人力量,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李自成》所写悲剧的丰富性,归根结底是坚持现实主义、坚持倾向性与真实性相统一的结果。作者依据大量史料捉刀用墨,对人物身上的优缺点、正面反面,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都采取如实写来、好处说好、糟处说糟、绝不回避掩饰的态度。
在这里,农民英雄的失败固然是悲剧,封建皇帝的亡国也可以有悲剧意味;抗清将领兵权被削竟至血洒沙场是悲剧,“剿贼”大臣走投无路被逼服毒自尽未尝不含有悲剧成分。“大人物”演着悲剧,“小人物”也演着悲剧……人物复杂到了几乎要打破正反面界限的地步。这样一种将对立双方都按悲剧——自然是很不同的悲剧——来处理的方法,在文艺辞典、文艺学教科书里确实很难找到,它可能会使我们有的读者和评论者瞠目结舌,茫然不知所措。然而,这一切又是有分寸的,其前提是决不模糊历史唯物主义所应该有的倾向性,并且有助于更充分地揭示各类人物的本质真实。以崇祯的悲剧为例,小说一方面认真写了他欲做中兴之主,企图力挽狂澜,宵衣旰食,事必躬亲的干练和辛劳;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了他的色厉内荏,精神上无比虚弱与孤独狂躁。尽管崇祯用尽吃奶力气,然而,积重难返,国势的衰颓,朝政的腐败,义军的蜂起,清兵的进逼,使他陷入焦头烂额、心劳计绌的境地,依然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有些乖张措施甚至加速了这种命运的到来)。这样,就不是一般地表现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而是透过崇祯个人思想性格的悲剧,更深一层地显示了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明王朝无可挽回地崩溃下来的时代历史特征。这种艺术描绘,实在意蕴深沉,耐人寻味。它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也不能不信服:《李自成》这部长篇所表现的种种悲剧内容,不仅是明末社会的真实再现,同时又是从历史生活的实际出发的一种出色创造。
《李自成》所写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悲剧,不是零碎的、孤立的,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具有艺术和谐的美。大悲剧中套着小悲剧,小悲剧的演进受大悲剧的支配和制约,而小悲剧的完成又有助于大悲剧的推演和发展。这些小悲剧的出色表演,与诸多社会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它们与各种事件和人物交织在一起,构成明末社会错综复杂的历史悲剧环境,大大有助于显示正在酝酿、发展中的李自成大悲剧。
例如,卢象升的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民族战争的严峻形势,展示出农民战争与民族战争相互纠结的现实社会背景以及明朝统治阶级面临的严重内外矛盾,在读者心理上投下了民族战争的浓重阴影,为李自成最后军事上遭受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准备了间接的伏笔。
张存仁一家的悲剧,又从另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明末社会危机的无限深重,崇祯朝廷的黑暗、腐败达到何等惊人地步,人民面临一场空前的浩劫,同时也显示出李自成随着地位的变化开始增长的某些严重消极因素。
慧梅奉“父帅”之命与袁时中完婚的悲剧,则暴露出李自成上升时期麻痹大意,丧失警惕,以至头脑昏昏、滥用权术的失利,并且表明即使像李自成这样的农民起义英雄,思想中也仍有不少封建专断的东西。
总之,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事业发展中必定面临的社会环境的制约和思想意识的缺陷,充分预示着李自成大悲剧的必然结局。这种种悲剧,无论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如卢象升的悲剧和张献忠的悲剧),还是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如慧梅的悲剧和张存仁一家的悲剧),都是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的有机融合,它们既有各自独立的艺术价值,同时又构成了李自成大悲剧高度典型的历史环境,布置了异常浓重的悲剧气氛,使整个大悲剧闪现出灿然夺目的光辉。这种种悲剧,从不同的生活矿层,不同的历史视角,不同的思想深度,不同的艺术容量,蕴蓄着、丰富着、扩展着、补充着李自成大悲剧巨大的历史内容和强烈的社会意义。这是《李自成》全书悲剧艺术的又一重大成就。
三、悲剧结构别出心裁
为了完成李自成的大悲剧,在艺术表现上自然要求作者采取大悲剧的结构和布局。
《李自成》一开篇就是惊心动魄、壮怀激烈的潼关南原大血战。这个艺术的开篇,犹如一部大型交响乐的基调,为这部大书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风貌定了调。在明末崇祯王朝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情势下,勾画出了李自成起义的典型历史背景;李自成在最危厄的境遇下,又犯了一个致命的大错误,从而渲染出极其豪迈、悲壮的艺术气氛;在李自成仅率十八骑突出重围的艺术氛围中,展示出农民起义军的命运多舛与慷慨悲歌的咏叹旋律……总而言之,无论从环境条件、艺术氛围、人物色彩、社会风貌以及艺术表现等诸多方面,都为全书确定了悲剧的基调。
这个悲剧的基调,不是低沉阴暗的、悲悲切切的,不是使人感到压抑的、凄婉的,而是充满着慷慨激昂的豪情,舍身取义的壮志,因而是深沉而悲壮,令人感奋、使人惊醒的,整部作品是豪壮、悲愤、感人肺腑的大悲剧。
《李自成》的铺叙,不像过去常见的悲剧故事那样,习用陈词滥调,情节落入窠臼,采用单线发展,平铺直叙,而是以多线条的复式发展来推动情节,展开故事:以李自成农民军的斗争生活为作品的主线,辅以张献忠等起义队伍的武装活动和崇祯王朝的宫廷生活两条副线并行发展;从第三卷开始,清军正式登场,则又增加一条副线……这种复线式的推动故事发展的方式,使李自成大悲剧的历史环境扩展到了明末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便于揭示不同的生活侧面,深入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李自成》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刻性、广阔性、丰富性,都不是平常的作品可以比拟的。这是李自成大悲剧历史画卷的又一突出成就。
为了完成多线条的复式发展,作者采用了按单元结构的方式。以内容相联系的不同章节构成单元,然后根据这些单元的内在联系加以组合,使每一卷、每一册形成一个各自独立的统一整体。这种组合方式,既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表现形式,又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艺术结构方法,有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灵活性,又有和谐统一、完整匀称的艺术美。这种结构,是《李自成》艺术创造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展现丰富多样的历史面貌,有助于深掘历史生活的多种内容,对于完成李自成的大悲剧,提高李自成大悲剧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是有重大作用的。
根据作者的设想,《李自成》到第五卷结尾达到高潮,才最后完成了这部悲壮宏伟的历史大悲剧。在“尾声”里,高夫人所率领的李自成残部被清军包围,一场熊熊大火焚毁了起义军最后的营寨,从而也焚毁了李自成一生的事业和全部的理想。从李自成在南原危机中的崛起,到最后的全军覆没、清王朝统治着整个中国大地,一幕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大悲剧,实在撼人心魄、感人肺腑!作者有关这个悲剧结构的通篇设计,是首尾呼应、相当完整的。
悲剧结构的完整与悲剧主题的显现,很重要的还在于整部作品基调的连贯性和艺术构想各个环节的协调一致。在第一卷里,李自成起义军正处于创业中最艰难最危急的时期,如果只是悲哀和感伤,缺少豪迈的气概和宏大的志向,那是不可能把农民起义的斗争从困难引向顺利发展的一个转机的。这一卷里只写卢象升的悲剧,侧重点在点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动向,而用了较多的篇幅表现起义将士豪迈和悲壮的气质。即使这样,小说在开始亦已勾画出了悲剧的环境,渲染了悲剧的气氛,给了人们鲜明的印象。第二卷,李自成起义由困境走向转折和发展的阶段,悲剧气氛的渲染较多放在崇祯与皇亲贵戚、朝廷大臣之间的复杂矛盾以及宫廷生活纷繁而又无法解决的纠纷之中,同时,透过王吉元的悲剧反映了农民阶级狭隘眼光的局限性,从李自成与张献忠不能联合抗敌看到李自成大悲剧的另一个侧面。到了第三卷,李自成起义正在迅猛发展的阶段,但小说却大大加重了悲剧的成分。这里有洪承畴降清的处理,有张存仁一家的悲惨遭遇,还有用很长的篇幅贯穿着写慧梅的悲剧,等等。如果说,第一卷侧重在定下了整个悲剧的基调,到第二卷则着重从另一个侧面去加深悲剧的气氛,而且为整部作品更为广阔的社会大悲剧作了较多的艺术准备,那么,在第三卷里,这种悲剧的旋律更为反复地出现,如多棱镜似的,从许多不同的方面相当充分地透视和加强悲剧的主题,相当有力地展示和突现出李自成大悲剧的必然发展和历史归宿。如果把《李自成》看作一部大型交响曲,那么,随着乐章的推进,其悲剧的基调一次比一次突出,主旋律一次比一次鲜明,它们多角度、多侧面地谱写出李自成大悲剧的动人主题。
《李自成》这种多卷集的长篇悲剧结构,在中外文学史上也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在我们见到的一些描写农民战争悲剧的长篇中,大多是比较单一地在叙写农民起义和武装斗争的整个过程或主要经历,却较少采取《李自成》这样繁复多变的结构来表现。也许是李自成起义面临的复杂局面决定了作者的艺术构思,也许是明末清初变化动荡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小说的结构方式,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繁复多变的单元结构,在中外众多小说创作中,可以说是姚雪垠一个别出心裁的独特创造。
谈到国外,自然使人想到描述奴隶起义的历史长篇《斯巴达克思》。这也是一部著名的历史悲剧。也许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这次奴隶暴动决定了这部小说的结构比较单纯,无论从这部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还是揭示历史面貌的深度来说,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李自成》的结构和它所表现的主题意义的优长之处。有人曾经怀疑,《李自成》采取如此卷帙浩繁的庞大结构和众多篇幅来表现这次农民大起义是否有此必要?当然,我们不能说已出三卷大书没有繁冗之处,没有某些较次要的生活事件和艺术情节占去了过多篇章的现象存在。但是,从整部大书的宏伟结构去表现作者拟定的丰富多彩的悲剧主题,小说的这种艺术独创性还是堪为人们称道的。
姚雪垠可以说是一位长于写悲剧的作家。他较早的一些作品,从短篇《差半车麦秸》,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重逢》,到长篇《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都在不同程度上结合时代的脉搏,绘状、烘托了一种悲壮或凄婉的气氛,刻画出一些性格较为鲜明的悲剧性人物,结局往往含有某种发人深思的悲剧意味。《李自成》是作者进入成熟时期后,在新的高度上发扬自己长处而创作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作者决心花几十年心血,结晶出这部与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样悠久的文化传统相称的长篇巨著。虽然它的后两卷有待完成,全书也有待统一修改定稿,但从作者已做的艰巨准备和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的壮志宏图定能实现!
原载香港《星岛日报》副刊,1985年8月14、21日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