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绿化树》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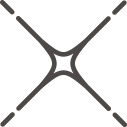
早就想读《绿化树》,却因刊物被争相传阅而延误了。这次是先看了批评文章《〈绿化树〉的严重缺陷》,注射过“思想防疫针”以后再去读的。不料读完之后,仍不禁要“欣然认可”:它是一部写得既厚实又深沉的好作品。
《绿化树》真实地、艺术地写出了我们历史的严峻的一页——二十多年前的艰苦年代。由于我们指导方针失误而导致国家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的年代。“普遍性的饥饿正使千千万万人共享着同样的命运。”小说通过主人公章永璘——一个在“左”倾思想下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所见、所闻、所行、所感,真切感人地反映了那段令人难忘的生活。章永璘在贮存的两个稗子面馍馍被老鼠吃光以后,没有力气动弹,竟然感到:“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饥饿成为“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这仿佛难以想象,然而有过这类似经历的人都会承认:它是一种极真实的体验。小说没有回避我们国家和人民当年经受的困苦、挫折、艰辛,这使它非常贴近于历史,显示出十分严峻的现实主义色调。但是,贴近历史又不意味着贴地爬行。《绿化树》并没有像有些作品那样去写饥饿年代人们吃虫子、吃蝎子一类情节或细节。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去透视那段历史,使小说获得了温馨的情愫,幽默的笔调,在严峻中时时透露出暖意和诗趣。冰冷和愤怒都会扼杀幽默感;幽默来自与历史的距离相联系的宽阔襟怀和乐观自信。“晚上,我万分小心地钻进棉花网套里,就像把一件珍贵器皿放进衬着缎垫的锦匣中一样。”——读到这类描写,我们恐怕都禁不住会受作者情绪的感染。同样,像下面这段文字:
这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虱子感觉到热气,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虱子在不咬人的时候,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动物,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与贫穷——还有种活生生的东西在抚摸我!我身上还养着点什么!
当我们诵读的时候,一种混合着悲哀与温暖、难过与幽默、黯然神伤与忍俊不禁的复杂情绪,也会从心底油然而生。它给人的感觉,绝不是单纯的悲抑与痛苦,而是透露出亲切与乐观。这是饱含情趣的生活,又是真正动人的艺术!尤其可贵的是,《绿化树》在表现饥荒年代的艰苦生活时,还着力表现了劳动者淳朴高尚的心灵与主人公不断解剖自己、“超越自己”的执着追求。这就不仅写了苦难与不幸,更写出了美好与希望。作品中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就是三个塑造得相当出色的劳动者形象。马缨花虽然在一些人的舆论中蒙着不洁的灰尘,但她那黄土高原上旋风般的泼辣性格,善良直率、助人为乐、急人所难的可贵品德,面对爱人立下“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的坚贞誓言,以及平时爱“帮着娃娃多的妇女补她们男人的衣服”的热情行动,无不在读者心中熠熠闪光,使人难以忘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这样刚强爽朗、机智明快的妇女形象,在我们的文学中似乎还是第一次出现,她可以说是张贤亮同志所做出的新贡献。海喜喜的粗野、雄豪、蛮悍,认清事理后又能通达大度,极其诚挚,乃至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人,也写得颇有感染力。谢队长这类形象的出现,更表明农村基层干部中有一批人能够代表群众利益,从实际出发抵制各种错误倾向。正是从这些人物身上,主人公章永璘深切感受到:“人心里,竟有那么绚丽的光彩!他们鲁莽的举止,粗鄙的谈吐,破烂的衣衫,却毫不能使他们内心的异彩减色。”本来,章永璘与马缨花的爱情最后是个悲剧,他们的结局使许多读者真想为之一哭,然而,整个作品的基调读起来却并不压抑,根本原因就在于小说挖掘了生活中的美好情愫,写出了以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为代表的劳动者的美好心灵。
应该怎样看待《绿化树》中关于章永璘思想历程的描述?小说是否在这方面犯了“贬低知识分子”的原则性错误或者存在“对苦难的病态崇拜”之类的“严重缺陷”呢?
这需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生活本身是极其复杂的。作者显然无意于用一个章永璘来代替整个知识分子。按照小说的描述,章永璘是个特定的人物: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虽然在新中国成立时只有十三岁,却并非没有接受过家庭的影响。作品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具体写到了这样一些场面:
我小时候,教育我的高老太爷式的祖父和吴荪甫式的伯父、父亲,在我偶尔跑到佣人的下房里玩耍时,就会叱责我:“你总爱跟那些粗人在一起!”
——第十一节
……在一间讲究的天蓝色壁纸贴面的大房间里,在凤尾草图案的绿窗帘下,在大理石镶边的法兰西式的壁炉旁边,我的一个伯父坐在棕色的皮面沙发里,我坐在放在地毯上的一只蜀锦软垫上。他晃动着自己调的加冰块的鸡尾酒,向我说摩根家族发迹的故事。据他说,老摩根从欧洲老家飘流到北美洲时,穷得只有一条裤子,后来夫妇两人开了一爿小杂货铺。他卖鸡蛋的时候从来不自己动手,而叫老婆拿给顾客看。因为老婆手小,这样就衬得鸡蛋大一点。正是由于他这样会盘算,他的后代才建立了一个摩根金融帝国。
“听到没有?做生意就要这样精,门槛不精不行!”这位证券交易所的经理端着高脚酒杯教育我,“谁倒闭了谁是憨大(念‘杜’音),能赚钱才是英雄!”
——第十四节
正因为回忆起了幼年时资产阶级家庭对自己的这类教育,主人公自然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态度,联想到“老摩根会利用人的视觉误差把鸡蛋变大,我会利用人的视觉误差把打的饭变少;摩根们会盘算,我的算盘也很精:用钉子代替稗子面,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和交易所的‘买空卖空’一样,一倒手就赚了两块钱”,由此而为自己身上潜在的某些打着阶级烙印的习性感到“大吃一惊”。这类描写,我以为是很有历史真实性的。在当时条件下,章永璘产生这类想法毫不足怪,它正体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与剥削阶级有瓜葛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虔诚态度。即使从今天来看,这种情况恐怕也不能简单地一概斥为“‘左’的印记”。知识分子固然不必妄自菲薄,但如果意识到自己身上真有旧的精神负担,那还是应该正视和警惕的。从这方面说,《绿化树》中有关章永璘及其思想历程的描述,总体上还是真实的、成功的,有些描写甚至是很深刻的。尽管《绿化树》的实际艺术表现与作者在题记中谈到的创作意图还有距离,但小说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便在于写出了有某些旧的负担然而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在被历史的旋风不正常地抛进可怕的旋涡、陷于灭顶之灾以后,怎样从劳动人民与马克思著作中获取救援的力量,从而逐步摆脱旧的负担这一艰苦历程。章永璘的个人经历是特殊的、非常的,他那令人战栗的遭遇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再重复;但是,章永璘经历中所包含的一些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例如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又是不应该简单否定和抛弃的。只要读一读20年代彭湃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我们就会强烈地感受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亿农民的国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过程中提出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不是毛泽东的过失,而是他的功绩(毛泽东在40年代不提出,其他人也会提出来)。在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犯过片面性的错误:在一个时期内,只讲知识分子必须向农民学习,不讲或少讲农民也必须向知识分子学习,只讲知识分子有弱点,不敢讲农民也有弱点,不敢讲受过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有高出农民小生产者的地方。我们只肯定那些写了知识分子向农民以及农民出身的干部学习的作品(如《闯关》《三个朋友》《我的第一个上级》等),而去批判那些写了知识分子纠正农民以及农民出身的干部弱点的作品(如《在医院中》《我们夫妇之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认为它们歪曲丑化了劳动人民。这个历史教训一定要牢记。但在纠正这种片面性、记取以往的历史教训时,我们绝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好像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根本没有意义,好像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结合本身就是一种“左”的思想(当然,这种结合在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方式)。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证明:知识分子需要磨炼自己,需要改变自命清高、孤芳自赏、个人主义等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思想感情,这绝不是什么“空想社会主义”,也不是“对知识分子过分的贬低”。《绿化树》主人公章永璘说得好:“即使一个人把马克思的书读得滚瓜烂熟,能倒背如流,但他并不爱劳动人民,……那这个人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根指头也不是!”爱不爱劳动人民,这还是问题的关键和根本!主人公之所以产生“要追求充实的生活以至去受更大的苦难的愿望”,正是同这个根本点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就扯不上什么“对苦难的病态崇拜”了。
《绿化树》对章永璘思想历程的描述并非没有弱点。以第二十六节描写的主人公那场猛烈的内心风暴为例,生活的内在根据就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在相当成熟的爱情基础上的一次拥抱,何以竟会使章永璘羞愧、痛苦到要自杀,认为自己已经“向一个深渊坠落”?为什么主人公要莫须有地谴责自己“心怀恶意地去扮演着乞讨者的角色”?即使用人物处于特定的恶劣环境中所产生的虔诚悔罪的畸形心理来解释,似乎也还不足以完全令人信服。更何况作品起先所写的章永璘,已经在哲学讲师的启发下,开始相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了这个样子”,是因为和“我们的命运”相连的“国家的命运”方面也发生了问题。或者是作者把章永璘虔诚的自我谴责写得过了头,或者是作者有时把章永璘政治上又写得过于清醒——二者似乎必居其一(甚至可能兼而有之)。至于作品结尾提到的章永璘是个“接受过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知识分子”这一说法,可能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封建时代文化并不都是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时代文化也并不等于资产阶级文化。就作品所写章永璘接受的文化而言,实际上相当复杂,而且其中有不少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接受的影响,不应该下那样简单的断语。即使如此,所有这些弱点(如果是弱点的话)加在一起,充其量不过是个分寸感问题,并不能由此引出胡畔同志做出的那么严重的结论。胡畔同志的文章强调反“左”,而他所采用的立论方法——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不从作品形象整体出发,这些却都打着很深的“左”的印记,使人们感到面熟得很。看来,真要肃清“左”的影响还不那么容易,一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容上准确地做出分析,二要从主观运用的方法上剔除旧的遗留。这两点,才是我们这次讨论《绿化树》的意义所在。
1984年国庆节
原载《文艺报》1984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