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文学”的出色代表

——伯尔和他的《洛恩格林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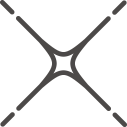
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德国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战争,不仅对欧洲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祸。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德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伯尔、博歇尔特等一批新涌现的作家痛定思痛,纷纷写普通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写城市变成废墟、田园成为公墓的残酷现实,写小人物因战争而在肉体上、精神上蒙受的深重创伤。这便是人们称为“废墟文学”的浪潮。而亨利希·伯尔,则是这个文学潮流的重要代表者。
亨利希·伯尔是当代西德最著名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17年出生于科隆的木匠家里,1985年7月病逝,他一生当过学徒,做过工,还在科隆市政府当过人口统计员,尝过许多同辈人共同尝过的痛苦、辛酸。他记忆中最早的事情,是看到兴登堡军队神情沮丧地带着马匹、大炮,战败归来的情景。1939年,他二十二岁时,被法西斯军队拉去当兵,经历了六年之久的战争生活。战争结束后还曾在战俘集中营里待了几个月。对于这场战争,他是厌倦的、深恶痛绝的。由于他这种下层生活的经历,许多被损害、被蹂躏的小人物,就成了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早期所写的中短篇小说,如《列车正点到达》《流浪人,你若到斯巴……》《洛恩格林之死》《我的悲哀的面孔》《干粮袋历险记》等,都被称为“废墟文学”。对此,作家直认不讳。他说:“给这种文学起这样一些名称是有道理的:战争打了六年,我们从战争中返回家园,我们见到的是一片废墟,而我们写的也是这些题材。”“事实上,我们所描写的人们都生活在废墟之中,他们刚经历了战争,男人和妇女都在同样的程度上蒙受了创伤,儿童也是如此……他们绝不是生活在完全的和平之中,他们的环境,他们的情状,他们自身的一切和周围的一切,丝毫不具牧歌与田园诗的性质。作为作者,我们感到自己同他们如此息息相通。”(《“废墟文学”自白》)可以这样说,伯尔等人的“废墟文学”,实际上也是人们经历了一场巨大灾难之后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是一种揭露和谴责法西斯战争的文学。
《洛恩格林之死》发表于1950年,是伯尔短篇小说中脍炙人口之作。他用极凝练的笔墨,通过一个孩子悲惨的死,反映了法西斯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虽然此刻战争已经以德国的失败告终,但战争留下的创伤——死亡、饥饿、贫穷、混乱,却并没有成为过去。食物奇缺,“五十公斤煤只能换两块巧克力糖”。生活的极度困难,不但迫使抬担架的人想占有一条并非属于他的旧床单(“这年头,床单也可以卖不少钱哩”),还推动医生们相互勾结,盗卖医院里的强心剂等紧俏药品,以致小施兰茨因无药可治而终于死亡。社会秩序继续混乱,“谁都随时有被抓去的可能”。洛恩格林的父亲、哥哥神秘地流亡在外不露面,而他的母亲则死因不明:“谁知道,也许是纳粹杀死了她,她曾经狠狠地咒骂过……”也许是“卢森堡兵把她打死了,不,是俄国兵……”作品选择一系列真切典型的细节,有力地烘托点染出战后西德的环境气氛,显示出战争的严重恶果。一个短篇小说能触及战争造成的这么多问题,概括性这样强,是颇不多见的。
这篇小说最成功之处,还在从受伤的洛恩格林的角度,写出苦难中三个孩子相濡以沫的动人情景和小主人公善良纯真的美好心灵。洛恩格林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儿童,在正常情况下,他也许还只懂得在父母兄姐照料下顽皮,撒娇。然而,战争造成的残酷命运,使他早熟、懂事地独自担负起五岁的阿道夫和八岁的汉斯两个弟弟的生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躲过卢森堡兵的枪弹,爬到正在行驶的火车上去偷煤,以此换取食物。终于在最后一次行动中摔成致命的重伤。他短促的一生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尝过甜丝丝的味道。全身“瘦得真可怜,像只老鹅似的皮包骨头……”他从不知幸福为何物,只是在被打了止痛针以后,才清除剧痛,产生一种幸福而温暖的奇妙感觉。在临死前的半昏迷状态中,他牵挂着家里无人照管的两个小家伙,为自己平时管他们太严而自责,并且念念不忘将来要为弟弟们“买一些这种针管里的幸福”,使他们得以分尝。请看作品所写的小主人公以下一段心理活动:
那一针打得可真好,他感觉到被扎了一下,突然幸福就出现了。这个脸色苍白的护士,一定是把幸福装在针里了。他听得很清楚,她把那么多的幸福装在针里,太多了,真是太多了。……幸福真是美妙,也许可以给小家伙们买一些针管里的幸福,一切不是都可以用钱买吗?……买面包……堆得像山一样的面包……
读到这里,不禁令人心酸得潸然泪下。幼小无知的孩子临死前关于“幸福”的这番憧憬,实际上就是对希特勒发动的法西斯战争的血泪控诉!这些篇章里浸透着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伯尔向来主张,“要用人的眼睛来看事物”。他认为:“作家的眼睛应当是人的、公正不阿的。”他谴责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不是用人的眼睛来看世界,而是兽性地歪曲地看待世界。正是这种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构成了伯尔小说真挚感人的思想艺术力量的核心支柱。
在其他小说里,伯尔也从各个角度写出无辜的人们怎样成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战争的牺牲品。
中篇《列车正点到达》里那些性格各异的士兵,几乎每人都有精神伤痕。他们极其厌战,预感到前途凶险而想竭力躲脱,最终却一个不落地在开赴波兰前线途中进入死神的掌心。
短篇《苍白的安娜》中,那位房东太太失去了儿子,她的未婚儿媳安娜失去了爱人。安娜原先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一次爆炸中被气浪甩进橱窗,“她的脸完全毁了”,脸上布满了有点发青的放亮的疤痕。
《干粮袋历险记》中,年轻的钟表匠约瑟夫·斯多伯斯基潜心于技术研究,整天摆弄数不清的齿轮;被征当兵以后,还随身携带那个包着油封齿轮的小包裹,对战争丝毫不感兴趣,他在昏睡时被一发炮弹打死。不料,他所属连队的士兵几天后在附近英军壕沟里发现了他的干粮袋。连长就认为斯多伯斯基在那天冲锋时深入敌阵,血战身亡,尊为英雄。真是莫大的讽刺。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中那个中学生,当兵刚三个月,就失去了双臂和右腿。他被抬回到母校,看到自己当初受军国主义者布置写下的一段欺骗性宣传文字:“流浪人,你若到家乡,请报告斯巴达公民们,我们阵亡此地,至死犹恪守他们的命令。”现在他不但不被古希腊人这段铭文激动,反而感到如梦初醒,震撼万分。他羞于把自己的负伤与“祖国”这类神圣字样联系起来。惨重的血的代价,使他终于有所觉悟。
伯尔在揭露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战争的恶果时,把谴责的矛头对准纳粹头子和一小撮战争贩子。他说:“应负罪责的一小批人欠下的血债太多了,时至今日,还剩下一些没有偿还。”(《关于我自己》)在《“废墟文学”自白》中,他还说:“我们只需睁开眼睛,随便向哪里望去,看见的都是破坏,这一切都要记在这个自称阿道夫·希特勒的家伙身上。”所有这些,都说明伯尔的“废墟文学”忠实地道出了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艺术上,伯尔的作品以传统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他特别倾心于查理士·狄更斯,坚决反对人们玩弄捉迷藏的游戏;反对用玫瑰色来粉饰现实,把同时代人诱骗到田园诗中去。他的小说敢于正视现实,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写法细腻逼真。同时,伯尔也吸取了意识流小说、心理分析小说的一些长处。《洛恩格林之死》最动人的部分,便是顺着主人公意识、潜意识的流动来写的。洛恩格林先是因剧痛被制住而感动得流泪,接着想起了小家伙们,担心他们因无人照料而挨饿,责备自己过去对他们管得太严,想起他们“一听到楼梯上有声音,就激动地跳起来,把苍白的脸贴到门缝上”的情景,为自己这么晚不能回家而感到难过;又想起白天避开卢森堡士兵的监视溜上火车的情形,仿佛自己还在火车上紧张搏斗,直到摔下来失去知觉,想到“要不要告诉护士,他的父亲在哪里,他的哥哥胡伯特夜里上哪儿去了”;然后思路又回到弟弟们身上,学校的校长身上……这一切,既有意识流的跳跃,又极其亲切自然,并且完全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洛恩格林善良坚强的性格。《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这一篇,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意识流手法来完成。作品从受伤者被抬回母校写起,顺着“我”的五官感觉和思路逐步展开,写得异常真切生动。表现“我”从怀疑到断定确是回到母校这一过程时,把“我”眼前所看到的东西和受伤后肉体的异常感觉结合着写,水乳交融,浑为一体;人物的内心独白是顺着事情的发展和意识的流动来写的,始终紧紧围绕母校这个典型环境描叙自己的感觉和心理,联想紧凑,清晰,连贯,与现代派作家意识流手法的排斥理性、艺术效果晦涩混乱很不相同。这也表明,在运用心理分析与意识流技巧方面,伯尔已经达到了相当圆熟的境地。
伯尔的小说严肃,深沉而又诙谐、亲切。他能将辛酸和幽默,眼泪和笑声统一在一起,用诙谐的调子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悲哀,因而构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洛恩格林之死》以外,抨击纳粹政权的短篇小说《我的悲哀的面孔》,也可以看作这种风格的一个代表。小说中的“我”曾因一副“高兴的面孔”触犯了纳粹法令而被判刑五年。出狱后的第二天,当“我”站在港口观看海鸥翱翔的时候,又因“悲哀的面孔”再次受到警察的逮捕,被判处十年徒刑。“我”因刚出狱,一身污垢,没刮胡子,衣衫褴褛,又触犯了一条新公布的法令。那条法令规定,人人都要干干净净,胡子刮得光光的,露出一副高高兴兴、吃得饱饱的模样。“我”被判刑后想道:如能熬过此后的十年,“真得想办法什么面孔也别再要了”。这是借“我”的遭遇,道出了在法西斯政权的控制下,人民动辄受惩、无法生存的可怕处境。小说用幽默、夸张的手法,对纳粹政权荒唐的愚民政策作了极其尖刻的讽刺。伯尔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历史上极其惨痛的大悲剧,却对人类历史本身并不悲观,他的作品具有内在的乐观温馨的情愫——这可能就是伯尔独特风格的一个最基本的构成因素。
1985年7月于北京
原载《人民文学之友》1986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