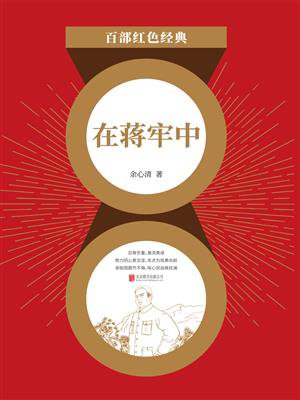事件爆发的前夜

我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到北平的,到被捕的时候,恰是一年零二十四天。在这一年多当中,中国的问题,有着很多重要的变化。当我离开南京的时候,正在马歇尔九上庐山的当儿,这以后马歇尔的回国,军调部的撤销,张家口、延安的被占,一连串的事件,使得独夫和好战分子们,更放心大胆地进行大规模内战,“戡乱令”也应运而生,各地的民主运动,受到了更严重的摧残,大规模的逮捕,成了报纸上常见的新闻,北平的政治情况,急转直下地恶化下去。
在我被捕的前一个月,北平的特务们,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深夜逮捕。许多文化人、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以及给叶剑英治过牙齿的牙医生——那位从来不过问政治、彬彬有礼的公务员,也被捉进去了。这是暴风雨的前奏曲,也是我被捕前的一个信号。
不过,这些现象,在革命过程中,是无可避免的,在黎明之前,“夜”总是分外黑暗,历史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凡是向时代开倒车,想“残民以逞”的独夫们,不过都是在努力给自己掘坟墓。这时候的蒋介石,正趾高气扬,以为他“得势了”,“得时了”。他深深地了解了“干爸爸”的意思,搭上了这根做奴才的线,便倒行逆施,为所欲为。你等着罢,蒋介石!垮台的戏在后头呢!曾有一次我看到了风筝摇曳在高空,我就想到了蒋介石,我就这么写了:
不要炫耀你飞得高,
若不是那阵西方的风,
你怎么会爬上云霄?
当心断了那细麻线,
看谁从高空里——
翻筋斗,摔跤!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我正在北平一个很老的饭馆——东兴楼——吃午饭,刚刚拿起筷子,就有一个茶房进来对我说:“您有一个电话。”当我去接听的时候,“绥署”一个旅级先生告诉我说:“孙主任(连仲)要和你说话。”我心里很奇怪,他为什么在这时候找我?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沉重而急促,这好象预兆着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
“王冶秋现在在哪里?我要见他。”他问我。
“有什么事找他?”我反问着。
这时候他吞吞吐吐地说:“我要请他替我写一篇文章,希望愈快来愈好。”我告诉他今天早晨我请他和周范文(“绥署”少将参议)给许多大学教授们送八月节的礼物去了,现在他在谁那里,很难说定,并且,在城外有两个一定要去的地方,“清华”和“燕京”,可是那是没有方法用电话找到的。他们回来,最早怕也要到黄昏。
当天下午约莫三点半钟的时候,我在一个国际俱乐部里打网球,忽然有一个仆役来告诉我:“孙主任有电话请你说话。”这时候我心里便嘀咕起来,感到了老大的不快。
“请你立刻到我的家里来!”这是他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的一句话,说话的声音是那么急促。
我放下耳机,匆促地披了一件西服上身,便跑到东城角他的公馆里去。他的副官告诉我:“孙主任因为等不及,到‘绥署’去了,请你到那里去。”这时我更怀疑起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到了“绥署”,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坐在一张沙发上,涨紫了脸(遇到严重问题的时候,他的脸就变成了猪肝色)。他请我坐下,好半天没有开口,当他猛然抬起头来,就命令他的副官:“你们走开!不要站在我门口!”这时我意味到事态的严重。我便问他:“你有什么事吗?”他劈头就说:“王冶秋出了麻烦了,这几天破获了共产党在北平的一座电台,抓到了很多共产党的重要分子,和许多重要文件。其中抓到一个女的,是个重要角色。她在北平非常活跃,打通了各阶层的关系,搜集了各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里面,有一部分是王冶秋供给的。是属于经济方面的,这个女的已供认她和王冶秋的关系,但她并未承认王冶秋是个共产党,仅仅只供给她经济情报。所以我要当面问问他,并要把他送交张家耀(李宗仁‘行辕’第二处处长,管情报的)处问话。”停了一下,他叹息地说:“这次电台的破获,查到的文件太多了!”
我当时相信王冶秋不会有什么“绥署”的军事情报泄露出去,因为他与军方毫无接触,所以我便对孙说:“这是不是一件诬陷的阴谋?而王冶秋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你如果把他们送去,来一个苦打成招,是会造成冤狱的。”他说:“不会的,叫王冶秋安心,如果和中共没有什么关系,问问话就可以回来的。”其实这是废话,特务不抓人则已,一抓便不会轻易放过。不过要抓一个少将头衔的参议,在形式上总须打个招呼。也许特务向孙说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这样,则孙给我说的,就是真的了。当时我在心里盘算,在五个月前,我的那个电报是否也在这次破获的文件之中。我们沉默下来,各人都在打点着自己的事,彼此的外表象很沉静,而心里却在忐忑着。
沉默,象沉重的铅块似的,重压着会客厅,我终于站起来告别,他送我到房门口,我们握了一握手,谁知道一个严重的节目,就从这一握手间开始了。从此,我和孙连仲之间,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政治关系上,也永远地分手了。
我为了急于要知道王冶秋与这件案子的关系,即刻跑到了他的家里去。不巧得很,连他的太太高履芳也不在家。我留下了一个便条,请他在回来的时候,一刻不耽误地来见我。恰巧在路上碰见了高履芳,我便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了她,希望她等冶秋回来的时候,尽速作个打算,并约好晚十点以后在我家里会面。
当天晚间,我应苏联驻平领事的邀请去吃晚饭,座中只有我们主客两个。这位领事说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和华语,我们在不断地碰杯中谈了不少问题,谈到第三次大战问题的时候,他问了我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的晚餐延续到十点钟。最后喝过了咖啡,道过晚安便告别了。
我回到家里,差不多是十点半钟,冶秋还没有来。经过了一天波动,这时候疲倦得上眼皮离不开下眼皮,“冶秋为什么还没有来?是不是已被抓去了?”不然,这个时候他该到了。十一点钟了,静静的院落中,风吹下几片落叶,沙沙地响着,却没有冶秋的脚步声。
我困倦得不能再支持,便脱下衣服睡下去了,可是心里万分不安,象大祸将要临头似的,十一点半钟,冶秋终于带着他的太太走进了我的客室!我揉着疲困的眼睛,披上一件棉袍,光着脚走出来,我们彼此脸上都被一种忧郁的表情笼罩着,好象泰山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我问他:“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他说:“办完了事就去找王倬如一同下小馆。”(王倬如也是逮捕对象之一,因为他很机警,在特务抓他之前,已经躲开了。)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和一个中共的女同志发生情报的关系?”他说:“我的女朋友你也都认识,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女朋友,只是有一个男朋友曾经向我要过冯先生在美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我更进一步地问他:“你还有其他的活动没有?因为这个时候,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应当考虑对策。”他坚决地告诉我决没有其他活动。我之所以这样问他,他之所以这样答复我,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经过。他是冯先生(玉祥)的秘书,但冯先生出国的时候,他并没有随着出去,我在南京碰到他,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他告诉我没有任何打算,但为了生活的压迫,已把两个儿子送回安徽老家交给他祖母去抚养,另外两个较小的孩子交给太太带到北平,他希望她能在北平找到一个工作岗位,解决母子三人的生活问题。因此,他自己向南、向北尚未决定。当时我对他说:“我现在是要到北方去,你最好也能同来,我相信能够给你设法找到工作。”他劈口就答应到北方来和我一起工作,只是他要先回安徽老家替他母亲做了寿才能动身。我到了北平就和孙连仲谈到他的工作问题,希望孙能用他作一个随从秘书,给他讲一讲国际和国内的情势,拟一些演讲和会见新闻记者的谈话稿子等等。孙当时满口的应承,所以我就打电报把他约到北平。当我介绍他和孙见面以后,有一位孙的军法处长徐惟烈便当面从中破坏,说他是跟冯先生颇久的人,思想上恐怕有问题。胆小的孙连仲听见这两句话,便立刻动摇起来。我因为对朋友信用的关系,非常恼火,向孙一再地保证他决没有问题,这样勉勉强强地让孙下了一个手令,任命他做“绥署”的少将参议。后来还有人不断地说些闲话,于是孙就不能把他留在身边了,到差不多一星期,就把他派到我负责的“设计委员会”来服务,我便请他主持资料室工作。
提到徐惟烈,他是冯先生一手培植起来的一位军佐,而且有一个很长的时期表现过对冯先生特出的忠实。一个瘦削的白面书生,脱发的前顶,露出一个宽大的额头,灼灼的两眼,不时左右扫射着,充分表现了他的机警、酷辣和一种显露的聪明。一九二九年韩复榘在河南的叛变——这是西北军最初崩溃的信号——他是促成的因素之一。当冯先生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代,他思想变得很“左”,他做过托派张慕陶的干部,我还和他开过玩笑,说他是“典型的红萝卜”——外红内白,把他气得拍桌狂叫,说我太看不起他,侮辱了他。以后蒋介石的特务对他盯过梢,宋哲元把他拘押过,韩复榘在济南坚决地要杀他,我为了友情,挺身救了他一条命。孙到北平之后,他被目为孙的智囊,却没有想到这位“智囊”现在和我站到敌对方向,做了我的对头!伟大的时代,真是一座“洪炉”,把许多人烧成灰渣,同时也把许多人炼成金子。
因为有了上面这一段经过,所以我愿意清楚地知道冶秋真正的活动是什么,这样不但他可以作准备,我也可以作准备。可是冶秋矢口不承认有任何活动。他的太太并且向我解释说:“余先生,如果我们有那样的关系,我们瞒别人,还能瞒你吗?明天早晨,请你陪着冶秋一块儿去见孙,希望他不至把冶秋送到特务那里。”我说:“只要我们确实能把握住这一个问题,就没有什么严重的案件能给特务们发掘出来,那么我想不会在安全上出岔子的。”谈话就这样告一段落。我将他们送到门口。冶秋推着自行车,他的太太一旁低着头走着。我望着他们的两个背影,消逝在夜的黑暗里。我们真是太天真得象一群孩子,警觉性木头一样地迟钝,在被捕的六小时之前,我们还这样地欺骗着自己,愚弄着自己,安慰着自己,而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