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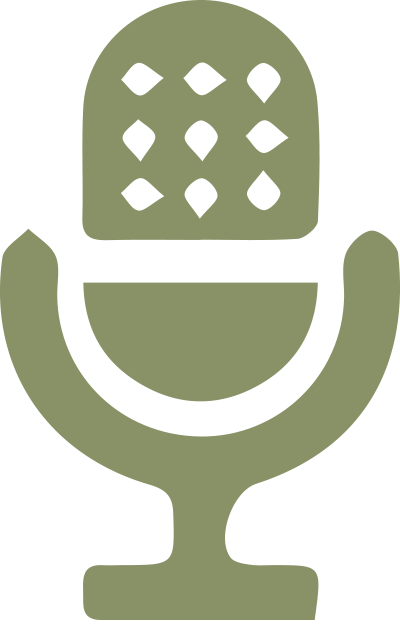
夜里,我躺在一张大床上,身上严严实实地盖着大厚被子。身材高大的外婆跪在地上,默默地祈祷着。这时是严冬时节,外面天寒地冻,刺骨的寒风簌簌地劲吹着,清冷的月光透过玻璃上的冰花,照在外婆那善良的长着大鼻子的脸上,她的两眼闪闪发光。
月光之下,外婆头上系着的绸丝巾发出金属般的光泽,黑色外套垂在地板上,外婆的动作像在跳舞,外套也随着舞动起来。
外婆祈祷完后,脱了外套,细心地把它叠好,之后蹑手蹑脚地走到我的床前,我赶紧假装睡着了。
“又在装蒜吧?小鬼,你没睡着。”外婆轻声细语地说,“听见了没有,我的小宝贝儿?”
她这样讲时,我就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她也大笑起来:“好啊,竟敢耍到外婆头上来了!”她说着抓住被子的边儿,用力一拉,我被抛到空中打了个滚儿,落到了柔软的褥垫上。
外婆哈哈大笑,说道:“小乖乖,怎么样,吃亏了吧?”我们一起笑了起来,笑了很久。

有时,她祈祷的时间很长,我听着听着就真的睡着了,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躺下的。哪天家里有了吵架、斗殴之类的事,哪天的祈祷时间就会长一些,她会把家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
外婆跪在地上,像座小山岗,一开始她讲得很快,听起来有些含糊不清,后来就诉起家常来:“每个人都想过上好日子。米霍亚是老大,按常理他应该留在城里住,可他爹喜欢雅科夫,有点偏心眼儿,就让他搬到河对岸去住,他认为不公平,说那是不毛之地。托梦开导开导这个倔强的老头子吧,让他明白该怎样公平地给孩子们分家。”
她虔诚地磕着头,大脑袋磕得地板直响,然后她又祈求道:“给沃尔沃拉一点快乐吧,她犯了什么罪过?她年轻力壮,怎么落到了这步田地,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她每天都沉浸在悲哀之中。可怜可怜戈列高里吧,他的眼睛越来越不行了,要是他瞎了,就只能去讨饭了,那可太不公平了。他一辈子为我家老头子耗尽了心血,我家老头子是不会帮助他的啊!”她低着头,垂着手,沉默不语,好像睡着了。
“还有些什么?噢,对了,宽恕宽恕我们这些虔诚的信徒们,怜悯怜悯我们吧!饶恕我这个无知的老婆子,我并无恶意,糊里糊涂犯了过错。”
外婆诉说了心里想说的话,心满意足,长嘘了一口气。
外婆经常暗自祈祷,说一切都会好的。
这就让我有些纳闷了,一切都会好?我却觉得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糟糕。
有一次,我从米霍亚舅舅的房门前走过,瞥见身穿白衣服的妮坦列娅舅妈双手按住胸口,在屋子里跑来窜去,大喊大叫:“啊,带我走吧……”
我知道她在喊什么,也明白为什么戈列高里总是暗自嘀咕说:“我就是看不见了去要饭,也比待在这儿强!”我心里想,戈列高里赶紧看不见吧,这样我就可以给他带路,然后我们一起到外面去讨饭,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把这个想法跟戈列高里说了,他哈哈大笑道:“那好啊,咱爷儿俩一块儿去要饭,你就到处吆喝:‘我是染坊行会头子瓦西里·卡萨列的外孙,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们吧!’那可太逗了!”
我注意到妮坦列娅舅妈的眼睛底下有几块青色的瘀伤,嘴唇肿胀,我悄悄地问外婆:“是舅舅打的吗?”
外婆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叹了口气,说道:“唉,是他偷偷打的,该死的畜生!你外公不许他打,可是他晚上偷偷打,这小子太狠毒了,他媳妇儿也太软弱可欺了……”
外婆讲得起劲儿了,打开了话匣子,其实她也想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现在打老婆没以前打得那么厉害了。现在只打打脸,揪揪辫子,也就算了。以前一打可就是几个小时呀,你外公打我打得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复活节的头一天,从午祷一直打到晚上,他打一会儿歇一会儿,用木板,用马鞭,抓到什么就用什么打。”
“外婆,外公为什么打你?”
“记不清了。有一回差点儿被他打死了,我被打得一连几天不能动弹,五天没吃没喝,唉,我这条命算是捡来的啊!”
我听了外婆的诉说,实在感到有点儿惊讶,外婆的块头儿几乎是外公的两倍,难道她打不过他?
“外公有什么绝招吗,他怎么总能打得过你?”
“他有什么绝招呀!他的力气不比我大,可他岁数比我大,又是我丈夫,他是来管束我的,我命该如此……”
外婆虔诚地擦净了圣像上的灰尘。圣像做工精美,镶嵌着珍珠和宝石,富丽堂皇。她小心翼翼地摆弄着圣像,就像表姐卡杰琳娜摆弄洋娃娃一样。
外婆煞有介事地说她常常看见鬼,有时看见一个,有时看见一大群。
“那是大斋期的深夜,那天月光皎洁,四周亮亮堂堂。我从鲁道里夫家门前经过,忽然看到房顶的烟囱旁边坐着一个鬼。它个子很高,毛茸茸的,头上长着角,正在闻烟囱上冒出的香味呢!那家伙,尾巴在房顶上扫来扫去,沙沙地响!我赶紧祈求道:‘小鬼遭殃。’我话音刚落,那鬼惨叫一声,从房顶上一下子栽了下去。那天鲁道里夫家破斋,在家里煮肉,那个鬼闻到肉香味,流着口水就跑来了。”
我想象着鬼从房顶上栽下来的滑稽样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外婆也跟着笑了,说道:“小鬼们就像孩子,顽皮、淘气。有一回我在浴室里洗衣服,一直洗到深更半夜,炉子门突然打开了,一群小鬼从炉子里一拥而出,叽叽喳喳的。这些小家伙,一个比一个小,有红的,有绿的,有黑的,有白的……我急忙向门口跑去,可是它们挤满了浴室,到处乱窜,挡住了我的去路。它们对我拉拉扯扯,这些小东西毛茸茸的,软绵绵的,暖烘烘的,像小猫似的,只是它们都是用后腿走路。它们对我龇牙咧嘴,小眼睛闪着绿莹莹的光,头上长着尖尖的角,尾巴像小猪的尾巴……我吓得晕了过去!醒来之后,蜡烛灭了,澡盆里的水也凉了,洗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一片狼藉。真是活见鬼了!我一闭上眼睛,就又看见那些花花绿绿、浑身是毛的小家伙从炉口跑了出来,满地都是,挤得屋子里乱哄哄的。它们吐出粉红色的舌头吹蜡烛,样子又调皮可笑,又令人毛骨悚然。”
外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来了精神,继续说道:“还有一回,那也是在一个夜里,刮着凛冽的大风,下着鹅毛大雪,我在久可夫山谷里走着。你还记得吗,我曾经给你讲过,你的舅舅米霍亚和雅科夫在那儿的冰窟窿里想弄死你的父亲?我走到那里时,突然听见了一阵吆喝声!我猛一抬头,见三匹黑马拉着雪橇向我飞奔过来。一个个子很高、头戴红帽子的鬼直挺挺地坐在车上,像个木桩。这辆三套马的雪橇从我身边冲了过去,立刻就消失在风雪之中,雪橇上的鬼打着呼哨,挥舞着帽子,大呼小叫。后面还有七辆这样的雪橇,依次冲来,又疾驶而去。马都是黑色的。我那次看见的,可能是鬼在娶媳妇……”
外婆说得有鼻子有眼,形象生动,我不得不信。
我还特别爱听外婆念诗。有的诗讲的是圣母严厉训斥女强盗安加雷柴娃公爵夫人,责令她不要抢劫、殴打俄罗斯人;有的诗是歌颂天之骄子阿列克赛的;有的诗是赞扬战士伊凡的;有的诗是关于英明的华西莉莎、公羊神甫和上帝的教子、女王公马尔法、乌斯达老太婆的;有的诗是关于鞭笞强盗头子、有罪的埃及女人玛琳娅的;有的诗是诉说强盗的母亲的悲哀的;等等。外婆肚子里的诗歌、童话和故事多得很,不计其数。
外婆的胆子特别大,什么都不怕。她不怕鬼,不怕外公,再邪恶、再狠毒的人她也不怕,可就是特别怕蟑螂。蟑螂离她很远很远,她都能听见蟑螂爬动的声音。她常常在半夜三更把我叫醒,说:“亲爱的瓦廖沙卡,你听,有一只蟑螂在爬,快去把它弄死吧,我的好乖乖!”
我点上蜡烛,迷迷糊糊地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满屋子寻找蟑螂,可并非每次都能找到。
“没有啊,外婆。”
外婆用被子蒙住头,一动不动地躺在被窝里,害怕地说:“肯定有啊,我听得一清二楚,你再找找,它正爬着呢……”
外婆的听觉太神奇了!没错,我终于在离床很远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只蟑螂。
“踩死了。”
“噢,你把它弄死了?谢谢你,我的小宝贝儿!”
她掀开被子,露出头来,喜滋滋地笑了。如果我找不到那只蟑螂,她会一整夜都睡不着觉。
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外婆的耳朵极其灵敏,稍有蟑螂的动静,她便会浑身颤抖,细声细气地说:“它又在爬,在往箱子底下爬呢……”
“外婆,你为什么那么怕蟑螂?”
外婆振振有词地讲出了一套她自己的道理:“每一种小虫子的出现,都有一项特定的任务:出现千足虫,说明屋子里太潮湿了;出现臭虫,说明墙壁太脏了;跳蚤来咬你,你就会生病……只有这些黑乎乎的鬼东西,忙忙碌碌,爬来爬去,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它们为什么要来呢?”
外婆还很勇敢。有一次,外婆正跪着虔诚地祷告,外公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声音嘶哑地吼道:“老婆子,染坊着火了!”
“什么?啊!”外婆“腾”地从地板上一跃而起,朝染坊飞奔而去。“娅夫戈尼娅,把圣像摘下来!妮坦列娅,快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外婆临危不惧,镇定地大声指挥着。外公则只是在那里哀号。
我跑进厨房,看见面朝院子的窗户被照得红光闪闪,地板上飘动着闪闪烁烁的火光。
雅科夫舅舅一边惊慌地穿靴子,一边乱喊乱跳,好像地上的红光烫了他的脚似的。他大喊:“是米霍亚放的火,他放完火就跑啦!”
“混蛋,闭上你的臭嘴!”外婆大声呵斥舅舅,把他往门口一推,他一个趔趄(liè qie),差点儿摔倒。
染坊的屋顶上火舌翻滚,烈火熊熊,直逼门窗。寂静的黑夜中,红红的火焰如同花朵一样跳跃着绽放,黑色的烟云在高空中升腾,却挡不住天上银白的天河。白雪被火光映成了红雪,墙壁似乎在抖动,火光流泻,火舌从墙壁的缝隙中窜出,红色的火带缠绕着染坊。突突、沙沙、哗啦……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一齐奏响,大火把染坊装饰成了教堂里美轮美奂的壁画,你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根本无法抗拒它的魅力。
我胡乱抓了一件笨重的短皮大衣,把脚伸进了不知道是谁的靴子里,啪嗒啪嗒地走到门口,跨上台阶。
门外的景象实在让人震惊:火蛇乱窜,啪啪的爆裂声和外公、舅舅、戈列高里的叫喊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
外婆头顶一只空口袋,身披马褡子,飞一般地冲进了火海,她大叫着:“一群傻瓜,硫酸盐会爆炸的!”
“啊,戈列高里,快拉住她,快!唉,这下她算完啦……”外公疯狂大叫着。
话音未落,外婆便从火海里钻了出来,怀里抱着一大桶硫酸盐,躬身飞跑,浑身上下都在冒烟。
“老头子,快把马牵走!”外婆嘶哑着嗓子,边咳边喊,“快给我脱下马褡子,我都快被烧成火人了!”
戈列高里赶紧把外婆身上的马褡子扯了下来,马褡子都烧煳了,特别烫手。戈列高里用铁锹铲起大块儿大块儿的雪往染坊里扔着。舅舅们拿着斧头在他身边蹦来跳去。外公急忙往外婆身上撒雪。
外婆把硫酸盐桶塞到雪堆里,打开大门,向拥进来的人们边鞠躬,边高声说道:“街坊邻居们,行行好啊,快救救这大火吧!大火就要烧到粮仓了,马上就烧到干草棚,我们家要被烧光了,你们家也会遭殃的!来,快掀掉仓库的屋顶,把干草都扔出去。戈列高里,快!雅科夫,瞎跑什么,把斧头、铁锹递给大家!大家行行好吧,保佑你们!”
外婆风风火火地东奔西跑,像个将军,指挥着所有的人。大火好像一直跟随着这个一身黑衣服的老太婆,无论她走到哪儿,都把她照得通体透亮。
沙拉普跑到了院子里,一见火光,唰的一下抬起两条前腿,直立了起来,把外公掀了个大跟头。它的两只大眼睛被火光映得特别明亮,不停地嘶叫着,躁动不安。
“老婆子,快抓住缰绳!”外公大声吼叫。
外婆飞快地奔了过去,张开双臂,大马长鸣一声,顺从地让她靠了过去。“别怕,别怕!不会伤害到你的,亲爱的,胆小得像小老鼠……”她拍着马的脖子,爱抚地念叨着。这个比她大几倍的“小老鼠”,乖乖地跟着她向大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打着响鼻。
娅夫戈尼娅把哇哇哭着的孩子们一个一个抱了出来,然后大声叫道:“阿列克赛找不到了……”
我藏在台阶下面,怕保姆把我弄走。
“好啦,走吧走吧。”外公一挥手,其他孩子都走了。
染坊的屋顶塌了,几根木梁窜起烟柱,直冲天空。屋里面噼噼啪啪,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旋风把一团团的火焰带到了院子里,喷向了铲雪灭火的人们。
大伙儿正在用铁锹铲雪往火上扔,几口大染锅沸腾着,院子里充斥着一股非常刺鼻、辣眼的气味,熏得人直流眼泪。我也呛得受不了,只好从台阶底下爬了出来,正好碰到外婆的脚。
“快走开,小心踩死你。”外婆大喝一声。
突然,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闯进了院子。他戴着钢盔,高高地举着鞭子,大声喊道:“快闪开!”马脖子上挂着的小铃铛急促地响着。
外婆把我从台阶上拉开,说:“闪开,快走,小心踩死你!”
我跑到厨房里,把脸贴在窗户上往外看。可是人群挡住了火,只能看见铜盔闪着金光。
火很快被压下去了。警察把人们都轰走了,外婆走进了厨房。
“谁啊?是你呀,小乖乖,别怕,没事儿了。”她坐在我身旁,一言不发,身子晃晃悠悠。
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只是火熄灭了,没什么意思了。
外公走了进来,在门槛旁停下脚步,问道:“是老婆子吗?”
“嗯。”
“没烧伤吧?”
“没事儿。”
他划了根火柴,微弱的青光照亮了他那满是烟灰的黄鼠狼似的瘦脸。他点上蜡烛,挨着外婆坐了下来。
“你去洗洗吧。”外婆这样说道,其实她自己也是满脸烟灰,身上散发出刺鼻的味道。
外公叹了一口气,说道:“多亏你的智慧,否则……”他抚摸了一下她的肩膀,谄笑地说,“多亏你了!”
外婆苦笑了一下,刚想开口,外公的脸陡然一变,大声吼道:“哼,戈列高里这个坏蛋,都是他粗心大意,这家伙算是干够了,活到头了!雅科夫在门口哭,这个混蛋!老婆子,你去看看吧。”
外婆起身,吹着烫伤了的手指头,快步走了出去。
“看见着火了吧?”外公并没有看我,轻声地说,“你外婆怎么样?她受了一辈子苦,如今岁数大了,又有病,可她还是挺勇敢、挺能干的!唉,可你们这些废物……”
外公沉默了,半天不吭声,他躬着腰掐掉了烛花,问我:“害怕啦?”
“不害怕。”
“没什么可怕的。”
外公心烦意乱,脱掉了肮脏的衬衫,匆忙洗了把脸,跺着脚怒气冲冲地吼道:“谁干的混账事,应该把他抓到广场上用树条抽一顿!放火的人和偷东西的人是一路货色!……小鬼,怎么还不去睡觉,坐在这儿干什么?”
听了外公的话,我赶紧走出厨房去睡觉,可哪能睡得着?刚躺到床上就听到一声号叫,我立刻从床上爬起来,跑到厨房里。我看到外公手拿蜡烛站在厨房中间,双脚在地上来回磨蹭,喘着粗气问道:“老婆子,雅科夫家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爬到炉炕上,蜷缩在角落里,看见屋子里乱作一团。有节奏的号叫声持续着,如波似浪地拍打着天花板和墙壁,一阵高过一阵。外公和舅舅像无头苍蝇似的四处乱窜,外婆把他们撵出了厨房。
戈列高里抱来柴火,填进了火炉,又往铁锅里灌上了水。他忙忙碌碌,晃着大脑袋来回奔走,像一头阿斯特拉罕的大骆驼。
“先生上火。”外婆镇定而有条不紊地指挥着。
戈列高里赶紧找松明子引火,一下子摸到了我的脚,吓了一大跳,惊叫起来:“谁呀?吓死我啦,你这个小鬼!”
“这是干什么呢?”
“你舅妈妮坦列娅要生孩子!”他面无表情地回答。
在我的印象中,我妈妈生孩子时并没有像她这样痛苦地号叫过!
戈列高里把铁锅放到了炉火上,回到我身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陶制的烟斗:“我要抽烟了,为了我的眼睛。”
烛光照着他的脸,他的脸上、身上沾满了烟灰,他的衬衫也被撕破了,从衬衫的破洞里可以看见他瘦骨嶙峋,根根肋骨都露了出来。他的眼镜片破了一块,从那里可以看见他那受了伤的红肿眼睛。
他把烟叶塞满烟斗,听着产妇的呻吟,他心不在焉、语无伦次地说:“看看,你外婆都烧成什么样子了,她还能接生?你听,你舅妈号叫成啥样了,怪可怜的,可得记住她呀。刚开始大家都把她遗忘了,一着火她受了惊吓就发作了。你瞧瞧吧,生孩子有多难,有多痛苦!就是这样,可有些人还是不尊重妇女。你可得尊重女人,尊重你母亲啊!”
我实在撑不住了,就打起了瞌睡。
后来,嘈杂的人声、关门的声音、醉醺醺的米霍亚舅舅的叫喊声把我吵醒了,我断断续续地听见几句奇怪的话:
“快给她喝掺了半杯甜酒、一勺烟渣子、半杯灯油……”
“让我看她最后一眼……”米霍亚舅舅无力地哀求着,喊叫着。他瘫坐在地上,两只手绝望地拍打着地板。
炉炕烧得太热,我从炉炕上跳了下来。我刚走到米霍亚舅舅身边,他突然一把抓住了我的脚脖子,使劲儿地把我推了个仰面朝天,我的脑壳碰在了地板上。
我骂了他一句。他倏地从地上一跃而起,把我拽起来又摔在地上:“摔死你这个小坏蛋……”
我苏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了外公的膝盖上。他坐在角落里,眯着眼,仰着头,摇晃着我,口中低声念叨着:“我们都是上帝的不肖子孙,我们都逃不过上帝的惩罚,上帝不会宽恕我们,我们谁也得不到宽恕……”
他的头顶还点着长明灯,屋子里很亮堂,桌子上点着蜡烛,可曙光已经从窗户里照射了进来。外公低头关切地问我:“怎么样了?哪儿疼呢?”
我浑身酸疼,头很沉重,晕晕乎乎的,可我不想说出来。
周围的一切出奇的古怪:大厅里的椅子上坐满了陌生人,有神甫,有戴眼镜、穿军装的白发老头儿,还有说不上是干什么的一大群人。他们一动不动,一个个都像木头雕成似的。
雅科夫舅舅站在门边儿。外公对他说:“嗨,雅科夫,你带他睡觉去!”
舅舅打了个手势,招呼我跟他走。进了外婆的房间,我爬上了床,他哀伤地说:“你的舅妈妮坦列娅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因为舅妈很长时间没露过面,她既没到厨房吃过饭,也没出过门。
“外婆在哪儿?”
“在那边儿。”雅科夫舅舅朝门外挥一挥手,然后就蹑手蹑脚地走开了。
我躺在床上,偷偷地东张西望,墙角上挂着外婆的衣服,那后面好像藏着一个人。窗户的玻璃上似乎贴着几张人脸,他们的头发都特别长,眼睛是瞎的。我将头藏到枕头底下,用一只眼睛窥视着门口,想看看门口的动静。我捂得太严,又闷又热,感到窒息难耐。突然我想起了茨冈人死时的情景,仿佛看见地板上的鲜血还在慢慢地流淌,又仿佛一个载重的车队从我身上走过,把一切都碾得粉碎……
门终于缓缓地打开了,外婆用肩膀顶开了门,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几乎是爬着进来的。她对着长明灯的清亮的火光,伸出两只消瘦的手,孩子似的哀叫着:“我的手啊,疼死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