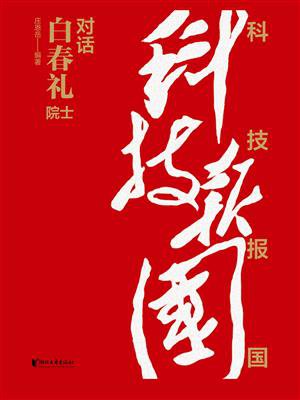03 拥抱困难,迎难而上

庄恩岳:白院士,在您刚回国,准备开展科研工作的时候,您遇到了哪些具体困难?您当时又是怎么克服的?您有什么心得体会想跟当下的年轻科研工作者分享?
白春礼:困难和挫折肯定是有的,所幸我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砺,所以对克服困难既有准备、有韧劲,也有信心。
我中学毕业以后,进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做过汽车司机,这是我走出校门以后迈入社会的第一步。在那个地方,我度过了难忘的青春时光。那段时间里,我虽然不能像在学校里那样系统地学习科学知识,但是那段“社会大学”的经历对我来说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经历了艰苦、痛苦的磨炼后,我对将来生活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挫折,都有了比较充足的思想和心理准备。所以,后来无论碰到什么困难,我只要想起当初那段生活来,就觉得任何困难都是不在话下的。
1987年,对于我来说是个令人难忘的年份,一是我于那年的11月底从美国回国,来到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工作,二是我在当年被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
在我回国后,碰上化学研究所进行正副研究员职称评审,我起初并没想参加:一是因为忙于实验,觉得时间非常宝贵,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做准备工作;二是觉得我还年轻,所里有很多老同志都在等这个机会,我想把有限的名额让给其他同事。但是研究所的领导告知我,如果科研人员具备了高级职称,有利于日后申请科研项目,能更好地开展工作。而且据他说,当时中科院为提拔年轻科技人员,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即通过职称评定委员会的正常考核评审后,只要符合学术标准和提职条件,四十岁以下的同志提升为副研究员,五十岁以下的同志提升为研究员,可不占所里的名额,院里会单独增加名额。于是,我按照申报要求积极做了准备工作,结果顺利通过了答辩,经评定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在当时,三十四岁就评上了副研究员的同志在中科院实属凤毛麟角,而我能取得这一成绩,也得益于中科院的领导为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断层所采取的鼓励支持年轻人的新政策。
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是在国内做的,所以我对国内进行科研工作所存在的困难有一些思想准备。我知道国内申请外汇很难,周期也很长,这样往往不利于需要抢时间、赶速度的科研项目尽快开展,所以我在回国之前,也是做了些准备工作的。
可是,我刚回到国内,准备从事最前沿的科学实验时,还是体会到了创业的艰辛。而且,当年在建实验室时,我也面临着一穷二白的困境,因为单位只给了我一间空空的地下室。我一个人从买电线和工具做起,为防止水泥地面起土,我还特意选了一些很便宜的地板革铺上;为尽量保持整洁,我又在墙上刷了一遍大白。当时,我们所处的大楼正在装修,有些实验室丢弃的物品被扔进了仓库,而我为了节省科研经费,独自蹬上三轮车把别人不要的破桌椅、水管子之类的东西全都拉了回来,自己逐一擦干净,坏了的请木工修一修,刷一遍漆后继续使用。就这样,我回国后的工作灿烂地开始了。
虽然我把工具、桌椅和实验台都准备到位了,但实验用品却成为一大难题。在国外买实验器材时,每个公司都有产品目录,型号和价格清楚明晰。要什么打个电话,商家服务周到,送货上门。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商家根本没有这些服务。如果没有公司准备目录,采购诸如电阻、电容之类的小元器件,就必须自己跑到商店去挑选。当时,尽管北京海淀区中关村有个被叫作“电子一条街”的地方,但是好多东西根本没有。
譬如,我需要64个灰度级的计算机图像板,一问商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灰度级。我几经周折,多方打听,才得知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在现在的北京市上地开发区),开设了一家公司正在研发这种产品,于是我风尘仆仆地前往订购。
譬如,做电子控制系统设备需要购买机箱,我就坐公共汽车从海淀区的化学研究所到位于朝阳区大北窑再往东的一家公司去采购,尽管今天看来那里是繁华地区,但在1987年底的时候,交通并不便捷,那里还是一片荒凉的郊区,坐公共汽车过去都很困难。更无奈的是,我动身前尚不知这个公司是否有货,只是去碰一下运气。我乘车颠簸几十公里后,下车还得步行到处找厂房。当我筋疲力尽地赶到仓库一看,恰好剩下最后一台机箱。验货后如何往回拿,着实让我伤脑筋。我先是要来一个纸箱子将设备装进去,随即有些吃力地将其搬到公共汽车站。当时已是下午五点,正值下班高峰,挤公交车的人特别多,怎么才能把重重的箱子弄上车?我几次自语“等下一趟吧”,但左等右等一直也挤不上去,这种尴尬的情形实在令人沮丧。最后,我在人们的白眼中,抱着箱子挤上公共汽车回到了海淀区的化学研究所。一进门我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多年后,我和别人无意间讲起此事,听者笑问我有科研经费为什么不选择打出租车,我说:“舍不得那些钱。”当时出租车是每公里 1.2元的车费,但我被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后的月工资只有122元,而且我的科研经费还是“借”来的,是要还的。当时也有人认为我缺心眼,但是我认为自己这么做值得,节省经费可以多买些好的设备。
虽然搞科研的人需要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难道我们就不搞科研了?不,我们要克服困难,坚持工作。现在回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我们确实有点“拼命三郎”的感觉。当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时,我总是心无旁骛,每天都是最晚一个从实验室出来的人——好像作者写作需要安静的环境一样,扫描隧道显微镜也需要安静的环境,因为晚上打扰相对少,这时户外汽车、骑车和步行的人都少,数据性噪比更高,科学研究效果好。忙碌到最后,经常是传达室的守门人来敲门提醒我该走了,我才依依不舍离开。有时我为了等一个实验数据,过了深夜十二点才收拾东西离开,这时候大门已经被锁,没有办法,我只好翻栅栏跳出来了。好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年轻人,身强力壮。正是凭借着对科学事业的执着和热爱,并依靠自身过硬的实力,我们整个科研团队不断拼搏,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很大的进展。
所以,虽然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差一些,但是,我的内心是灿烂的,充满阳光,充满激情,充满希望。我相信,哪怕是最没有希望的事情,只要有一个勇敢者坚持去做,到最后都会拥有希望。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难免会遇到艰难的时刻。有些人咬牙度过了这些艰难的岁月,有些人却被小小的困难打败了。用积极的态度面对艰难的时刻,坚持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往往就能走出人生的阴霾天。
宋代诗人刘过有句诗:“精神经百炼,锋锐坚不挫。”著名诗人萨迪说:“事业常成于坚忍,毁于急躁。我在沙漠中曾亲眼看见,匆忙的旅人落在从容者的后边;疾驰的骏马落在后头,缓步的骆驼继续向前。”世界上许多事情皆由人的意志创造。科研工作者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和坚决的行动。
如今,回顾起科研工作初创岁月的坎坷颠沛、艰难困苦,我认为,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有对科学事业的信仰与追求。因为当人有信仰和追求的时候,再苦再累也不觉得,别人再怎么议论,也不会在心里纠结和计较。所以,我觉得当前我们尤其应该强调“科技报国的奉献精神”。在我们的国家经济不发达时,我们要提倡为国家、为事业奉献的精神。现在我们虽然可以给归国人员提供很好的工资待遇和物质条件,但对科技工作者来说,仅有这些仍是远远不够的。年轻人如果一定要看到自己的前途和荣誉才肯付出,那是肤浅的。人生的最大快乐和成就感,往往来自战胜困难的过程。我们可以忍受困难,即使被困难所打败,也不可以轻易放弃,而要千方百计去战胜困难。人有着惊人的潜力,只要立志把它发挥出来,就一定能够渡过各种难关。我们在身处逆境时,适应环境的能力是惊人的。金一南教授写的《苦难辉煌》证明了这一点。科研工作中遇到困难是经常的事情,但这却是好事,因为它会逼着我们去想办法,急中生智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