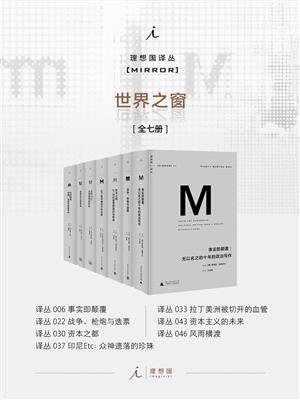八 1857
——消逝的沙贾汉纳巴德
我心不住于这被毁坏之地,
谁能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欢愉?
……
告诉这些遗憾去安住他方,
这颗烧焦的心哪里还有空间?
——出自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扎法尔
 在最后一次流放中写的一首诗
在最后一次流放中写的一首诗

如果说德里特别恐惧价值观的失落,那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所在地区的价值观被摧毁了很多次。数世纪以来,来自北方和西方的侵略者一直被印度次大陆的富足所吸引,而德里正位于侵略者的必经之路上。这一事实使一切都变得脆弱,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东西。至今,一些旁遮普家庭中还保留着一句谚语:“吃下去的才是你的,别的都是(阿富汗)侵略者艾哈迈德沙汗
 的。”这样的想法来自最坏的打算,即更好地生存下来——财富总会被偷走的,所以要用尽手上的东西,至少保证这部分不会失掉。对很多人来说,甚至对那些从中获利的人来说,全球资本主义是另一种外国侵略。尽管它让人们疯狂消费,却平息不了对于失去的焦虑。
的。”这样的想法来自最坏的打算,即更好地生存下来——财富总会被偷走的,所以要用尽手上的东西,至少保证这部分不会失掉。对很多人来说,甚至对那些从中获利的人来说,全球资本主义是另一种外国侵略。尽管它让人们疯狂消费,却平息不了对于失去的焦虑。
通常,人们把德里视作一个古老的城市,认为最开始它的前身是《摩诃婆罗多》( Mahabharata )中描写的印德拉普拉沙(Indraprastha),但是严格来说德里并不是印德拉普拉沙。很多被认为是德里前身的城市在物理空间上并没有连续性,没有一个城市有机地并入下一个。这些城市被入侵者洗劫一空,无法居住,然后被遗弃。或者有的城市建设一完成,就因为缺水而不得不被废弃,然后这些居住点的石头就被运走用来建造下一个城市。每当一个新的政权来到这里,就换一个地方从头再造一座新城,把之前的所有消耗殆尽,任其溃朽。这种对现有存在的不满并没有终结于现代——英国人在一片荒野中建造了“新德里”,而全球资本从无到有建成了古尔冈。这个地方的精神一直是不连贯的,充满了断裂。
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是这里最稳定的时期。这个王朝源于中亚,传奇的财富和辉煌在17世纪到达巅峰,也是在这个时期,皇帝沙贾汗(Shah Jahan)
 把首都从阿格拉(Agra)搬到了德里,在亚穆纳河(Yamuna river)岸边建起了一座新的都会。新城建立在一座14世纪被洗劫过的城市废墟上,那是一个到处都是穹顶建筑和花园的灿烂天堂,并且令人惊讶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壮大。当时的城市叫作沙贾汉纳巴德(Shahjahanabad)
把首都从阿格拉(Agra)搬到了德里,在亚穆纳河(Yamuna river)岸边建起了一座新的都会。新城建立在一座14世纪被洗劫过的城市废墟上,那是一个到处都是穹顶建筑和花园的灿烂天堂,并且令人惊讶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壮大。当时的城市叫作沙贾汉纳巴德(Shahjahanabad)
 ,现在称为“旧德里”,这样叫是为了区别于“新德里”,后者是英国人1911年迁都到这里之后建的。但是那些辉煌岁月里所建的带露台的凉亭、无节制的显赫、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道,还有大道旁散发着玫瑰香的喷泉、精品商铺和皇家队列,这一切似乎都是不朽的。
,现在称为“旧德里”,这样叫是为了区别于“新德里”,后者是英国人1911年迁都到这里之后建的。但是那些辉煌岁月里所建的带露台的凉亭、无节制的显赫、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道,还有大道旁散发着玫瑰香的喷泉、精品商铺和皇家队列,这一切似乎都是不朽的。
但是莫卧儿帝国衰亡了,衰落的速度和其崛起时一样快。18世纪,帝国的皇权在宫廷暗斗、腐败和军力衰退中渐渐瓦解;帝国一些重要的部分,例如海得拉巴(Hyderabad)和孟加拉分裂并独立了出去,其余的部分被新的次大陆帝国马拉地(Maratha)的国王们匆匆吞并。德里不断遭受袭击,最具破坏性的一次是1739年,波斯帝国的军队在纳迪尔沙汗(Nadir Shah)的带领下,洗劫了整座城市,屠杀了两万居民。这场溃败证明了莫卧儿帝国势力的终结——纳迪尔沙汗带着孔雀王座回到了波斯,这个王座是为沙贾汗打造的,用了超过一吨的纯金,上面镶嵌了230公斤重的珠宝,其中包括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光之山钻石。
距那次袭击一个世纪后,一个名叫艾玛·罗伯茨(Emma Roberts)的英国旅行者站在顾特卜塔的塔顶,眺望远处沙贾汉纳巴德晦暗的光辉。她书中的“旧德里”是那些中世纪王朝(被她统称为帕坦人[Pathans]的王朝)和前莫卧儿帝国崩塌了的城市,即使与旧德里曾经的恢宏相比,她眼前的景象仍然让人敬畏:
莫卧儿帝国的首都……现代城市,或者按照当地人的叫法,叫沙贾汉纳巴德。这些人还没有习惯和欧洲人一样叫它新德里……伫立在一片沙土平原中心,四周被旧德里的废墟围绕,和它形成奇异对比的是一个新的郊区、居民区里欧洲人的别墅和新近为三个兵团的印度兵建起的兵营……在(顾特卜塔的)顶上,眼前是最让人敬畏的景象。一片沙漠,上面到处是美丽异常的废墟,包围着这座城的每一面。这里由蛇形的亚穆纳河哺育,它银色的宽阔水面蜿蜒着,流经宫殿和陵墓的残碎遗迹。背景里是一座古堡高高耸起的暗色围墙和层层叠叠的塔,这座古堡是帕坦首领们的要塞。这些曾经宏伟的建筑体量巨大且依然美丽,视线在其中游走,最后落在现代城市里熠熠发光的白色清真寺和尖塔上,其郁郁葱葱的树林和繁花似锦的花园与视线下方的孤单和荒芜形成了精致的对比。
在穆斯林入侵前,(这塌陷了的城市)已经是非常著名的地方,许多残存的印度教建筑与穆斯林征服者的建筑瓜分着这座城市——据说,在所有的寺庙和宫殿塌成无法辨认的荒地之前,人们还能在残垣断壁中找到属于忠诚的十八万名圣人和殉道者的坟墓,但现在这片荒野只显得整个景象更为荒芜……
从外面看(沙贾汉纳巴德的)景色非常壮丽。穹顶和清真寺,塔楼和尖塔,伴随着层层叠叠的帝国宫殿,如一座红色花岗岩的山在树林中若隐若现。树林非常茂密,以至这些建筑在东方意象中被比作从翡翠海洋中升起的珍珠和红宝石。从亚穆纳河东岸往这座城市靠近,所有关于东方的壮丽想象都在此成真——清真寺和尖塔在阳光里闪耀,有些被野生藤蔓缠绕,有些装饰着华丽的金饰,塔楼的外墙覆盖着闪亮的金属;从麦仑山(Mount Mejnoon)上看去(山上现在通了一条很好的路),亚穆纳河的河水在远处闪闪发光,隔开了萨林加尔(Salimgarh)古堡,然后在放着孔雀王座的厅堂和帝王们的宫殿背后消失,为整个场面增添了另一道美丽的风景……(然而)莫卧儿帝国的荣光已逐渐暗淡,他们的伟大也消逝了……夏利马尔(Shalimar)最负盛名的花园,连同那栽着柏树的大道、绚烂的喷泉、玫瑰色的凉亭,还有雪松的黝黑而宜人的树荫(据说全世界最有品位的君主沙贾汗为这些雪松豪掷了1000万卢比[100万英镑])——所有这些几乎完全坍圮,成为一片荒芜的废墟。 [1]
和周期性发作的、笼罩着整个城市的乡愁相比,这种触动外来者的伤感根本不算什么。艾玛·罗伯茨到来的数年前的秋天,沙贾汉纳巴德的贵族们在写作和欣赏某首诗歌时找到了乡愁的残余功用:这首诗歌以比其他诗歌更夸张的方式,表达出他们对于逝去的甜蜜痛楚。诗歌由两种语言写成,一种是莫卧儿的宫廷语言波斯语,还有一种是乌尔都语(Urdu),后者是印度的一种土著语言,在过去的近千年间兴起,是梵语中德里方言与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这些来自西方侵略者的语言杂糅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首诗与来自侵略者土地的诗歌一脉相承,在那些诗歌里,俗世转瞬即逝的本性(关于爱、美和欢愉)是数个世纪以来不变的主题。归根结底,这个主题诉说的是一种全情投入的痛苦——因为虔诚的诗人必定生活在凡尘世界暂时的奇迹中,每时每刻都知道自己最终是要离开这些奇迹退入不朽的。不过,18世纪印度的艰辛生活为这种哲学气质增添了一种特别的经验性的东西。在这首米尔·塔基·米尔(Mir Taqi Mir)所写的诗中,“荒凉”完全不是隐喻。1756年,波斯人又一次袭击了这座城市,米尔被迫逃离,来到了辉煌的勒克瑙(Lucknow),在那里迎接他的是穿着长袍的诗人,后者鄙夷地看着他的破衣烂衫:
何处是我之所属?你,东方之人,问道,
还嘲弄取笑一个可怜人。
德里,曾为这世上独一无二之城:
神的选民和天才能人之家,
现在已被命运之锤夷为平地,沦为废墟。
我便来自那片荒芜。

这首诗很能说明德里的精神——直到现在,这种心情、这种生活在创伤中的感觉仍旧主导着这座城市的文学作品。这座城市或许是一个高速发展、人口密集到令人眩晕的国家的首都,但德里的作家始终将其视为一座废墟之城。他们用自己的创造力来表达那种精神上的憔悴,这种憔悴来自与自己过往的隔绝。这既是德里的现实,也是德里的幻梦——这座城市总是处于一种已经被毁的状态。大多数远道而来的人似乎体会到一种奇怪的绝望感,而这种感觉正源于此——似乎每个人都由于在德里而变成了一个幸存者,一个失去了所有珍爱之物后仍活下来的人。尽管这本书明显写的是当代的内容,但或许只不过是重复这古代文学中的心绪,因为在这座没有任何东西能长久的城市,我最根本的经历也是恍然若失。也许,我父亲也会说同样的话。
在艾玛·罗伯茨造访德里约二十年后,对18世纪夸张的遗憾被强化成了世界末日,罗伯茨曾经热切描写的城市严重衰败,而且正是被她的同胞所捣毁的。
到那时,在这片次大陆上的主要力量是英属东印度公司,那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垄断企业,业务涉及丝绸、棉花、靛蓝燃料、硝石和鸦片等商品的生产和贸易。这样一家企业需要大范围地控制印度的土地、劳动力和法律。整个18世纪,这家公司以野心勃勃的军事行动达成此目的,征服这片次大陆的许多地方,并且镇压了马拉地人。莫卧儿的皇帝成了空架子,他的军队被解散,自己则住在红堡(Red Fort)里,由东印度公司保护。
1857年,德里的“西帕依”(sepoys),也就是为东印度公司效力的印度士兵(罗伯茨曾从顾特卜塔看见他们的军营),参加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对公司的暴动。德里的西帕依杀死了英国士兵,随后官方接管了这座由城墙围起来的城市。英国人在震惊和恐惧之下重整军队,用炸药开道入城,在一场毁灭性的战役后,叛军被镇压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洗劫和报复,其失控程度让肇事者自己都觉得恐怖。城里数以万计的居民被吊死或开枪打死,更多人逃走了。尽管之前参与暴动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比例相当,英国人的严苛报复却大多针对后者,因为他们控制着政治机构,也因为英国人害怕他们会以穆斯林君主的名义发动圣战。那位君主被审判后流放到仰光(Rangoon),好几个家族成员遭处决。大多数穆斯林难民被永远禁止回到德里;多年后,他们仍然偷偷住在南边莫卧儿陵墓的废墟里,财产被剥夺,受着风吹日晒。他们中有些是最有修养的人,还有一些直到最近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沙贾汉纳巴德的莫卧儿文化——花园、后宫、商人和诗歌,终结于一夜之间。
米尔扎·迦利布(Mirza Ghalib),一位穆斯林贵族,也是沙贾汉纳巴德的许多乌尔都和波斯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在信中描写了1857年的惨景。由于他和英国人的关系很好,所以被允许留在城里,但他大部分朋友都逃走了:
……身后留下的是满是家具和无价之宝的房子。这些……血统高贵的人拥有好多栋房子、礼堂还有宫殿,全都毗邻彼此。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有人丈量他们所占的土地,即使没有一个镇那么大,也有一个村那么大。这些伟大的宫殿被抛在身后,无人照看,被彻底洗劫一空,弃为荒芜,尽管有些价值较低、更重一点的东西,比如说大厅的窗帘、亭子、天棚以及……地毯,被留在那儿没有动。突然有一天晚上……这些东西着火了。火焰蹿得很高,石头、木材、门和墙全都被火焰吞噬。这些建筑就在我家的西边,离我家非常近,半夜我能从屋顶看见跳跃火光里的一切,我的脸能感受火的热度,眼睛能感到浓烟,还有灰飘到我身上,因为那个时候吹的是西风。邻居家的歌声如昔日所说,是一件礼物;那么为什么邻居家的火不能送来灰烬作礼物?
关于王子们,能说的就是有些成了来复枪子弹的受害者,被送进死亡之龙的嘴里,有些人的魂魄则冻在绞刑吏的绳子套索里,有些人在监狱里,还有一些流浪在这地球上。 [2]
对迦利布来说,这座城死了,陪葬的是它的文化和语言。英国人为了给自己的林荫大道、兵营和军事训练场腾出空地,不仅摧毁了房屋和清真寺,还摧毁了无价的图书馆。因此,很多乌尔都文学的实体记录都不复存在。很多践行和保护乌尔都语文化的穆斯林贵族也消失了,而那些取代他们的人,在迦利布看来,是一伙粗野的乌合之众。他引用一个朋友来信中赞美乌尔都语的句子——“我的朋友,这是德里人民说的语言”,最后这样写道:
朋友,“德里人”现在指的是或是印度教徒,或是工匠,或是士兵、旁遮普人、英国人。他们谁说的语言是你赞美的语言?……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片沙漠。既然井都没了,水也成了稀有而珍贵的东西,那么这里将会变成一片像卡尔巴拉一样的沙漠。我的神!德里人还在因为德里的语言而为自己骄傲!多可悲的信仰!我的朋友,乌尔都市场都没了,哪儿来的乌尔都语?感谢老天,德里不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兵营。没有城堡,没有城市,没有集市,没有河道。 [3]
“很难再理解德里这座城市,”萨迪亚·德维(Sadia Dehlvi)
 说,“尤其是很难再理解德里的人。”
说,“尤其是很难再理解德里的人。”
作为德里最古老显赫的穆斯林家族之一的成员,萨迪亚仍然会回顾迦利布在1857年后的日子里所悼念的文化,并把这种文化视为 自己的 文化。
她已经写了好几本有关苏菲派(Sufism)的书,这是伊斯兰神秘主义的一个分支,在1200年左右从波斯传入印度次大陆,并且在印度北部创造出一种特别有生机的知识、精神和美学文化。它吸收了印度教、锡克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反过来也影响了它们。苏菲派的泛神论倾向推动了这种融合,认为区别和差异的表象是错误的,并宣称至善是唯一的,没有标签或者偏好。苏菲神秘主义者还喜欢避开教士的权威,发展出一种拒绝外部法则和准则的道德语言,主张正确的行为来源于内在的智慧和良知。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年纪较大的精英们怀念苏菲派,将它作为北印度不复存在的催情剂而铭记在心,它曾经使不相干的团体聚在一起,并从中孵化出一种拥有丰富音乐、哲学和寓言的共有文明。
“唯一一个我真正理解的地方,以及我从心底里爱的地方,是尼札姆丁·欧里亚(Nizamuddin Auliya)的神像。它代表了这座城市的连续性,至少是过去七百年的连续性,包括它的文化、灵魂、语言和诗歌。现在,如果你去那里,你会看到富人和穷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印度人和外国人——因为哈兹拉特·尼札姆丁(Hazrat Nizamuddin)
 继续鼓励一种平等的文化,正如他在世时所做的那样。”
继续鼓励一种平等的文化,正如他在世时所做的那样。”
14世纪的圣人尼札姆丁·欧里亚是德里历史上一位形象崇高的人物,也是少数几个能为德里散乱零落的历史提供真正一致性的人物之一。每年尼札姆丁逝世的纪念日,仍旧会有朝拜的信徒从北印度四处赶来,在附近的街上睡一个礼拜。他们在人行道上煮饭,并为了安全,睡在载他们前来的近百辆公共汽车下方。
尼札姆丁布道克己,满怀爱意,宣扬一切形式的精神生活的统一,他避开那些当权者,并建议他的追随者也这么做。但他是一名直率的政治评论者,不只斥责政府的不公,也会表扬他们的明智。比如,他说苏丹伊勒杜密什,“是因为他为德里人民建造的供水设施,而不是他的战争或者他的胜利为他在天堂里赢得了自己的位置。”
尼札姆丁·欧里亚最显著的成就是通过他的弟子阿米尔·胡斯劳(Amir Khusrau)的帮助,扶植了一种被称为“卡瓦里”(qawwali)的狂喜音乐形式,这种音乐将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为尼札姆丁在其收容所举办的音乐集会带来了新意。卡瓦里成为苏菲派表达虔诚的特色形式,这让正统的穆斯林惊慌,因为苏菲派是自觉的多元论,吸收了更加古老的印度教风格音乐和诗歌,因此建立起一个跨越宗教分歧的灵修社群。到今天,人们仍旧每周四晚上在尼札姆丁神像前唱卡瓦里,唱歌的是不变的几个家庭,他们的祖先七百年前从阿米尔·胡斯劳那里学习了这门艺术。
萨迪亚的家在尼札姆丁东部附近,是以这个圣人命名的居民区的一部分。这一区有很多公园和鲜花,还有莫卧儿陵墓梦幻般的景色和散发着贵族气质的低调店铺,这些都让它受到外国新闻记者的喜爱。
“我的家族自沙贾汗皇帝时代起就生活在德里。我们是成功的商人,几乎拥有整个萨达尔集市(Sadar Bazaar),控制着大量批发交易。我们有自己的法庭,不去英国人的法庭。即使到现在,我的家族仍然会避免在官方的法律系统打官司。”
萨迪亚对于法律程序的评论很能说明她所承袭的流派。英国法律被引进后,就被莫卧儿政权视作一种来自外国的、不敬神且不合法的强加,所以苏菲神秘主义者教导他们的信众,说他们并没有向英国法律陈述事实的道德责任。萨迪亚的家族似乎从那时起,就一直沿袭着这种历史上的反叛。
英国法律体系被强烈地反对,以及这个体系从未在北印度获得广泛认可的事实,其实和它未能承认诸如苏菲派这样的当地道德权威有关。苏菲派在莫卧儿时期的部分社会力量源于其充当了一种平民的政治力量:苏菲派圣贤的威望之高,使其能够对莫卧儿王权不受约束的权力进行约束。皇帝会就伦理和政治事务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且不愿违背他们的话语,因为这些话语承载着宇宙的力量,这样就在王权中为公正规则建立了一种双方达成一致的公认机制,否则王权就是独裁。
但自英国法律体系以降,近代的法制系统给这样的中间人提供的空间更少。而如今,当政治和法律机构常常被视作腐败、谋私并远离普通人的需要时,仍旧有一种普遍的渴望,渴望有无所畏惧的圣人或许能带着宇宙性的权威和统治者对话,并且只用一句话就将一切改变。
“我成长的过程中,家里总是充满了音乐和诗歌。我们家族有个出版社,出版很多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的杂志,包括著名的叫 Shama 的乌尔都语文化杂志;它的发行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很有名。我们还有一栋很美的小木屋,从前所有的诗人和电影明星经常造访。任何稍微有点重要的文化人物都来过我们家,包括作家和艺术家,比如伊斯马特·秋泰(Ismat Chughtai)、柯莱特林·海德尔(Qurratulain Haider)、艾力达·普利特姆(Amrita Pritam)、费兹·艾哈迈德·费兹(Faiz Ahmed Faiz)、古泽尔(Gulzar)、M. F.侯赛因(M. F. Hussain)、萨迪什·古宙(Satish Gujral),等等;电影明星中的纳尔吉丝·达特(Nargis Dutt)、拉杰·卡普尔(Raj Kapoor)、米娜·库玛里(Meena Kumari)、狄力普·库玛(Dilip Kumar)、达尔门德拉(Dharmendra)……
“随着乌尔都语的衰落,我们的杂志也一本接一本停刊。几年前,我们卖掉了祖传的房子,那栋房子是我的家族从老城搬来时住的地方,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房子的买主是玛雅瓦蒂(Mayawati),北方邦的邦长。
“我对复兴家族生意不感兴趣。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对自己的时代很满意。我很高兴专注于自己内心的东西,并以灵性为主题来写作。我们的城市精彩、现代。我不想消极,但我们的灵魂受到了影响。某些东西断裂了。我说不出是什么。”
确实,也许这个已经断裂的东西难以辨认。也许它不是源于一个事件,而是源于这座城市的某些状态,这种每一件有意义的东西都已经被摧毁的感觉——萨迪亚悲叹的内容几乎与一个半世纪前迦利布的悲叹滑稽地相似。
“如果没人能读懂记载历史的语言,你怎么能期望德里在乎自己的历史?这座城市的整个历史都是用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写的。政府在1947年以后刻意消灭了乌尔都语,因为它被当作一种穆斯林语言。但是乌尔都语和宗教一点关系也没有——它是德里的语言,是德里每个人的语言。巴基斯坦把乌尔都语作为其官方语言,但乌尔都语并非起源于巴基斯坦的任何地区。失去这种语言,我比任何人都更哀伤。当你想要毁掉一个民族,你只需夺走他们的语言。
“德里人过去很讲究语言的优美。他们热爱诗歌,拥有真正的诗人。以前,说起德里,想到的是美味佳肴、温柔和优美的生活。下雨的时候,店主会关了店,到梅劳里(Mehrauli)的空地上去享受这样的天气。他们花时间准备精美的食物,热爱赛鸽子,也爱在贾玛清真寺(Jama Masjid)的台阶上听说书人讲故事。他们没什么营销技能,所以被淘汰了。他们信仰精致,他们制造毯子和家具,装订书籍。在乌尔都语里,我们把这叫作‘saleeqa’,一种高雅的敏感。”
和迦利布一样,萨迪亚非常纠结于未开化的外来者——那些对这样的敏感毫不关心的人。
“对德里文化的第一个打击来自英国人,然后是分治后涌进来的旁遮普人。德里的原住民不知道1947年以后重创他们的是什么,他们完全被旁遮普移民的吵闹、好斗和企业家精神弄得惊慌失措。我父母那时候很震惊:‘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这么吵?他们都吃什么东西?’他们试图保留1947年之前的文化。他们不断地纠正我们说话的语言。‘我们有一门语言,’他们常这么说,‘我们拥有一门优雅的语言。我们要用它。’旁遮普人夺走了这座城市所有的土地,他们消灭了它的语言和礼仪。他们吃烤鸡和黄油鸡。黄油鸡!这些东西我只在外面看到过,从不会出现在家里。
“当然,后来我变得更愿意接受其他文化。但是我很高兴自己是在旧德里的文化里长大,因为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文化,一个热情友好的文化。任何人到你家门口,你都会给他水;家里来了客人,你会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住,让他们吃好,给他们披肩。
“分治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永远地破坏了它的气质。看看我们那些雄伟的纪念碑,除了五六个被当作旅游景点,剩下的都逐渐倒塌倾颓。它们现在是垃圾场。自分治以来,几乎没有创造过什么美的东西。看看这些五星级酒店。要创造美,你自己必须是美的,我不认为现在的人还拥有那种内在美。现在和我们的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是侵略性、愤怒、不平等、腐败和个人利益,当然还有消费主义和商场。几乎没有空间让人反思和雕琢心灵。我们没有美能留给我们的孩子。”
这间房间的墙上挂满了乌尔都语书法作品。萨迪亚十几岁的儿子在另一个房间练习演奏音乐——他在用吉他弹奏中世纪的苏菲派音乐。萨迪亚说话很快,在乌尔都语和英语之间转换,她的句子一个紧接一个,因为她已经在头脑里把这些话预演了很多遍。
“我以前很喜欢去派对,因为以前的人待人更诚恳。现在,你遇到的人一边和你讲话,一边东张西望,心里则盘算着要给谁递名片。我和社交文化没有关连。“9·11”事件以后,真正的歧视开始出现。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太敏感了,但其实不是。我看到自己的朋友圈内有一部分人流露出歧视。现在我很难再和他们碰面打交道,因为他们内心有对穆斯林深刻的偏见。这些日子里,他们会说出真的很异想天开的话。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不做那么穆斯林的事。”
和我们在一起的有萨迪亚的两个朋友,一对巴基斯坦夫妇。男的开了一家公司,制作莫卧儿珠宝的仿制品,在巴基斯坦很受欢迎。但现在还有手艺能制作这些珠宝的工匠不在巴基斯坦而在印度,所以他经常过来和他们一起工作。
“我朋友昨晚去了一个派对,”萨迪亚说,“遇到个旁遮普女人——她是旁遮普人对不对?——嗯,然后她说她害怕巴基斯坦人。他们就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去巴基斯坦看看?’她说,‘不不,我们太害怕了。那里的人可能会在你房子里放炸弹。’然后她大笑起来。‘而且我们的丈夫永远不会让我们和巴基斯坦男人待在一起!’我说怎么会有人允许别人这样和客人说话?我是说,这样太粗鲁了!如果有人在我家这么说话,我肯定会说,‘对不起,但是你不能和我的客人这样讲话!’”
她的朋友补充说:“她丈夫还去过巴基斯坦!而且回来以后还说了好多你能在巴基斯坦体会到的美好事情!”
“任何从巴基斯坦来这儿的人都得听这些话,”萨迪亚说,“以前,那些人至少还把这些想法放在心里,但是现在他们会公开这么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出去了。我没办法听那些人那样讲话。
“看看穆斯林怎样在这座城市生活。看看那些年轻的穆斯林,无论什么时候想要去租房子,都会被拒绝。你知道披萨外送不送穆斯林区域吗?那天,我在一个朋友家,打电话叫披萨。对方说,‘女士,我们不送那几区。’‘那几区是什么意思?’我在电话里朝他大喊。”
她转向那位来自拉合尔的朋友。
“昨晚派对上那个女的对你说什么来着?她问要不要送你回家,然后你告诉她你住在尼拉穆丁。然后这个女的——她还是他们的朋友!——这个女的说,‘你疯了吗?我不能晚上11点到一个穆斯林区去!’你能相信吗?这些人都在最好的地方上过学。他们觉得去尼拉穆丁不安全。这些人都住在乔巴格(Jor Bagh),穿着高级时装、喝红酒,还送孩子去美国读大学。他们想要相信自己是非宗教的、世俗的,但他们不是。他们不停地这么说,因为这是他们对自己的幻想。”
萨迪亚对她的巴基斯坦朋友体贴关怀备至,向他们展示至少在她家里古老的文化依然存在。他们也谈起以前一起吃过的盛宴。过几天,她要在家里办一个苏菲音乐之夜。她邀请我也来参加。她儿子会演奏,还会有一个她支持的年轻卡瓦里歌手以及伊朗来的音乐家。
“我最近很累,”她说,“我想要一个夜晚来充盈我的灵魂,和我爱的人在一起,有诗和音乐。”
注释
[1] 迭辑自艾玛·罗伯茨两本书中对德里的描写,见 Scen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ndostan with Sketches of Anglo-Indian Society (1835)和 Views in India, China and on the Shores of the Red Sea (1835);拼写已改为现代英语。
[2] 1857年的信件引自Ralph Russell and Khurshidul Islam (eds), Ghalib 1797–1869 : Life and Le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dia, 1997), p. 148.
[3] 1861年的信件引自Russell&Islam, Ghalib , p. 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