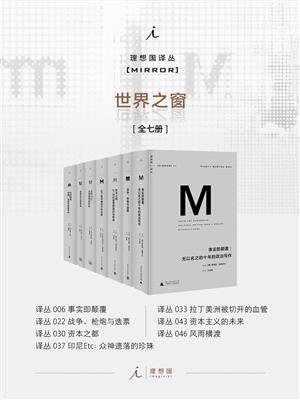九 1911
——英国人的新德里
我不否认德里这个名字的魔力,也不否认那些附着在它身上、已经死亡且被遗忘的城市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我冒险说一句,如果我们希望为将来画下幸福的预兆,那么越少谈德里的历史越好。现代德里只有两百五十年的历史。它只是莫卧儿统治苟延残喘时期的首都,它作为他们集体统治的首都只有一百多年。当然,在德里之前,那个地方也是首都,但一切都已经一一逝去了。我们知道德里的整体环境是一个巨大的荒地,满是被遗弃的废墟和坟墓。我认为,这些呈现给来访者的,是你所能设想到的关于人类伟大无常的最庄严的场景……如果试着去创造一个生气勃勃的未来首都,而不是谈论这些已经死去的首都之过往,那么国王陛下的政府统治将更有保障。
——柯曾(Curzon)爵士,印度前总督,1912年2月
在英国上议院发言,反对英国政府当时要把印度
首都从加尔各答迁往德里的决定。
[1]
随着1857年的骚乱,似乎又一座大都市加入了德里土地上城市相似而反复的命运。在之后的岁月里,德里对于欧洲旅行者来说变成了一幅描绘关于无常和人类野心的愚蠢的肖像。1912年,一位意大利诗人来到那儿,希望通过炎热来减轻他的肺结核。他从沙贾汉纳巴德往南,穿过通往顾特卜塔的平原,展现在他眼前的是这样一幅景象:
……从生机勃勃的城市转换到这座死城。最终,房子里不再有人类居住,而逐渐被猴子占领……废墟无穷无尽地延伸;整个大草原,举目所及和所不及之处,都是一座巨大的墓场,在它之上,四千年间,一座城市被摧毁和重建了十次以上……在这里,在这垃圾的荒漠中,横行着一种忽视和遗忘的混乱,使得研究者必定一阵头晕,因为他们被抛回了五百年、一千年甚至三万年的时间深渊——从伟大莫卧儿帝国最后的伊斯兰辉煌,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早期耆那和巴利结构中黑暗的婆罗门,再到已经黯淡的吠陀原型。
我发现本地和欧洲的学者在这里工作:考古学家、专家、建筑师在制作模型,测量尺寸。英格兰已经准备好要大干一番:进入埋藏着这些死城的藏骨洞穴,修复遗迹,然后在白天的日光下恭敬地把它们重新排序。这是一项值得做的事业,尽管我怀疑这么做是否有利于书写承载这些记忆的诗歌。我真心感谢上天让我能够在今日造访,在其还是荒凉和被忽略的时候。 [2]
但是这位诗人是透过肺结核的阴霾观看这一切的
 。英国人准备好的“大干一番”不是要整修。他们的项目,就像他们之前许多德里的统治者一样,是要平整好土地再建一座新城。从那年起,这些“无尽废墟”中的大部分被夷为平地,而下一个“新德里”展开了,就像在昨天的隔夜饭上铺了一块崭新的桌布。
。英国人准备好的“大干一番”不是要整修。他们的项目,就像他们之前许多德里的统治者一样,是要平整好土地再建一座新城。从那年起,这些“无尽废墟”中的大部分被夷为平地,而下一个“新德里”展开了,就像在昨天的隔夜饭上铺了一块崭新的桌布。
1911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宣布英属印度的首都将从加尔各答搬往德里。加尔各答对英国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中心。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越来越因为自己被剥夺的政治权利而灰心丧气,他们已经把这个英属领地的首都变成了反帝国思想的主实验室。通过“分治”这样的政策笨拙地尝试控制孟加拉人的骚乱效果适得其反。英国人决定逃往别处,而德里是个明显的选择。总督哈丁(Hardinge)爵士在191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德里仍然是一个重要且有巨大影响力的城市。它在印度教徒的心里和神圣的传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些传说甚至可以追溯到有历史记载以前……旧堡(Purana Kila)仍然是他们曾经创立的城市印德拉普拉沙所在之地的标记,距离现代德里的南城门仅仅三英里。对于穆斯林来说,看见莫卧儿的古都在其骄傲的位置被修缮并作为大英帝国的王座,将是无穷满足感的来源。印度全境,往南一直到被穆斯林征服的地方,每一座有城墙的镇都有自己的“德里门”……这种改变将前所未有地冲击印度人民的想象力,并向整个国家送出一波热忱,使英国在印度维持统治的坚定主张被所有人接受。它将受到印度北部统治长官和各个种族满怀喜悦的赞颂,而且将受到大多数印度人民的热烈欢迎。 [3]
但英国人不顾这些来自德里过去荣光的吸引力,决意在那里建一座将否定它自身所有过往的城市。帝国主义者将设计一座在几何学上非常欧洲的城市,这座城将用自己的规划布局击败所有过往岁月中落后的东方主义,并为一个启蒙的新未来搭起舞台。
在这座英国人的城市,不会有那些狭窄的街道,沙贾汉纳巴德和无数其他气候相似的地方(从托莱多到威尼斯到巴格达)用这种狭窄的街道来使行人免受太阳的直射。这些小巷,兜兜转转让人猜不透方向,两边的围墙也没有窗户,这些都让英国人不舒服。英国的城市理论依旧由19世纪的“毒气”病理学神话所控制,认为疾病来源于有害或者不新鲜的空气,而且在英国人看来,沙贾汉纳巴德是一片温床,不仅潜伏着咒语和东方共谋者——这些共谋者是白人在如此蜿蜒曲折的巷子里永远追不上的;这里还滋生着肮脏的蒸汽、疯癫和疾病。而英国人的城市构想是引入光线和空气来驱散污浊难闻的空气: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钟情于英国的乡村风格,并且受到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理论启发。那时,霍华德在他的书中提出了花园城市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优势,并在大西洋两岸都引起了一场思想运动。路特恩斯决定将德里建设成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体,就像霍华德的乌托邦那样:低层建筑物间隔疏松,之间有广阔的花园;宽阔的道路和公园会令城市保持新鲜和通风;通过在亚穆纳河上建起大坝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湖泊,而这个湖能为城市居住者提供水源和开阔的天空(尽管计划的这部分从来没实现过)。总而言之,这就是一个逆转:沙贾汉纳巴德的街道狭窄,如迷宫一般,而新德里会有宽阔的几何形大道;老城的商业在众多熙熙攘攘的市场,而在新城,商业会被限制在一个有立柱的圆形区域,最终被叫作康诺特广场。沙贾汉纳巴德是一座城市,新德里则可以说是一座官僚的村庄——因为尽管它有着极其宏伟壮丽的行政大楼,但是分散的田园式规划和宏大而空旷的开放空间,几乎没有给城市留下任何喧嚣吵闹的空间。规划里几乎没有为娱乐活动或宗教集会提供空间,也没给商人和他们的交易提供空间,当然更没给穷人的住宅提供空间——所有这一切都曾经是旧城显而易见的特色。
就像之前在这亚穆纳河左岸的建筑项目,新德里是一个项目,一个史诗般的事业。三万劳工用镐和炸药平整土地,同时火车沿着专门铺设的铁路源源不断地运来一车又一车石头和钢材。令人窒息的灰尘云团笼罩着约90平方米大的工地,伴随着巨大的噪音,在那儿石头被切割凿磨成形,同时还有几十个烧砖的砖窑冒着滚滚浓烟。从那位意大利诗人所谓的“巨大公墓”中浮现出了一座城市的轮廓,一座大得不可思议的六边形广场在其中心摊开,向外朝着德里的古城辐射出六条大道,宽得惊人。观察者们一定会觉得这样很傻,因为尽管这些建筑第一层的体量大得让人神魂颠倒,风格让人眼花缭乱,但是这座城市本身仍然是极度概念性的,没有居民,也没有文化。它正如所有新的开始一样激进——它根本不管要怎样运作起来,或者能不能运作起来。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耗尽了建造者的金钱和精力,因此有很多声音要求放弃;但是建造工作仍然坚持推进——这座英属印度的新首都在二十年内建成了。
这是一座充满惊艳建筑的城市——这样的建筑比同期在伦敦建成的还要多——这座城市有意识地让人想起雅典和华盛顿的超凡壮丽。当这座外国的城市从草图变为现实,两边种着树的大道最终消失在尘土缭绕的树林中,这座城市也为这里带来了全然不同的氛围。
为了把这座巨大的空城变为一座真正的城市,英国人需要人们住进来,但几乎没有人愿意。大部分管理建筑项目的人,无论英国人还是印度人都把家人安顿在老城,或是城墙外的公民路(Civil Lines),那里有商业、社会生活和娱乐活动。为了能让这些人(他们提供劳力、石材、家居、酒精、食品等)搬到新城里,城市管理者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向他们提供大面积的土地。所以承包商来了,将市中心的土地一抢而空,纷纷建起自己的大厦,并囤积了大量城市土地作为投资。在建设德里的阶段,这些承包商用公平或不公平手段赚来的钱已经使他们富有起来,而现在在这个将来的首都市中心拥有的房产,确保了其家庭在接下来一个世纪里的财富和声望。这些承包商,实际上成了德里的新贵。
他们是和沙贾汉纳巴德衰颓的贵族非常不同的一个群体,大多数是来自旁遮普的锡克教商人。在他们的世界中,赚钱的方式各种各样,封建地主、贸易商、土匪,都可以。如果说他们完全成功地挤进了英国人的财库,那是因为他们是拿下合同的大师,而且从那时起“拿下合同”就成了定义德里商业精英的标准。这些锡克教商人身材魁梧,给人印象很深,他们热爱政治喧嚣,当后代谈起他们无畏的创业精神时仍然带着敬畏。而正是通过这种创业精神,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王朝。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是市政厅(现在叫作国会大厦)的建造者,还是德里豪华酒店——帝国酒店(Imperial Hotel)的拥有人,在他孙子的回忆里,他的创业精神就和英国人完全一样。
“我祖父在柯曾路(Curzon Road)的隔壁邻居是拉拉·史瑞·热姆(Lala Shri Ram)爵士,德里纺织公司(Delhi Cloth&General Mills)的所有者。他们两人都习惯早上6点半在自家的草坪上喝茶。1932年的一天早晨,拉拉爵士在早茶时间匆匆来到兰吉特家,态度里有一种不同往常的焦急。他穿着三件套西服,戴着帽子,拿着手杖,身后还跟着带着一本分类账簿的助理。‘你看新闻了吗,辛格?’他大喊。
“那时候,英国人正试着从荷兰人手里夺走亚洲的糖贸易,印度大部分地区供应的荷兰糖都来自爪哇(Java),那里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1932年,英国人对荷兰糖发动了一轮攻击,对进口到大英帝国的糖收取高额关税。这个举动马上给能在印度生产糖的人带来了机遇。而且,由于爪哇的糖业马上就会被毁掉,他们就能以很低的价格收购爪哇制糖厂。
“拉拉爵士告诉我祖父这一切的时候,我的祖父飞快地把这些记录下来。爵士走后,祖父自己把数字算了一遍,意识到拉拉爵士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机遇。当天他就写了封信给他的姐夫,这位姐夫在昌巴(Chamba)的一片封地上过着悠闲的生活。祖父随信还附上了一张40万卢比的信用证。
“他姐夫坐火车去了加尔各答,再从那儿搭蒸汽船到爪哇。他看了四座制糖厂,选了其中最好的一座,把它拆光,然后将所有设备运回印度,并在英属印度联合省的卢克索(Laksar)把糖厂建了起来。他监督了整个过程,直到制糖厂完全重新装配好,然后他就回自己的封地读小说去了。他对制糖一点兴趣也没有,纯粹是找点乐子。
“兰吉特让他的兄弟负责糖的生意。这家厂今天还在运转,我还是它的股东。
“我多希望自己能用摄像机把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录下来。因为对他来说,这件事再简单不过了,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就是去爪哇,把厂买下来再带回来。他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他总是维持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他只有一辆捷豹车。他从来没给自己买架飞机或者类似的东西。他有萨维尔街(Savile Row)
 最好的西装,但他待人处事非常脚踏实地。他抛弃了封建生活,而且他知道倒退到那种环境里有多容易。他的一个表兄弟在旁遮普有近4900公顷的土地和一整个车队的劳斯莱斯;他看着所有的财富在几代人手里就消失殆尽。那些封建地主们活在一个泡沫里:他们关心的只有金钱、汽车、香槟和打猎。我能和那些男人聊四小时武器。
最好的西装,但他待人处事非常脚踏实地。他抛弃了封建生活,而且他知道倒退到那种环境里有多容易。他的一个表兄弟在旁遮普有近4900公顷的土地和一整个车队的劳斯莱斯;他看着所有的财富在几代人手里就消失殆尽。那些封建地主们活在一个泡沫里:他们关心的只有金钱、汽车、香槟和打猎。我能和那些男人聊四小时武器。
“那是兰吉特的噩梦。他总是告诉家里的每个人,让他们学习和工作:‘如果你没有正经手艺,你就会变得封建,失去一切。’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家里有人卖掉了价值连城的财产,把钱全花在派对上。有个表亲连续开了三十年的派对。”
从这最后的回忆里,我们很好地理解了德里最早的承包商们的财富多年来是如何被稀释的。他们后代中的一些人仍然住在市中心的房产里,统治着德里的生活,但其他人已经没了声息。财产被分了卖掉,很多力气都用来打官司,争夺剩下的部分。土地就那么消失了,年复一年,大片土地被其他人占用,并在上面修起建筑,随着时间过去,地契也搞不清了,大家也渐渐没精力再去争论。这些人中,很多人现在住在经过财产分割的豪宅裙楼里艰难过活,维持自己地位的方法是偶尔去很贵的地方喝茶,傲慢地蔑视那些代替了他们的新贵。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家庭成员的自杀、癫狂和酗酒。他们对过去有着古怪的妄想,会把威士忌藏到挂在墙上的曾祖父威严的肖像画看不到的地方,他们的曾祖父是个爵士或者别的什么,建造了这座他们现在深居简出的房子。
有法律争议的房屋不能出售,而且维护成本太高。康诺特广场周围的豪宅里空空荡荡,电力已经被切断了很久,里面只有些做清洁工作和守卫这疲倦庭院的人。远离这座城市奔腾的脉搏(尽管一切只是在墙的另一边),这些人在价值3000万美元的房产里过着杂乱无章的生活,偶尔清扫草坪上的落叶,用木头生火煮饭。他们撬开生锈大门的门栏,走到外面的街上,但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在阳光下睡觉,有时候抬起头,徒劳地向一只入侵的狗扔石头,而狗和他们一样昏昏欲睡。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杂乱又破败的院子里玩耍,又睡了过去,接着,他们看着自己孩子的孩子在那里玩。
如果说新贵是对于老一代贵族的背离,那么他们来到英属德里也代表了对他们自己生活的一次重大背离。他们继续获得合同的能力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成功地融入这个英式社会的新世界,他们确实做到了,并把自己曾经拥有的留在了身后。
比如说,他们曾经在庭院风格的房子里长大,这种风格是从中亚来到印度北部的。在这种风格里,空地不是在边缘而是在中心——那里有一个露天的庭院,多数有树木和喷泉,为整个大家庭提供了一个公共区域。院子周围是房子,家族的各个分支拥有自己的私人房间,有的还有供家里的妇女在日间活动的独立场所。这种风格有很大的吸引力,至今仍是一些德里老年人的梦想。他们出生在这样的房子里,但几乎之后所有的日子都生活在风格完全相反的住宅里。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迎合英国人,德里的承包商无情地抛弃了这种亚洲风格的住所,转而建造被草坪围绕、有大客厅的豪宅,在那些客厅里,男人和女人可以进行“英国式”的、没有隔阂的交往。
英国化的回报是巨大的。英国人关心这些新贵族的培养,不仅奖励他们商业合同,还奖励他们骑士称号和其他国家荣誉。英国人让他们成为自己俱乐部的会员,帮助他们把儿子们送到牛津和剑桥。于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崛起时迅速地接受了英式作风。他们将英国人的穿衣风格消化成自己的。他们打网球和高尔夫球,周末时去狩猎,他们在毯子上野餐,用闪亮的银器喝下午茶。
但他们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他们重新创造自己语言的能力。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儿子这样写道:
我的父亲,索伯哈·辛格(Sobha Singh)……非常超前于自己的时代。他意识到,如果要和英国人相处,就必须懂得他们的语言。他登广告找了一个辅导老师……三四年内,他就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他试着让我母亲也学说英语。他请了一个印度裔的英国人赖特(Wright)夫人教她。苦苦学了好几个月之后,我母亲只学会了几个词:早上好,晚上好,晚安和谢谢。她常常自嘲,还会把谢谢转换成‘非常感谢(thankus very muchus)’。训练她使用英语几乎就是一场灾难……父亲放弃了把她英国化的战斗。
我父亲身高一米八,体型苗条。我母亲身高还不到一米五。父亲对自己的穿着特别讲究。他穿着英国西装:外套和条纹长裤,戴领结或丝绸领带,还有晚礼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穿传统的印度服装,他唯一的印度服装是晚上在家休息时穿的。他对饮食的要求很高——早饭分量很大,有玉米片、鸡蛋、烤面包片和水果;午餐前喝几杯金汤力也很重要;喝茶的时候要有蛋糕或酥皮点心;他喜欢在晚餐前喝几杯苏格兰威士忌,晚餐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要有好几道菜,随后是一两杯干邑白兰地。 [4]
这些人在印度北部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共同文化中长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地方以其优美精巧的语言而自豪。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使用好几种这个地区的亲属语言,包括用阿拉伯字母写成的乌尔都语、印度斯坦语(和乌尔都语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文字用天城体)、旁遮普语(文字为与天城体相近的古尔穆奇字母)以及可能还有其他一两种方言。语言不仅仅是一件用来做事的工具,即使对于他们这样的商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爱好诗和歌曲,许多人自己写诗,通常用的是乌尔都语——虽然可能不是他们的母语,但被普遍认为是最适合写诗的语言。然而突然之间,他们用自己最弱的一门语言来生活,或者说一门他们甚至都不会说的语言——英语。他们用英国官僚和军人之间的黑话互相咆哮,他们与那些人(“六尺大汉”)过从甚密,而从前的文化在他们身上萎缩了。英语成了他们的语言,虽然他们给后代留下了梦幻般的财产,却没能让他们继承自己的语言。
当你看着新完成的英国行政综合大楼的照片——巨大的、完全现代的建筑,周围方圆几公里一片空无,你不禁感觉到有一些妄想的东西在里面——因为有许多城市曾经建在这个地方。确实,从这个意义来说,英国人完全是“传统的”德里统治者。在他们的故事中,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首都,使用的时间比建造它的时间更短。1947年,他们匆忙离开,随后,独立印度的管理者就搬进来了。
这些管理者有意无意地完成了英国人起头的事——破坏北印度古老的印度教和穆斯林共有的文化。分治的毁损过去后,在极度痛苦中,新的国家决心抹去所有会让他们想起这道伤痕的存在。那种共有文化将被遗忘,其中伊斯兰的痕迹被消灭了。语言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1950年的宪法为一种新语言——“印地语”——规定了明确的传播目标。印地语是对传统印度斯坦语的重新发明。传统印度斯坦语是一种北印度语言,其中乌尔都语被用来进行最高水平的文学和哲学研究,是最复杂的一门。现在,印度斯坦语将被重新组织,尽最大可能去掉其中所有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带来的影响,并用从梵语中找回或创造的词语来取代它们。从今以后,印度人的舌头不会再发出穆斯林的声音。
印度人的手也不会再写下穆斯林字母,这种语言已经不再用阿拉伯文字书写,印地语只用印度本土的天城体(Devanagari)书写。中央印地语管理局成立了,职责是在这种语言的街头巷尾巡逻,同时保卫它的边界。官方通讯比如学校教科书或者全印度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都被制作成这种新语言的展示样品。这是一种糟糕的学术展示,因为里面梵文过多,完全不像真人在说话。
也许有人会想象,一个独立的国家会比殖民地发出更多的声音。也许有人把独立想象成为这样一个时刻——从前沉默的声音以谈话和歌曲的形式爆发。但在印度北部,真相更为复杂。人们不再阅读印度斯坦尼最伟大作家的作品,因为里面包含了太多不被许可的元素,并且他们很快就将无法读懂这些作品使用的文字了。从前以文学素养自豪的旁遮普人家庭,自己也开始不喜欢书籍。大多数书籍,尤其是那些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没有直接促进效用的书籍,成了没有回报的支出。事实上,这些书代表着对生活在分治后的家庭的威胁,在这些家庭中,重建物质基础是唯一正当的关切——对深奥幽微世界的关注现在被视为是危险的,父母应该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其影响。此外,在充满恐惧的新家庭气氛中,父母对孩子拿着一本书自得其乐感到不安,他们希望孩子需要他们,正如自己需要孩子一样。他们堵住了通往孤独和遐想的道路。
德里这座城市延续着自己久已有之的名声——语言的死亡之所。分治的难民不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遗忘了乌尔都语,他们甚至难以把自己的旁遮普母语传承下去,他们的孙辈中很少有人了解这种语言,除了只字片语。这里许多中产阶级的成员最终哪一门语言也说不好。他们说不好英语,尽管在职场里英语用得越来越多;他们也说不好印地语,虽然在家里说,但除了日常词汇以外也知之甚少。关心语言被看作是毫无价值和娘娘腔的,而且口语特有的模糊性和对语法的故意忽略成了一般的风格。书本和报纸上到处都是拼写和语法错误,更不用提广告和街道标志了。很难找到能在印度诸语言间进行翻译的人,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同时掌握高水平的书面印地语和书面英语。以往的宽阔视野逐渐消失。人们对于和自己不相像的人的了解越来越少,阶级和种姓变得更加孤立而可疑。
倒是来自小镇的贫困移民往往保留了关于优美语言的观念。登陆的分治难民计算着自己的房子和存款,面对后来到达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他们陶醉在自己的优越感中。但有时他们听到来自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说的话——在那些地方印度斯坦尼诗意和狂喜的元素还没有变得陌生——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多不善表达。
对诗歌和精致语言的挚爱现在失去了表达的对象,也许这些爱被转移到了孟买的电影艺术那里,使其在分治后的几十年里享受着偶像式的崇拜。孟买的电影制片厂,成了许多乌尔都语诗人和剧作家迁徙向往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创造了一种蕴含着精致感觉的电影艺术。在这些电影中,英雄说的是讲究的波斯印地语,情歌里的隐喻让人回忆起乌尔都语诗歌的艺术高度。那个时代的三个超级男星,拉杰·卡普尔(Raj Kapoor)、狄力普·库玛(Dilip Kumar)和戴夫·安南(Dev Anand)都是从现在的巴基斯坦来孟买的。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印地语电影甚至在晚于那个年代很久出生的人之中仍然带有这种情感力量,那是因为它成了印度斯坦尼文化中浪漫和诗意最后的避难所,而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被独立国家更加严酷的氛围赶到了地下。有一点也许意义重大,那就是孟买的电影艺术是印度公共生活中极少数穆斯林男子能享受毫无顾忌爱慕的领域之一,尽管他们起了印度艺名。
富有启发意义的是,这种电影艺术在整个苏联集团里产生了狂热的吸引力,那里的观众经历过严厉的肃治,并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生活里饱受沧桑。因为这是一种与日常世界有一定距离的电影,其中的生活就像以前那些更美好的事情一直都在(比如,电影故事几乎完全不提分治,好像它并非生于那场阵痛)。对于那些失去了自己东西的人来说,这无比辛酸,不管他们在哪里。
国防区(Defence Colony)是德里南部绿化最好、最让人喜爱的街区之一。在印度独立之后,这里宽阔的地块被分给了军官。最初的居民们现在已经老了,他们以一种古老的节奏生活着:早上6点在国防区的许多公园里快步散步,有时伴随着一阵阵充满活力的拍手声,或者一群人不约而同的大笑声;接着,7点在阳台上吃早餐看报纸。午餐和遛狗由在家里工作的“男孩们”安排,这些男孩通常是他们在军队时就认识和信任的仆人的儿子和孙子。下午,茶和饼干如同军事纪律般雷打不动地被送到露台。那些5点就起床的人早早吃过晚餐上床睡觉,但晚上也有可能到当地俱乐部喝一杯,在那里分享关于往昔的回忆。他们会聊20世纪40年代的军事学院,那时分治还没有将军队分裂成两半。分治时,一半的军校同学成了敌人,并和他们在三场大战中作战,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老交情(有时甚至包括越界的暗中合作:“老伙计,别打那个目标,我侄子躲在那儿。”),现在他们仍然与边界另一边的前同事保持着友谊。他们聊过世已久的上司们,那些被取了伍德豪森式(Wodehousian)笑话里的绰号,并能一口干掉威士忌的人。
他们是彪悍的男人和女人,同时拥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对乐趣的追求。“不打仗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年纪虽大却整洁美丽的军人妻子对我说,“那是你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我们所有人一起在一个军事基地,晚上喝酒、打台球,还有许多穿制服的高个子男人……”她说话带着桑赫斯特(Sandhurst)
 口音,面前是满满一杯金汤力。
口音,面前是满满一杯金汤力。
他们是俭朴的人,有舒适的住宅和不错的养老金,生活里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他们享有社会声望和关系,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婚姻和职业都很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他们的老年时光里,他们的生活超过了普通的富足,变得非常富有。
在21世纪初的房地产热潮中,他们生活的地块价值达到了200万美元,然后是300万美元、400万美元。社区里流传着数字。他们中很少有人真的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他们面临着释放其中价值的压力,这些压力常常来自他们正处于职业生涯鼎盛时期的孩子。于是,老人们搬出去到别的地方租房子住,一个接一个,房子破败下来。这些都是很有特色的房子,大多由房主自己设计,但都有一种优雅和匀称:房间宽敞,天花板很高,有屋顶露台可以在冬天晒太阳,底层房间在夏季通风很好,花园由恰到好处的树荫遮蔽。在很短的时间里,大部分房子只剩下了瓦砾,国防区也变得走风漏气的。坑洞里出现了棚屋,里面住着建筑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深色皮肤的农村孩子白天在街上玩,女人们晚上用木头升起火烤烙饼,这时你会听到忧郁的歌声。随着建筑的升高,劳动者的住宿条件也迅速提高。很快,他们住到了五星级公寓里,洗好的衣物被高挂在大理石大厅,他们的歌声也都变得更快乐了。然后工作完成了,这些家庭去了别的地方,再次住在帐篷里。
这些新建筑与旧的非常不同,它们是国际风格公寓的伟大堡垒。不再有花园了,因为这对房地产来说是不可能的牺牲;不再有露天阳台了,也没有阳光照耀下的白墙,没有遮阴的树木,没有任何古老建筑智慧的迹象,这些智慧可是在这个气候严苛的地方经过多个世纪积累下来的。这些新的庞然大物高耸入云,比树顶还高;石头材质的大楼冷冰冰地面对太阳;因为落地窗而产生的温室效应被空调的强大力量所抵消。高墙、安全门禁和闭路电视摄像头完成了“国际生活”的承诺。
原来的业主在这些街区为自己和孩子们保留了几栋公寓,其他的以每栋1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所有这一切解释了当我快到欧贝罗伊上校(Colonel Oberoi)的房子时,马路就像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原因。拆除和施工造成的粉尘扑面而来。空气与切割意大利大理石的巨大噪音一起尖叫(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必要的——这里所有的大理石都叫意大利大理石,不管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其中一栋房子前,有一队人在操作一个专业电钻,要把一口非法的私人水井挖得更深一些,这些房子都有这种井,好绕过市政供水的配给。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这些井不久之前还只需要深入地下十五米,现在却必须得深入六十米了。拥有钻探专业知识和设备的公司现在业务多得处理不过来。
我去见欧贝罗伊上校的时候迟到了,而且我从车里给他打电话道歉并没有让他感到一点安慰。“我给你五分钟时间到这里。”他在电话里大声咆哮道,然后就挂了。
欧贝罗伊上校的房子没有被拆掉,是极少数仍矗立在这里的原有房屋之一。欧贝罗伊上校自己设计了这座房子,现在这座房子显得非常古怪——在一片满是新德里规划排屋的土地上,非要应用旧式庭院的设计。
“我母亲坚持要有一个院子,”他说,“在50年代我们造这个房子的时候。”
对于一栋已经有人居住超过五十年的房子来说,里面的设施少得惊人。墙是裸露的,灯泡也一样。餐具柜上有几张孙辈的照片和军队授奖仪式的照片。
上校九十多岁了,已经退休好几十年。他有点聋,所以他军人式的嘶吼显得更加响亮。他穿着一套皱皱的猎装——以前印度公务员的制服。他坐下来,坐在一张写字台前。写字台上有用乌尔都语写着笔记的笔记本,本子是他自己用使用过的A4打印纸做的,每张纸被裁成四小张,钉在一起。他示意我坐在桌子对面。
“在我长大的村子里,”他说,“房子都有院子。你从街上走进院子里,那里会有家畜和干草,还有床可以让你露天睡在外面。房间在院子的尽头排成一排:它们都在一楼,由泥土和木梁建成。屋顶伸出屋子的墙壁很多,所以房间总在阴影里。所有这些房间都是卧室:起居活动区域就是院子。如果有客人来,院子里就会摆上一张桌子,倒上茶。我们不在家里办大型活动——婚礼和宗教活动会在社区中心,那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帮着建起来并维护的。”
欧贝罗伊上校在西北边境省(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的一个部落地区长大,那里的自然美景令人叹为观止,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喜马拉雅山,同时也是印度河河水最澎湃、水量最丰沛的河段。1947年8月,那个地区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欧贝罗伊上校一家成了印巴分治区的难民。
“当时我受命在孟买参加军事训练。我的家人滞留在马尔丹(Mardan),靠近希贝尔关卡(Khyber Pass)。他们无法动身去印度,因为我妻子怀孕了。我的一个穆斯林同事照顾着他们,他叫贾巴尔(Jabbar)上尉,他让他们住在他的军方住所以确保安全,其中有我的姐姐和姐夫、两个表亲和他们的孩子,还有我阿姨和母亲。那些地方传来的消息非常吓人,我很担心。独立后两周,我去了阿姆利则(Amritsar)的避难者组织。我的朋友在拉合尔有家人,他们由军队护送越过边境去接家人,但是马尔丹太远了,没办法这样做。我非常担心,不知道要怎么办。最后他们答应用飞机把我家人接出来。我还记得扩音器里播出公告的那个时刻:‘欧贝罗伊中尉的家人将会被空运出来。’
“但是我的家人还没准备好接受空运。我的妻子不能移动,所以她不得不一直等到10月我们最大的儿子出生。那时候空运已经太晚了。于是贾巴尔上尉亲自把他们护送到了白沙瓦(Peshawar),把他们交给了一个来自哈里亚纳(Haryana)的将军照顾。那位将军把我的家人带过边境,送上一辆军列。那时候的德里一片混乱——所有的火车都停了。我和他们都去不了德里。一个月以后我们才最终团聚。”
欧贝罗伊上校一边说一边画了很多画,有房屋的设计图,也有家人活动的地图。
“那些年我并没有驻扎在德里:我随着军队到处移动。1949年,我被送到英格兰参加长期炮术训练。之后,我被派到印度各地。但是我没有自己的住所,这是个大问题。我的大家庭仍然和一个亲戚一起,住在德里一栋只有一个房间的房子里。德里全是难民:有几十万人仍然挤在数个难民营中,住在帐篷和茅草屋顶下,政府在努力为他们安家。我的一个同事让我去问问避难者的房产。他们给我看了一个被穆斯林家庭遗弃的房子。我到负责安置的主管那里去问是不是能把那个房子分给我。他说我不符合条件,因为我不在德里服役。‘但是我们在建一个防卫定居点,’他说,‘在那里你可能符合条件,分下一块地。’”
政府为军人提供分期付款计划,让他们很容易就能买这些地。独立后,在德里人的概念里,这个城市是属于品格高尚、忠于国家的人的。当局使军队男子很容易购买这些地块,提供多年分期付款计划。埃德温·勒琴斯设计的这座英国行政城市中,新的“殖民区”迅速萌芽,遍布全城,其中比较好的区域被分给了工作对国家至关重要的非政府人员。除了国防区,还有为记者、律师等保留的街区。相比之下,商人的行当被认为更加庸俗和自私,因此被安置在德里西部相对偏远的街区。
“我坐下来写了一封申请书。第二天他们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申请成功了。我买下了地。等我回到德里的时候,我们建了这栋房子。”
我来见欧贝罗伊上校是为了参观他的这座庭院式住宅,房子建在新城,仿佛有些与时代脱节。他希望按照原定时间结束会面,但因为我迟到了,损失了一半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没时间参观房子。现在到他去市场的时间了。我们站了起来。
我问他,他在笔记本上写的是什么。“这是我的诗”,他说。“你用乌尔都语写吗?”“我用很多语言写。我的母语是西莱基语
 ,属于旁遮普的一种方言,是我出生地那里的语言。我以前常常和说普什图语的部落的男孩子一起玩。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孩子,我每天要说六种语言:西莱基语、旁遮普语、印地语、普什图语
,属于旁遮普的一种方言,是我出生地那里的语言。我以前常常和说普什图语的部落的男孩子一起玩。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孩子,我每天要说六种语言:西莱基语、旁遮普语、印地语、普什图语
 、英语和乌尔都语。我以前写信会用三种语言写三份,印地语的写给母亲和姐妹,英语的写给朋友,乌尔都语写给我叔叔。我也写英语诗歌。但是写诗最好的语言是乌尔都语。”
、英语和乌尔都语。我以前写信会用三种语言写三份,印地语的写给母亲和姐妹,英语的写给朋友,乌尔都语写给我叔叔。我也写英语诗歌。但是写诗最好的语言是乌尔都语。”
提起诗歌,欧贝罗伊上校忘记自己急着要走了。他想读给我听。他到书架上拿了一堆写满诗歌的笔记本。
“我写诗已经写了七年了。”他说。
大部分诗写在没用过的旧日记本里。他翻着本子,寻找他想念的诗。这些本子有些令人触动的东西,上面从左到右用灰色印着英语的日期和月份,这个字序对于拉丁文字的读者来说是从前到后,然而本子里却以反过来的方向写满了诗歌——诗歌让时光倒流。他用一种深沉而带着音乐性的声音朗读,读完每一首诗都稍作停顿。这些是古怪的韵文,给人一种带有不同寻常的好奇心的印象。“我们感觉到的对其他人类的所有情感,在天堂里有任何位置吗?因为如果没有东西把我们绑在一起,那就不是我的天堂。”
Jaise nadee ke bahaav main ek pathroon ka jaloos hai
Bahe jaa rahe hain ludak ludak
Wajood use na thahraav hai
Na lagaav hai na dosti hai
Na hai dushmanee
Chaahat nahin, nafrat nahin
Jannat hai uska naam agar jannat hamein nahin chahiye.
如石块行进
在一条河流中翻滚跌落
没有身份或根
没有对友情的依恋
或是对仇恨的
没有欲望,没有憎恶
如果你把那叫作天堂
我一点也不想要。

欧贝罗伊上校的态度总的来说严格而死板,但我们谈论诗歌时,他身上流露出了一些温柔和甜美的东西。这部分来自这个人心中对于宏大自然的记忆,他在这个巨大的城市中已经生活得太久了,但他的乌尔都语诗歌还坚定地维护着对一种已经失去的文化的忠诚——一种像他这样的印度教徒曾经与穆斯林共享的文化、一种多语言的大都会文化,在那种文化中,诗歌和精神的生活曾经有过更充分的表达。
朗诵完了之后,我问他:“你怎么看印巴分治?”
“最开始,我非常恨。我是说,我们期望的是独立,得到的是什么?国家一分为二。”
然后他用了一个印度的隐喻来详细解释,这个隐喻之后会一再出现。
“两个亲兄弟最后斗起来,然后分了地。”
他把怨恨的矛头指向了那些推行英属印度分治的政治家。
“我们服役的时候有行为准则。人民和国家的福祉优先,个人利益最后。这个誓言是写在我们军校墙壁上的。但是政治家不是那样的。他们考虑自己的利益,吊死了国家。”
“你仇恨穆斯林吗?”
“我为什么要恨穆斯林?我和这些人一起长大,他们遭遇的是和我们一样的情况。年轻的一代被教着去恨穆斯林。过去我们和穆斯林之间亲人般的关系现在没有了:年轻人听着恐怖的故事长大。但是我们爱那些人。”
他摸着自己浓密的白胡须说:“我给你倒点茶好吗?”
注释
[1] 引自Malvika Singh and Rudrangshu Mukherjee, New Delhi: Making of a Capital (Lustre Press, 2009), p.22.
[2] Guido Gozzano, Journey Toward the Cradle of Mankind , translated by David Uarinelli, 1913 (reprinted Marlboro Press, 1996).
[3] 引自Singh&Mukherjee, New Delhi, p. 22.
[4] Khushwant Singh,‘My Father the Builder’in Maya Dayal (ed), Celebrating Delhi (Penguin, 2010), pp.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