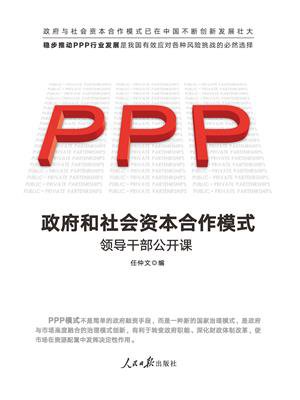在中国语境下准确理解PPP的本质内涵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最早起源于英国,自 2014 年起在中国得到推广运用。一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用PPP来定义国内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但严格来说,国外语境下的PPP和中国语境下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存在明显差异的。PPP模式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融入了许多中国元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发展,因而显示出中国特色。因此,我们应该在中国的语境下思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深刻内涵,而不是理解基于国外语境下的PPP内涵。就像我们理解市场经济一样,西方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存在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不在于形式特征,而在于内涵以及本质特征的差异。
社会资本概念本身就意味着社会责任
如果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我认为,中国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与国外的PPP,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存在较大差异。国外语境下的PPP,强调的是公与私的概念,合作方应该是私人资本或民间资本。而中国语境下的PPP,讲的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很多与政府合作的主体是国有资本或地方投融资平台,甚至这些国有资本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已经成为了合作主力军,但我们能说它是“私”吗?显然,采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进行表述,比私的表述更为科学,更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从这点来看,中国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虽然也简称为PPP,但只是一个大体上的转译,并非国外严格意义上的PPP概念。
我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应该对这种模式的表述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这一概念(简称“政社合作”),或许更能准确反映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特征。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强调社会本位,而不是资本本位。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包含了非纯粹盈利动机,是以大众福祉为最终目的。也就是说,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应该具有公共性、高风险、低收益的特征,而不是高收益的商业项目。所以,我们讲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意味着所有项目参与方应该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只追求商业利润甚至暴利的资本方,不能称其为合格的社会资本,因为他们并不愿意真正参与长期性、低收益的项目。可以说,采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进行阐述,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导向,也反映了一种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是采取市场化、商业化模式来体现公共属性的,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如果背离了这一原则,只能说是一种投融资模式。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共治的一种机制
对中国语境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概念的深刻理解,还有助于我们分析其另一个本质特征,即政社合作本质上还是一个治理问题。为什么说是一个治理问题呢?我们可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论分析。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所谓“治理”,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引领人民群众实现共治、共建、共享,这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共享。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也将“共享”作为重要的有机构成。
如何有效实现共享?从治理的逻辑来推导,无疑是基于共建,而共建的过程又是共治的过程。没有共治,就没有共建,也就谈不上共享。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我国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我们应在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下对政社合作进行研究、探索和不断的经验总结。如果脱离了这个框架,我们就难以看清政社合作的实质内涵。
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抓住两个关键词来准确理解“政社合作是一个治理问题”的观点。第一个关键词是“合作伙伴”,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是基于双方的平等关系。第二个关键词是“公共服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能提供更多公共服务,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第一个关键词来看,既然双方是合作伙伴关系,就应当是一种平等关系,而不是上级与下级,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因此,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首先应该转变政府身份,政府不应再作为行政主体,而应该是合作关系中的经济主体或者说民事主体。如果仍是以行政主体身份开展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就很难达成平等合作的关系,也违背了政社合作的基本原则。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关系仍在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之间争论和摇摆,各地方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如果按照政府是行政主体的身份来推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双方应该签订行政合同,可一旦签订这类合同,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合作关系难以维系。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行政手段推动项目建设和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一种行为惯性和路径依赖。而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更需倡导体现市场规则的平等合作关系。因此,在相关立法过程中,应当重视我国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的伙伴关系,双方应是一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而不应签订行政合同。
另外,由此还引发了相关问题的探讨。比如,针对特许经营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有人提出,政社合作是否属于政府特许经营,或者是不是政府特许经营的一个部分或一种类型?我认为不是。特许经营实际上是一种行政许可,仍是由政府说了算,双方按照特许经营的思维签订合同,不可能赋予社会资本太多话语权和选择权。可以说,政府特许经营实际上还是一种正面清单思维,与我们现在强调的负面清单思维是不吻合的。推而广之,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开展的所有生产活动,几乎都是政府特许经营,政府未许可的就不能去做。因此,政府特许经营是和行政审批紧密相连的。我认为,在探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时,必须先对政府的身份做出明确界定,我们虽然不能否定政府保留行政主体的功能,但在具体的政社合作项目中,政府应更多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同时又与社会资本保持平等的合作关系。这需要在法律层面予以明确,其本身就是一个实现共治的过程。
从第二个关键词来看,政社合作的目的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政社合作项目的建设运营,不仅涉及政府和社会资本,还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因此,既可以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解释,也可从公共需求这一角度进行阐述。可以说,政社合作是一项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充分考虑供给结构的优化和供给效率的提升,以更好满足民众对公共服务的多层次需求。所以,在理论上,政社合作仍是一个公共领域的共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