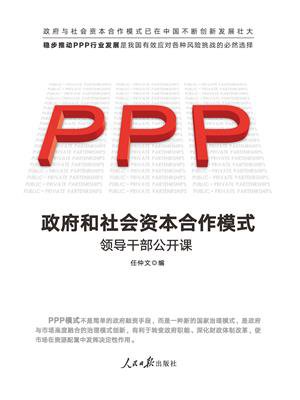以PPP服务逆周期调节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每当涉及PPP的问题,特别是谈及PPP意义的时候,不论是把它当作一种融资方式,还是当作一种治理方式,人们总会把它和宏观经济的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联系在一起,现有的观点大多把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挂起钩来。一旦挂钩,特别是和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紧密对接的时候,人们总是要把PPP从逆周期、调节政策相对接。
提到逆周期的条件,我们都能在脑子里立刻勾画出一批PPP和逆周期调节之间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每当中央决策层论及当前宏观政策主线索的时候,总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索。因而我们在当前的形势条件下谈论PPP的发展,自然就有一个逆周期调节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如何对接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逆周期调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往返。
进一步讲,意识到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PPP作为一件舶来品,最早在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形成,在中国高速增长阶段的时期被引进。因而我们在今天讨论PPP问题的时候,还需要在高质量和高速增长阶段之间协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四中全会闭幕之后,从制度建设的意义上讨论经济领域问题的时候,大标题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不能不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平台上去鉴别PPP的发展方向。PPP的完善之路究竟在何方,这不仅是在经济领域谈及PPP,还是谈及其他方面问题的时候必须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确不同于逆周期调节,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确有着一系列不同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实质内容。
在两者之间转换的前提是要明确,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有什么样的联系?四中全会在论及高质量的发展,谈及了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第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第三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实际上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描绘出一个蓝图,本着这样三位一体的认识,我们是能够在前几年研究的基础之上把高质量发展和高速增长、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逆周期调节做一个简单区分的。
比如说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大家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进一步问,提出新的发展理念,一定是基于旧的发展理念难以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妨回顾在过去没有提出发展理念概念的时候,我国的经济工作,或者说我们围绕着PPP的研究是本着怎样一种理念而展开的。可以看到在过去的经济工作也包括PPP,我们在论及它的时候往往是围绕着PPP的规模和PPP的增速这样一个主线的。
发问PPP显然是要提出GDP的规模扩大问题,是要提升GDP的增速。之所以要动用社会资本和政府资本合作、推进地方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奔着GDP的规模和速度问题去的。那么现在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这个新的发展理念又是奔什么而去的呢?显然作为规模和增速的一种替代,质量和效益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提到新发展理念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奔着质量和效益而去的,当提到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时候,实际上是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因而在今天我们谈论PPP问题的时候,论及它要本着什么样的发展理念而推进的时候,至少要做一道加法,也就是说要在GDP规模和速度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到GDP本身的质量和GDP本身的效益上来,所以这是绕不开躲不过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往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主线是什么?是需求管理,所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为了解决需求管理解决不了和解决不好的问题。如果说需求管理能够解决现在我们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就没有必要提出新的政策主线,之所以一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就是要将其作为需求管理的替代。有人讲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需求管理天赋性条款政策和方向性改变。这样一种变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妨回到过去,按照需求管理的理论和政策体系,做一番论证。
显然过去关注宏观经济领域问题,研究PPP的时候,我们是把自己放在了需求一侧的,而且我们眼睛盯的是需求的总量变化,我们想干的是逆周期调节,也就是对冲性的一种调节,东风来了我们就刮西风,西风来了就是刮东风,追求的是一种短期的平衡。大家看得很清楚,政策本身追求的就是短期平衡。那么现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显然是倒着来说的,我们得从需求侧移步到供给侧,我们得把主要聚焦点从需求总量转化到供给阶段,我们得从追求短期的平衡转到经济的持续发展,从主要依托于政策性的调整转到依托改革性的行动上来,这一些其实都是变化。所以现在谈及PPP的时候,肯定也有这样一个转化过程。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也要做加法。把PPP和宏观经济形势相对接和宏观经济政策相联系,除了用PPP的发展和完善去实现逆周期调节的效应,还要考虑到它还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背景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和完善。
如何兼容这两种政策让PPP走出一条适合高质量发展阶段,匹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路子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这样一条彼此融合的路或者说是跳舞弹钢琴的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可能要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调整过程,因为我们在高速增长阶段、在逆周期调节政策为主线的背景条件下,浸泡的时间太久。每遇到问题不自觉地就会用高速增长阶段的理念,逆周期调节的思维来加以认识和分析。
所以怎么完成转变?是我们在研究PPP问题时非常重要的一点。
完善和发展PPP事业,除了政策调整方面的视角之外,更重要的是把它要放在深化改革上,中国的PPP完善和发展需要政策调整,但更重要的需要的是改革。在设计PPP的改革清单上可以罗列出若干条来,但相比较而言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PPP在很大程度上演化为以PPP之名行地方举债之实。而谈论到去杠杆、谈论到一系列的这种金融领域的监管问题、涉及PPP无非是假的PPP和本来意义PPP、规范性的PPP和不规范的PPP之间的一个争论问题。
那么由此我们总在想,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包括其他方面,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一旦到了中国、一旦和地方政府层面的操作相对接就出问题。放到企业去可能就不是这样的问题,放到个人身上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地方政府主体本身的问题、地方政府领导人的问题,还是机制的问题?事实上,它不是人的也不是主体的问题而是机制的问题,所以地方和政府财政的关系,涉及地方本身财政体系的安排问题。观察一下地方政府的收支结构,地方政府没有能够拥有,或者没有能够稳定拥有,履行它自身职能的相应的财力。
就全国的平均数而言,地方政府掌握的财力和它自身支出的比例是50%多一点。中央政府取得的财政收入真正用到中央一级支出的最多不过30%,大量的钱是要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实施一般转移支付、各种各样的转移支付,下达到地方政府去。所以怎么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体系,让地方政府有一个稳定的财力、财源和财权基础,是今后规范PPP的运作、发展关键所在。
因而有两个概念需要重提,一个概念是分税,另外一个概念是财权。第一,分税不同于分钱,分钱和分税不是一个概念,之所以1994年提出分税是奔着分金钱的矛盾和问题而去,所以我们现在的财税体制的这种改革,特别是中央地方之间的改革,是围绕着分税而展开的还是围绕着分钱而展开的?不是说你干多少事我给你多少钱这事就解决了,小岗村当年的改革不就是把分钱、分粮改成了分田而导致的结果吗?类似这样的事情不用多说这是需要改变的理念。
第二,财权和财力也不是一回事,财权是处理地方财政收支的自主的一种权利,不是说你需要多少钱我给了你多少财力就可以解决问题这都是可以很深的问题,我们不用展开。
四中全会在这方面有新的表述,在谈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时候,提到优化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这里财权的二字对我们而言是久违的概念。
再联想新税法明确说国家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在讨论PPP时,把财权问题、分税问题纳入我们的事业。可能是在今天讨论PPP,并且把PPP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接在一起所应有的一个启示。
在今后,中国PPP的事业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坚持和发展PPP这样一个事业的道路将会怎么样,将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我们能否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站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处理好和PPP有关的基础性改革这样一个大的问题。
本文为作者 2019年 11月 12日在北京大学 2019“全球PPP50人”论坛第二届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内容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