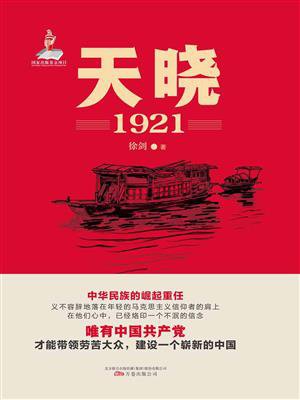1.风雪百里送君出津门
王会悟说,陈先生的名字如雷贯耳,她年轻时,是从《新青年》知道陈独秀其人其文的,但并未见过真人。在表侄沈雁冰那里,一拨年轻人常提及陈先生的锦绣文章,敬仰之情溢于言表。1920年2月,在《新青年》编辑部里,陈独秀真的向她走来了,这颗她仰望已久的新文化运动的巨星,悄然出现在上海,出现在她的面前。他是从北京由李大钊护送,秘密走滦州、乐亭,转道天津,来到上海,住进了渔阳里2号。
听着王会悟的叙述,我想起2019年6月22日,淅淅沥沥的烟雨,闷憋成一城瓢泼大雨。我从无锡而来,行一路雨天,为的是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车到了嘉兴湖畔,大雨依旧,仿佛天漏了。一脚跨出车门,遍地积水,如城郭落瀑,从高天砸下,还伴有雷声、雨声。一道道闪电穿云带雨,划破南湖的宁静。
坐上一艘画舫,游入烟雨南湖。雨点在玻璃般的湖面上镶嵌了一粒粒白珍珠。烟雨楼在视线中渐次放大。登岛时,我发现那艘“红船”旧影斑驳,或许在嘉兴湖中已泊了百年,等待风雨故人来。绕岛一圈,登烟雨阁远眺,觅那个革命年代消声于云天,与惊雷合成岁月的回响。回到船上,撑船向南湖革命纪念馆疾行。彼时,风一阵,雨一阵,梅雨越下越大了,我离船上岸疾步走向南湖革命纪念馆。登上二楼,在十三位中共一大出席者的照片前走过。一幅巨大的油画伫立眼前,北国大雪,一辆带兜篷的骡车前,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南陈北李立于雪中。看得出,油画的背景是北京故宫护城河东角楼街道旁,一匹黑骡拉着兜篷车正停在那里。众所周知的两位尊者并肩走来,李大钊在左,头戴水貂帽,穿一件狐狸领的皮大衣,陈独秀在右,戴一顶灰色的毡帽,着一件长棉袍,脖子上围着一条米色围巾,踏雪将行。
作者是原南京军区创作室的陈坚,我熟悉的一位油画家。油画前的铜牌上嵌了八个大字: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送君百里,终有一别。彼时,两位大教授紧紧地握手。此去沪上,两位贤者皆心照不宣,该说的话,已经说得差不多,该商量的事情,也都商量得差不多了。陈独秀该登车了,去往火车站,向南,从天津驶去上海,李大钊也该坐骡车返回北京。
李大钊坐上骡车,掉头转弯时向陈独秀踏雪而去的背影喊了一声:仲甫珍重!
守常保重!
……
清脆的骡蹄声,从北京驶往燕赵的冰雪道上传来,车碾在冰雪里,骡蹄声响不绝。百里风雪送君出京门,这是1920年2月,一个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前的清晨吗?
记得少年时,有一句黄钟大吕般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们“向冬宫开炮”的炮声,震动了世界。这时,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登上了历史前台,向黑暗沉沉的中国,喊出了科学、民主的时代先声,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埋下了思想的种子。当这场影响中国百年的运动将近尾声时,这位北大文科学长,因在北京城南香厂新世界楼上撒传单,被北洋军阀政府的警察抓捕了,这是他第二次坐牢。第一次是在安徽,差点儿被芜湖驻军首领龚振鹏砍了脑袋。可他一点儿也不惧怕,面对随时都会被绑赴法场的危险,他怡然自处,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

这次是在北京,这位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被关进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监狱,引起天下一片哗然。营救他的人,从北大校长蔡元培始,李大钊、胡适等皆站了出来,向政府施压,甚至连孙中山先生也站出来为他说话,正告北洋军阀政府,放人。
身在狱中的陈独秀,自然不知道铁窗之外的世界。坐牢,对于这位大教授而言,一点儿也不值得畏惧。在他看来,监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某种意义上,更是人类思想家的锤炼场。他盘腿而坐,面对铁窗、高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是一种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怆然。从青年时漂洋过海到日本留学起,他就在思考救国图强之路。
1901年秋天,陈独秀二十二岁,他想去看看世界。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走向西学之路,国力日盛,中国不少青年学子东渡扶桑留学,以寻找强国之道。仅20世纪的第一年,赴日留学者就达一千五百人之多,陈独秀也卷进了这股留学浪潮。他属意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那天,他扛了一个行李箱,与哥哥一道,往离家仅数百米的安庆南码头走去。登船,挥手兹别时,故乡在视野里渐行渐远,落成一个小小的墨点。站在甲板上,秋江澄清,两岸芦花白,横在家门口的大江,是他自小游泳的河流。在陈独秀的眼里,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如此时的大清帝国,水涸江枯,河床露出水面,平沙落雁,早已蓬头垢面,她的不肖子孙们,对她无药可施。彼时,大清王朝陷入衰败末季,像龙陷浅滩一样,几度幻想振翮再起,终归折戟沉沙。大清帝国之船正朝一个深海冰沟里撞去,最终的结局不外江山倾倒,政息人亡。此前,陈独秀的母亲刚刚病逝,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亲娘,不想再失去另一位祖国母亲了。他顺江而下,到了上海,哥哥则去东北,找自己的叔父,做候补道员。他来到吴淞口的一个码头,登上了一条邮船,驶往扶桑之国。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船近日本鹿儿岛。秋阳照在海上,透过舷窗照进船舱。他走上甲板,脑际掠过的却是七年前那场大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虽然这里离黄海大东沟很远,可是日本舰队就是从这里北上黄海的。
那是一场令国人伤痛之战,北洋水师舰沉之时,师夷之技、走船坚炮利之路的洋务运动也完成了最后的海葬,永远浸泡在冰海里,再无翻身之日。读史的陈独秀异常清醒,七年前那场大海战离自己并不远。六十年前,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百年闭关自守的大门,强行通关,把鸦片等货物倾销中国。因此,第一批站出来自救的是一些有头脑的封疆大吏,在不动国本的前提下,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洋务运动骤然而兴,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族企业应运而生,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居然打造出了亚洲最大的北洋水师舰队,一批留英学童毕业归国担任统领、管带,但还是在冰与剑、火与水的碰撞中折戟沉海,以清政府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落幕。孰料却在赴京会试的举子中引起轩然大波,广东康南海(康有为)趁入京应试之机,联合十八省一千三百名应试举子,发动了“公车上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尤其是倡导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较洋务运动众臣的图强之道,前进了一大步。然而,就在陈独秀参加江南乡试落第的第二年,康梁变法失败,六君子人头落地。陈独秀对大清王朝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帝国病入膏肓,犹如一段行将腐朽的枯木,离死期不远了。他东渡日本,寻找强国之路。第一次未入东京专门学校,而先在高等师范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然,仅仅待了三四个月,1902年春天,他便返回安庆。到这年9月,陈独秀又二度赴日,未报考他曾经心仪的日本东京专门学校,而是入成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军事,与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同学闯入大清国陆军学监姚煜的宿舍,剪其辫子,以示斩首,因而被日警逮捕,遣返中国。1907年春天,陈独秀第三次入日本留学,至1909年的三年之间,三进三出日本,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同盟会会员有了深度接触,成为挚友,一起投入推翻帝制的斗争中。
帝国真的死了,随着武昌首义一声枪响,千年帝制一夜崩溃,陈独秀也一度成为民国元年皖军都督孙毓筠的都督府秘书长。孙都督系公子哥儿出身,后又染上鸦片瘾,不理政事,都督府的大事小情全托付给陈独秀。但陈独秀因过于急躁,常为改革之事与人口角。每逢开会,总是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且固执己见,最终仅做了半年皖军都督府秘书长,便高处不胜寒,挂冠而去。
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去日本留学,这是他最后一次日本之行,也是他在日本住得最久的一次,近一年时间。此行,他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两位好朋友章士钊和李大钊。两个人名字都落在一个“钊”字上,从字形上看,“钊”含匕首,意为削去金属之角。而他们的志向便是要削去旧中国身上的痼疾顽症。特别是李大钊,是一位可托六尺之躯、寄百里之命的挚友。前者,陈独秀帮他编辑《甲寅》杂志;后者,则是先慕其文,后仰其人。章士钊这样记述他与李大钊的相识:“一九一四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
 陈独秀便是通过章士钊而识李大钊,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交往与友谊,直至李大钊溘然离去,血沃中华。
陈独秀便是通过章士钊而识李大钊,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交往与友谊,直至李大钊溘然离去,血沃中华。
扶桑一载,时光太匆匆,在与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章士钊等人共同编辑撰文的《甲寅》杂志中,陈独秀才情狂放、天马行空的政论如东风四起,吹皱一湾春水。日本岛国求学,学业虽未成,却遇神交挚友,斗室榻榻米上相谈甚欢,陈独秀不思归了。可是他夫人的健康却不允许他继续留在他乡。1915年4月,高君曼的身体开始出现不适。据陈独秀的朋友汪孟邹《梦舟日记》记载:4月25日,高氏“体气不佳,家中寂寞,甚为悲伤,竟至泣下”,而5月15日,“忽咯血”,18日,“咯血之症昨夕又发”,24日,“至同仁医院,察其病状,似渐加重,渠自己亦极畏惧,一种凄凉之状,令人心悸”。据此,汪孟邹看不下去了,给在日本的陈独秀写信,催他返国。
陈独秀回国了。他伫立于黄浦江畔,手擎一个思想的火球,将它投向长街黝黑的东方之城。火球沿街衢闾巷而滚,所过之处,火光四溢,一窗、一门、一户、一院,一个里弄,一条老街,瞬间亮了起来。一个民国初年的思想烧荒者兀自而立,陈独秀堪为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