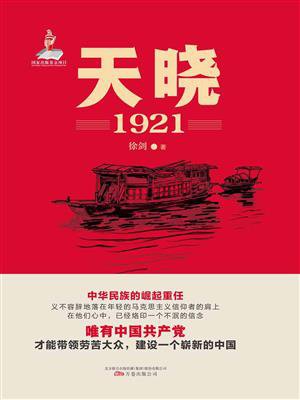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我凝视南湖革命纪念馆的那幅油画,“南陈北李”踏雪而去,于故宫东角楼登车,上车的地点距离北大红楼图书馆不远。通行的说法是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送陈独秀,经廊坊,直奔天津,然后登车南下上海。
但是,按照胡适的说法,陈、李登上骡车后,故意北去,让赶车人载着他们驰向离滦州不远的乐亭县,在李大钊老家躲了数日,风声渐息后,再从李大钊家坐骡车,突然南去,送陈独秀直奔天津,登上列车,南下上海。
冀东平原上,驰道覆盖一层白雪,寒烟孤村。一辆骡拉篷车在白雪覆盖的旷野碾过,大平原寂然无声,孤树上有一群寒鸦盘旋,车辇驶了过去,惊起寒鸦一片,复又栖息树上,尖啸的聒噪,哀鸣不绝。
两条深深的车辙留在北方大平原上,它是通向一条人间正道的岔道和路标,还是一代中国共产党的先驱留给后世的一道历史车痕?此时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南陈北李在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大车道上,讨论、商量,相约携手建党的故事。
……
天阴沉沉的,6月的上海,梅雨没有落下来,天有点儿闷,但没有想象中那般热。那天中午,我背着一个双肩背包,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展板前踯躅两个多小时,边看边记边拍,留下资料。下到一楼,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参观的人流量大了起来。在纪念馆图书专卖柜前,我买了一部《伟大的开端》。转出书屋,继续沿参观路线行走,进入望志路106号石库门——我向往已久的李公馆。当时,游人稀少。
走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记录一代代仁人志士的文字与照片令我肃然起敬。展板图说就像淬火的铸字,诠释旁边一尊铜雕的背景。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避免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和他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
铜板白字,下边印有英文解说,镶于一面情景再现的砖墙上。
我侧身走过,在一幅铜雕背景画前驻足。斯人,此景,与我后来在南湖革命纪念馆见到的巨幅油画《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异曲同工,是同一种情景再现。只是两个人的装束和背景不大相同。如果说南湖革命纪念馆画的是起点,南陈、北李在故宫东角楼登车前交谈,再别红楼;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画的则是终点。风雪迷茫的大平原,一条大车道伸向远方,寒林落叶,树梢犹如剑戟般伸向空中,赶车人喝马暂停。车辕上,李大钊、陈独秀掀开车帘,相继跃身下车,沿大车道前行,兀自立于旷野上。两道深深的辙痕嵌入北方古原的腹心,也通向远方。长亭外,古道旁,下车的陈独秀居前几步,他的服饰与南湖革命纪念馆纪念画中李大钊的调换了,穿一件西装领的皮大衣,而李大钊则穿一件中式棉袍。陈独秀目视前方,仿佛在考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百里送君行,守常与仲甫东瀛相识,已有六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心心相印,依依惜别,两个人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那还说点儿什么呢?再酝酿一下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情吧。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这样实景再现了出来。解放日报社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写的《伟大的开端》一书中这样写道:
那是1920年2月的一个凌晨,说是凌晨,还有星光依稀,但路上仍是黑得瘆人。北京朝阳门,此时驶出一辆旧式带篷骡车,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卷起了一路行尘。车上有两位乘客,坐在车篷里的一位,四十岁左右模样,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头上低低地压着一顶呢帽,看上去像个掌柜;坐在驾辕人旁边的一位,年龄看上去要小一些,微胖的脸庞蓄着八字胡,戴一副金边眼镜,随身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像是一个年前随掌柜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此时,正值生意人在年底往各地收账之际。
谁也不知道,在这辆不起眼的骡车上坐着的,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
……
那辆旧式带篷骡车一路南行,经廊坊转道天津。
北京至天津,大约一百五十公里,坐骡车赶路,须费时两天。两个同路人,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一边赶路一边交谈。历史为陈独秀和李大钊提供了一次可以更广泛交流、更深入沟通的机会,也给后人留下了“南陈北李”在这段行程中“相约建党”的佳话。

当时曾有一首嵌名诗,是一位叫征宇的革命家赋的:“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

依我读诗的感觉和判断,此诗少了民国风,多了革命味。但毫无疑问,这是“南陈北李”提法的来源。后来查证,征宇的真名叫罗章龙,是当年追随“南陈北李”的北大学生,年轻时也是一位激情的革命者。
但是真正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根据几部回忆录追根溯源,最早出自陈独秀与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的好友高一涵。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等八十余人,4月28日,将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者绞死于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这年5月,在李大钊的追悼大会上,高一涵在悼念演讲中这样说:
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与先生(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治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

这次讲演后,高一涵写过一篇悼念李大钊的文章,非常生动地描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是如何避险离京的,坐的是什么车辆,人化装成什么样子,在路上谈论了什么,写得非常生动、逼真。该文发表在1927年5月23日《中央副刊》第60号《李大钊先生传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高一涵又相继写了数篇回忆李大钊的文章:《和大钊同志相处的时候》,载于1957年4月27日的《工人日报》;《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1963年10月执笔),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这些文章都是讲“南陈北李,百里相送”的故事,商谈的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未来。
……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发着光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边,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着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之后,才回北京。

《陈独秀大传》的作者任建树在其五十余万字大著中,也引用了高一涵的回忆文章《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中的片段,并专门另辟一节《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1920年,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幼芽——共产党的发起组,在好几个大城市里先后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参加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大半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发轫于中国近代工商业最发达、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上海,李大钊策划于中国的首都北京。两位巨人一南一北相约筹建中国共产党。进步青年誉称“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里,李大钊送陈独秀登车的大幅油画前,展板上镶嵌着八个大字: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从这个起点,再到今天,百年之间,我们党的初心,始终未变。
傍晚,从南湖革命纪念馆出来时,雨仍在下。天光暗淡,我从雨幕中匆匆走过,想起胡适先生说过的一段话:
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在写作《天晓——1921》的日子里,我的案头始终放着一套《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涉猎了各种学术文章和专著后,我始终以这部权威的范本校正我的思绪流向。《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写道: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时陈独秀已将关注的主要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从进步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这是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最大肯定,也佐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