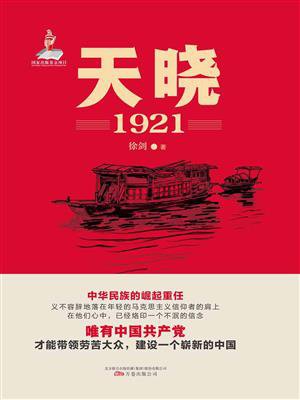4.《晨报》《学灯》与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
夜雨一直在下,在嘉兴城吃过晚饭后,天已经黑了下来。
江南的梅雨是温婉的。雨打车窗,偶然与路灯、霓虹相遇,连挂在玻璃上的雨瀑都是温润的。我的思想在穿越,忽而想到了胡适对“南陈北李”的评价。车子穿越雨幕,城郭、田园从车窗两侧淌过,也将我的思绪带到从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请胡适做口述历史,说起自己《新青年》时的老朋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走向马克思主义比之李大钊晚了些时日。
李大钊无疑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胡适说李大钊在1918年至1919年之间,便开始写文章颂扬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了。李大钊第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写于1918年,论述的就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其资料翔实,文笔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法国大革命,预示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而俄国十月革命,则预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曙光”。而在这一年,他还写了两篇同样重要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地赞扬了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的历史潮流,什么皇帝、大臣、军阀、贵族、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上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预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遥想当年,南陈北李,同在一个国度留学,同在一个杂志社做编辑,同在一所大学里教书,同在一个大中国,南北相望,携手建党,为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费尽心力。他们1915年先后从日本归国,陈独秀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成为民国初年唤起民众觉悟的第一刊,而李大钊则在北京成了《晨钟报》(后改为《晨报》)的编辑部主任,一刊一报,遥相呼应,呈南北掎角之势,宣传科学与民主。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陈、李相会于京城,陈独秀被邀为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被邀为北大文科教授,不久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从此《新青年》移师北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等人同为主要撰稿人。对于李大钊成为中国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党史界普遍看法是,他于1919年夏,避险河北昌黎,写了那篇值得永远纪念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于《新青年》)。文中,他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明确地陈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见解。雄文惊天下,从此一百年间,中共的党史界,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都绕不开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几乎全都认为,是他敲响了东方天晓的第一记晨钟。
晨钟鸣春,百年第一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当之无愧。可是,当时的中国,还会不会有与李大钊一样的人,同步敲响中国黑夜将尽、五更寒天里的晨钟呢?石川祯浩经过多年认真的考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只有十月革命第一声炮响,还有一条更早的海上之路,即被中国史家和研究者们长期忽略的日本传播渠道,就是通过中国留日学生带进来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社会主义者翻译的文章。
石川祯浩以他的前辈曾向中国传播过马克思主义为荣。事实真是如此吗?彼时,我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星空,投向民国初年,一批政治精英或长袍马褂,或西装革履,或布衣长衫,朝向我走了过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鲁迅,《新青年》编辑部八位重要编辑,半数以上曾留学日本。中共一大十三位参加者中,李汉俊、李达、董必武、周佛海都有留日经历,若加上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达六人之多。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周围,更是聚集着一批日本归来的学子,有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等诸公。
石川祯浩强调,1919年夏,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写就之际,北京《晨报》第七版(即《晨报》副刊)和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已经在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
本来,北京《晨报》属于康有为的研究系,是一个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李大钊从日本归国后,曾在《晨报》的前身《晨钟报》担任过编辑部主任,尽管时间不长,但他的影响力已不可低估。“五四”前夜,应当是1919年2月,北京正沉浸在一种过年的气氛中时,北京《晨报》突然在那个月初,专门辟出两个专栏“自由论坛”和“译丛”,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一部重头书稿是这年4月开始连载的《近代社会主义的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所著《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二天,5月5日起,以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形式,又连载了河上肇的第二本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译者是化名为“渊泉”的人。到了5月9日,刊登了食力译的《劳动与资本》。进入6月,又连载了渊泉译的《马氏资本论释义》
 。这次连载,因为各种原因,一度中断过,但最终连载到了这年11月,也就是李大钊避险昌黎时。7月,北京《晨报》副刊又刊登了《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原著是日本学者堺利彦写的《唯物史观概要》。随后,刊登了《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这是贺川丰彦写的,原著发表在《改造》1919年7月号上;紧随其后,他的另一篇大作《唯心的经济史观的意义》发表,这篇译文没有标明译自谁手,但似乎也使人们想起同一个译者:渊泉。
。这次连载,因为各种原因,一度中断过,但最终连载到了这年11月,也就是李大钊避险昌黎时。7月,北京《晨报》副刊又刊登了《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原著是日本学者堺利彦写的《唯物史观概要》。随后,刊登了《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这是贺川丰彦写的,原著发表在《改造》1919年7月号上;紧随其后,他的另一篇大作《唯心的经济史观的意义》发表,这篇译文没有标明译自谁手,但似乎也使人们想起同一个译者:渊泉。
《晨报》一唱报天晓。它不仅最早在中国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使后来流行了百年的“生产方式”“社会意识形态”“上部构造(上层建筑)”“下部构造(下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等社会科学术语,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的阅读语境里。于是,当时影响极大的《新青年》《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甚至远在四川的《民国公报》都争相转载这些文章。尤其是从6月一直连载到11月的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其德语版、日语版几乎同步在欧洲和日本发行,被认为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最简明且准确的著述。高畠素之译的日语版《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被坊间的译家誉为“无论谁来翻译,要做到比这更容易,恐怕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有人读这部译著还感到不好理解,那么,读德语原文,也免不了作同样的感想”。尽管这年9月这部书的汉译单行本在中国发行时,没有日文版那样轰动,可是人们却一直津津乐道于北京《晨报》副刊编辑的眼界和见识,纷纷询问译者渊泉是谁。
有人一直将“渊泉”这个译名与李大钊张冠李戴。可是严谨的中共党史专家很快便查明,渊泉并非李大钊。那么这个署名“渊泉”的人到底是谁呢?渊泉又名陈溥贤,字博生,福建闽侯人。李大钊与陈溥贤,冀东平原与东南沿海,隔着千山万水,可是两个人的生命之旅却在许多段落重合。李大钊长陈溥贤两岁,两个人先后东渡扶桑,为早稻田大学同学,都是学政治经济学科,留日期间,一同反对袁世凯称帝,在《民彝》《民鼻》杂志上撰稿,并在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同列委员。1916年又一起回国,同入《晨钟报》做编辑,李大钊离开后,陈溥贤一直在《晨报》做事,并在1918年末,以《晨报》记者身份被派驻东京,发来许多关于“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最前沿的报道。五四运动前,他当上了《晨报》总编辑。有一点可以肯定,1919年的春天,《晨报》大量发表了从日本翻译过来的马克思资本论、唯物史观等共产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另一个渠道。
1919年北京的夏天有点儿燥热。因为五四运动后大批学生被捕,陈独秀也下狱了,所以李大钊的心情很沉重。他对学生罗章龙交代,打通关节,全力营救陈独秀先生,可铁幕重重,一直无消息。暑假将近了,每年夏天他都回老家,到海边避暑,在旷野和海边上行走,极目远方,想想中国的过去与未来。去年晚秋,老同学陈溥贤作为《晨报》的记者常驻东京,他从那里发来了一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文章和专著,其中包括河上肇、堺利彦、高畠素之等人的译著。河上肇创刊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杂志,第一期竟售出了12万册。党史专家认为,李大钊于1919年夏秋之间写的那篇雄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多少有点儿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子。
李大钊写下那篇划时代的文章,就等于是在向中国宣布,他已经是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或许这就是李大钊欲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个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