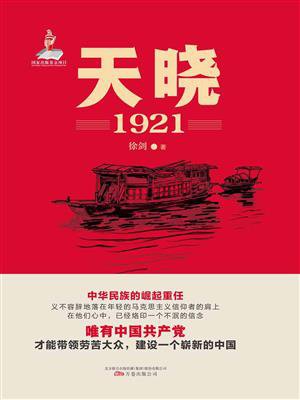5. 革命局,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你该返回到上海了吧?雨中,我似乎听到天堂里有个声音在呼唤我呢。她说,我看到你啦,嘉兴的雨下得好大呀,你们还坐了一艘画舫,驶入南湖,登上了烟雨楼。会悟奶奶,这些您都看到了呀?你们坐的画舫有点儿像我们当年开会的样子,不过,我们那艘画舫啊,没有你们坐的这艘大呀。我在红船前站了好一会儿,冥冥之中,好像看到您打着一把油纸伞,坐在红船的船头放哨呢。
江南雨幕雾锁楼台水榭,我从嘉兴返回无锡的路上,雨一直下得很大。上车不久,因为有点儿冷,车里开了暖风,很快我就眯着了,做了一个长长的仲夏夜之梦。这梦的时空,离中共一大开会的那个时辰并不远,或许这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记忆未尽,我居然梦见了王会悟。此时,一个一直无解的问题,又萦绕在我心头。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伊尔库茨克东方民族处的报告,第一次提到了“革命局”三个字,说到了革命局下属三个处之一的出版处的活动。可是对于“革命局”这三个字,王会悟也觉得很陌生,是因为译法不同吗?可是,有关上海的“革命局”的三个处的活动,其中出版处的活动是这样记述的:“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经译载在报刊上了。《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十五种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复印……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处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创刊号。它们是周报,印刷两千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处印刷厂承印。”
王会悟说,记得1920年夏天,陈独秀先生将《新青年》移师上海后会见俄乡密使维经斯基,成立了革命局,下设出版处,之后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就有经费了,不会再因杂志收入太低而陷入窘迫。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俄罗斯研究》等,主要的稿源也取自《苏维埃·俄罗斯》等美国刊物上布尔什维克刊载的文章,而推荐这些文章给《新青年》的,正是维经斯基他们。其实这些关系与资源,都与维经斯基的到来有关。因维经斯基曾经在美国待过,故与美国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宣传组织接上了头,不少书籍直接从美国寄到了上海,开始翻译与传播。为何维经斯基一到中国就有了这些资源,这恐怕与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维经斯基前半生,移居北美时,曾经加入美国社会党,他对于美国社会主义文献的出版情况,至少比上海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熟悉得多。据此可以断定,报告中提到的刊物自不必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比如说,1920年下半年译成汉语的美国社会党系统出版社(芝加哥的查尔斯·H.克尔出版社)的刊物都可以尽拾囊中,要么是维经斯基提供的,要么是他帮助订阅的。
彼时,一大批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发行,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让处于苍茫黑夜中的中国人,感到东方的地平线上,天边裂罅,露出一线黎明之光。
彼时,我想起了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词《清平乐·会昌》,乃我少年时代背诵过的,“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百年中国,正是有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贤踽踽独行,他们的历史脚印,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连成一条百年沧桑大道。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康梁公车上书、变法图强,直至辛亥革命,一代代仁人志士的探索,均告失败,唯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为浸沉在黑夜中的中国,点燃一簇理想篝火,天将破晓。庄子曾在千年前《天地》篇中仰天感叹:“冥冥之中,独见晓焉。”天将欲晓,你的、我的1921,只差一声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