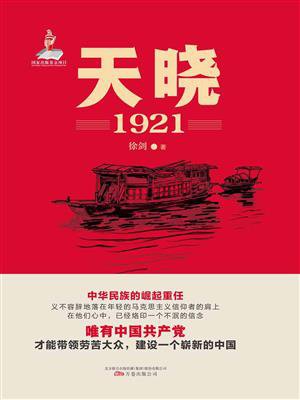6.华夏一声雷,《共产党宣言》出版
入夏,江南梅雨天来得有点儿早,墨云锁城,天要下雨了。闪电撕开云层,仿佛一株银色天树镶嵌于天上人间,根须纵横云间,倏然,闷雷响彻天地,整座申城都在颤抖。
王会悟在上海渔阳里2号楼上,忘情地读着一本书。书是住在楼下的书生李达送给她的,不厚,薄薄一本小册子,可捧在手里,却如天上惊雷落于掌上。它的名字叫《共产党宣言》。
轰隆隆的声波掠过城郭上空,一记惊雷从云间传出,犹如巨浪袭来。阁楼似乎在晃,王会悟的肩膀也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心在颤动,天又打雷啦!
彼时,她住在陈独秀先生家的楼上,或许她并未真正意识到,这座石库门,这些《新青年》编辑部里的年轻人,这些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精英,皆是手握雷霆、藏雷纳电之人,他们于黄浦江岸边兀自而立,最早听到霜天晓角。雷声起于一部印有大胡子马克思头像的小册子。
那天,王会悟又见到了她的表侄沈雁冰。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上班,也是《新青年》的撰稿人之一,不时会来渔阳里2号雅聚。见到小自己两岁的表姑,他倒没有姑侄之间的拘束,都是同龄人,又是革命者,见面便问:会悟,最近在读什么书?
李达送我一本新书。
什么新书?
《共产党宣言》哪,据说是刚印出来的!是一个油印本,只有五十六页,封面上印着红底的马克思肖像。
我查证不到这个情景出于何处,只能基于一种历史的想象与推理的复原吧。毫无疑问,当维经斯基拿到这个小册子,凝视封面木刻水印的马克思头像的《共产党宣言》时,他兴奋地向远东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处报告。
哦!与维经斯基一样高兴的人便是陈望道了。
时隔很多年后,静心于修辞学研究与教学的陈望道,偶然与党史访问学者谈及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情况,心情非常平静。可是作为《共产党宣言》全本中文翻译第一人,他仍掩饰不住几分激动,忆及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始末:
回国(1919年6月)后,我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非孝》的文章,遭到顽固势力的猛烈攻击,牵涉到我,我也被扣上“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随即离开一师,回家乡义乌译《共产党宣言》。我是从日文转译的,书是戴季陶供给我的。译好后,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设法出版。

那个冬天,一天早晨,邮差送来一封寄自上海的信,陈望道俯首一看,左下落款邵缄,是邵力子先生寄来的。未拆开前,他以为是约稿信,因为邵先生是《民国日报》的编辑,经常向他约稿。在一师任教期间,他为《民国日报》写了不少文章,邵先生对他的文笔很欣赏。可撕开信一阅,陈望道脸上浮出了笑容,原来是邵力子邀请他为戴季陶《星期评论》周刊翻译《共产党宣言》。于是陈望道兴冲冲地去了上海。
20世纪初的中国天空下,陈望道并不是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可作为全译本,他确实是第一人。此前,关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也有只言片语通过《万国公报》《民报》等传入了中国。1912年《新世界》发表了节译的《共产党宣言》。五四运动前后,《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刊物也曾对《共产党宣言》作过一些零星或片段似的摘译。但这一次,一直未在中国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如突然间平地一声惊雷,出现在上海。
陈望道坐车,换船,进入上海后径直去了民国日报社。邵力子已擢升总编辑,他比陈望道大九岁,都是浙江人,一个长于绍兴,一个家在义乌,前者为老同盟会员,后者则是学界新秀,都有日本留学的背景,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寒暄之时,陈望道谢邵力子的上海之邀。邵力子摇头,说非我所约,而是季陶先生所请。
戴先生?
对!
他请望道老弟出山,是想翻译一部皇皇巨著《共产党宣言》。啊,陈望道听到此,眼睛里重又燃起了一团希望之火。我能担当此任?戴先生说了,非陈君莫属。
五四运动后的戴季陶,年近三十,胸中仍有一腔热血奔突,虽追随中山先生多年,投身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但思想激进。他与浙江巨富沈玄庐在沪上创办《星期评论》,李汉俊也加盟其中,介绍研究国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和新思潮,一时与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齐名。然,戴季陶有一个夙愿,当年从日本归国时,他带回一部由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欲想转译为中文,却浅尝辄止,因为翻译的难度太大了,非他的笔力可抵,且编务又那么忙。“不如邀人翻译,并在《星期评论》上连载。”
 见到好友邵力子时,他道出了自己的初衷,两个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戴季陶喟然长叹:“可是何君能担此大任呢?”
见到好友邵力子时,他道出了自己的初衷,两个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戴季陶喟然长叹:“可是何君能担此大任呢?”
“非杭州陈望道莫属!”邵力子答道,“陈君文章、笔译和古学功底,堪称一流。”
“对啊,我咋没有想到他呢!”
邵力子、戴季陶点将,陈望道如约而至。那天,邵力子带着陈望道一起去《星期评论》编辑部,见到了戴季陶。寒暄过后,戴从抽屉中拿出珍藏已久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说,这是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书,我当年从日本带回,就交给望道兄了。
陈望道说,我留学日本时,幸德秋水已因“大逆事件”被杀,作品被禁,像这样的书几乎见不到啦。但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我都曾接触过,请教过他们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算略知一二啊。
好啊!就拜托望道兄了。
双方就此别过。返回浙江的路上,淅沥数日的雨天突然放晴了,陈望道的心情也随即晴朗起来。“一师风潮”后,他怅惘极了,一直纠结于“新”与“旧”的交战中。返乡道上,边走边读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他蓦地觉得,黯淡许久的心情突然被一束思想光芒照亮了。
何处择一室以译经典?陈望道想到自己的故里——义乌分水塘
 。彼时,因为村前有一池塘,乃上游清溪流出,一池碧波分两水,一系流向义乌县城,一系流至邻近的浦江县,两水交叉口有一小村庄,故而得名分水塘。这是陈望道生于斯、长于斯的桑梓,直到外出求学、留学前,他都未曾离开过。这是一个“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桃花源。离开西子湖畔的喧嚣,他走进了老屋,那间仍旧遗存着祖先气息和体温的老屋。屋里无桌子,只有一盏油灯,他便干脆将一块铺板架在了两条板凳之上,以木板为桌,展开稿纸,开始一段一页、逐字逐句地翻译。
。彼时,因为村前有一池塘,乃上游清溪流出,一池碧波分两水,一系流向义乌县城,一系流至邻近的浦江县,两水交叉口有一小村庄,故而得名分水塘。这是陈望道生于斯、长于斯的桑梓,直到外出求学、留学前,他都未曾离开过。这是一个“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桃花源。离开西子湖畔的喧嚣,他走进了老屋,那间仍旧遗存着祖先气息和体温的老屋。屋里无桌子,只有一盏油灯,他便干脆将一块铺板架在了两条板凳之上,以木板为桌,展开稿纸,开始一段一页、逐字逐句地翻译。
一盏油灯昏黄,将陈望道的影子投到了墙壁上,长长的,变形般地拉长,几乎覆盖了一堵墙壁。他才翻译完第一段话,便被这篇雄文点燃了,作为政治宣言书,竟然可以这样去写。他沉醉在优美的文字中,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暖意,尽管窗外仍是寒冬腊月,他却仿佛已经听到了春天的脚步,时代的脚步。
那一刻,他心中突然萌生一种感觉、感动,《共产党宣言》恰似华夏春雷第一声,震醒了多少迷惘的中国人。江南起惊雷,这之江大地一道闪电,让每个在黑暗中探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突然有了长夜中被篝火和灯塔照亮的感觉。
那些日子,陈望道蛰伏于老屋里,足不出户,几乎是夜以继日地翻译书稿。困极了,就将书和墨盒、文稿挪开,到床上一躺,就睡了。饭是由母亲送来的,母亲以为他在复习备考,在做大事情,每天按时给他送中饭、晚餐。
我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看展览时,解说员绘声绘色地讲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一个小故事——吃墨汁。那时他翻译《共产党宣言》进入物我两忘之境,几乎是废寝忘食。有一天,母亲从厨房里给他端来一盘粽子,还有红糖水,可他太全神贯注了,竟浑然不知,在翻译书时头也不抬。母亲站在门外说,你吃粽子要蘸红糖水,他说知道了,可是他一边写中文,一边看外文字典,一边拿起一个粽子往红糖水里蘸。岂料他太投入了,误将墨汁当红糖水,居然将手中粽子蘸到了墨汁里边去,还说味道甜极了。母亲后来再进来时,发现他一嘴都是墨汁。惊讶地问道,望道,你怎么不吃红糖水,而吃墨汁呀?是吗?陈望道用袖子一抹嘴,果然见到一袖口的墨汁。他哈哈大笑,对母亲说,这是真理的味道。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看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展板时,还向同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起了这个真理味道的故事。
在故里蛰伏了一个漫长的季节。陈望道看着这份不到百页纸的书稿,最后再校正了一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向窗外望去。清明前的黄花连天际,彼时,他的心情犹如田野里的油菜花一样灿然。
窗外,布谷鸟叫春了,那短促、清脆的啼鸣,划破了旷野的寂静。好消息也借着春天的翅膀,飞到了义乌城边这座江南的小山村里。4月末,陈望道接到上海《星期评论》的来信,说戴季陶随孙中山先生南下了,《星期评论》编辑部缺人,编辑们一致投票,接任编辑者,非陈君莫属,快快来上海与大家一起共事吧。
漫卷译著喜欲狂,青春作伴去沪上。陈望道携着《共产党宣言》新译稿,走进大上海,此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情。然,走进《星期评论》编辑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者,戴季陶奉孙中山先生电召,已经去了广州,留下编辑空缺给了陈望道,使他不再为失业发愁;忧者,当时戴季陶答应在《星期评论》连载《共产党宣言》的事化作了泡影。当局对刊物实行邮检,凡激进之文,都受到严格控制,纵使自己做了《星期评论》的编辑,也不能任性连载。再则,译稿还须校订,等一切就绪之后,6月6日《星期评论》也停刊了。陈望道和他新译的《共产党宣言》陷入窘境。
有一天晚上,他的学生施存统和俞秀松来拜访。彼时,他俩已参加陈独秀发起组织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而俞秀松正准备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施存统去年因一篇《非孝》让老师丢了饭碗,自己被开除学籍,可在浙江一师时,他一直将陈望道视为偶像。但是自从接触陈独秀后,他觉得北大前文科学长的理论和辩才更胜老师一筹。陈望道谈起自己的新译《共产党宣言》还在做最后润色和修订,出版无望,颇有几分怅然。
何不请仲甫公一阅?俞秀松建议道。
你说的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先生啊,我心仪已久。陈望道说,正想结识他呢!
老师,将《共产党宣言》的译稿交给我吧,我送到仲甫先生家去。
于是,那天上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交给俞秀松。
陈独秀如获至宝。那个上海的雨夜,街衢上静悄悄的,渔阳里2号的阁楼上,雨打梅花窗,一盏油灯,几乎彻夜不灭。陈独秀伏案看至天明,东方破晓时,他校改完这部汉译本,不由得拍案惊奇,连称“皇皇大作啊”。当读到最后一句话“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啊”(后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他更是击节而叹,雄文,雄文啊!
陈独秀推开阁楼的窗子,正是梅雨季节,天空仍旧下着雨,远眺上海的黎明,天与海的交接处乌云翻卷,可是东方天幕上却裂开一道云罅,筛下一抹晓色。继而,一道道闪电裂帛撕云,闪亮天际,随后一声惊雷,朝东方城郭劈了下来。对处于苍茫黑夜中的中国啊,这不啻是夏日晓天一记霹雳!他俯首看去,那华夏的第一声惊雷,那道闪电,已落在陈望道刚译好的《共产党宣言》上。书中那些坚不可摧的学理和观点雷一般地击中了他,灵魂被震撼,思想的燧石电火燃烧成熊熊烈焰。他是高举过“五四”大纛的旗手,大半生追求科学、民主与自由,心性孤高,雄睨宇内,并不是一个轻易在理论上被折服的人。可是当他校注完《共产党宣言》时,他还是被书中闪烁的思想与哲学光芒照亮了,仿佛探索了大半生的救国之道,终于在这里寻找到了答案。
第二天,他将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稿交给了李汉俊。李汉俊十四岁东渡扶桑,留学东京,通晓日、英、德、法四种语言。最后的校勘,唯有李汉俊能够接手,陈独秀可谓慧眼识才。
李汉俊与陈望道在《星期评论》一起做过编辑,共事一月有余,对陈望道的文字并不陌生。第一次拿到《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稿时,他也曾像陈独秀一样,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彼时,湖北潜江的李汉俊,可谓少年出英雄,家学渊源深厚;他少年即随大哥李书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日本,李汉俊与陈望道虽在不同的大学读书,可是都受过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李汉俊一页页读下来,觉得陈望道的译文语言高古、洗练,翻译准确,语气行云流水。他从日语上溯英文,再从英文直返德语,四种语言的比较中,觉得陈望道的译文规范、准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机理、概念和政治术语烂熟于心。他按照陈独秀先生之嘱,做了最后的校勘。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可出版经费难倒了陈独秀。踌躇之际,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会面了,提出成立革命局,下设三个处,且出版处是第一等要紧事情,经费一下子有了着落。
1920年8月初,《共产党宣言》终于付梓,印数一千册,是一个比小三十二开本还要小的开本。封面是红底马克思半身像,上边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署名“马格斯 安格尔斯 合著 陈望道 译”,页内没设目录,全文均为小五号铅字,但因校对有误,将书名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出了一个硬伤,可瑕不掩瑜。拿到这个小册子,维经斯基颇有几分激动地向伊尔库茨克民族处报告称,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了,《共产党宣言》已印好。
这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在东方的传播源流,也挺有意思。《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最早刊于1904年11月13日《平民新闻》周刊第53号上,转译自塞缪尔·穆尔的英译本。可后来日译本遭“报纸条例”封杀,自1906年3月在堺利彦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过全译本后,因“大逆事件”中幸德秋水被杀,从此再未见天日,只有手抄本流传民间。而戴季陶是如何得到《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的,引起了石川祯浩的好奇。他通过日译本来探究陈望道译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版的底本,通过比对《陈望道文集》,石川祯浩发现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底本最大可能性是发表于《社会主义研究》上的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合作的全译本,是当时在日本民间秘密流传的读本。他是从几个词的译法上破译的,比如说Bourgeois,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合译为绅士,陈译本则译为有产者。又如Proletariat,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合译为平民,陈译本则译为无产者,与当时民间流传油印本中的重要词相似。这个发现透出一个信息,戴季陶当年在日本留学归国时,居然带回了十几年前的日译手抄本,且只是地下秘密流传啊,弥足珍贵。
毋庸说,《共产党宣言》乃华夏第一声惊雷,影响之盛,出乎陈望道意料。仅广州平民书店,截至1926年,便重印了十七版。毛泽东就是此书的重要拥趸之一。他曾经对斯诺说过,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三部书对他影响甚大,最重要的一部就是《共产党宣言》。但是毛泽东1920年初次接触《共产党宣言》,是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比陈望道出版这本书要早。
一个人与一部书,一个时代与一部书,马克思在中国成了神一般的人物。作为《共产党宣言》第一位全本中文译者,陈望道成为陈独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后来他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
1975年1月22日,陈望道坐火车来到北京,踏雪赶至北海公园西侧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鲍正鹄闻讯后,立即赶至大门口迎接,向陈望道鞠躬道,北京下这么大的雪,老师远道而来,我们怎么敢当啊。老人平静一笑,说,你来看我不容易,我来容易,说走就走啊!鲍正鹄被老师的虚怀若谷感动,引领其进了办公室。陈先生刚坐定,他便说,这次请老师来,实则有事相求,就是想请您鉴定一下《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第一版。说着,鲍正鹄挥了挥手,说,拿过来吧,请老师过目。工作人员取来《共产党宣言》早期译本的多个版本,封面上皆印有马克思的头像,有红底的,蓝底的,但版权页已破损,无法辨认哪个是首版。陈望道仔细看来,然后指着一本封面印着红底马克思头像的版本说,这个红的是初印,那个蓝的是后印的,初印的“共产党”三个字还写错了。鲍正鹄说,老师为北图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过去我们一直将蓝底的当作首印版。说着,他将首版的《共产党宣言》递到陈望道面前,说,请老师题字留念吧。老人讶然,说这是马、恩的经典著作,我签名不合适。鲍正鹄道,您老是这部书的翻译啊,您不题,谁敢题?您签上名,就是一个历史鉴定。陈望道觉得学生说得对,于是翻开译本内页,工整地写下三个字:陈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