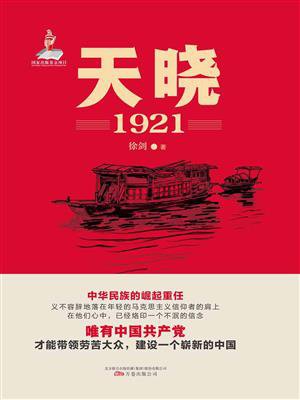7.王会悟:开会通知和旅差费已寄出
过了中秋,天气渐渐凉了。一阵阵秋风四起,风从苏州河边刮了过来,梅雨天被吹走了,上海的街衢变得清爽起来。弄堂里、石库门前,金桂怒放,像燃烧的火把,清馥浮浮冉冉,弥漫于里弄街边。一场秋风一场寒,花凋了,残香犹在,秋风香满楼,好一个江南的秋哟。
王会悟那天说,那个秋天,真的是金桂满堂。一夜之间,开至荼䕷花事了,好像都是为陈独秀先生开的,是献给他的啊!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同时还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 Y.),由俞秀松主持。沈雁冰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编《四部丛刊》,同时负责编辑《小说月报》,还翻译契诃夫的小说。《新青年》迁址上海后,陈独秀来找他约稿,写介绍俄国的文章,他就这样参加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因为与王会悟的这层亲戚关系,也经常来渔阳里2号的陈家。沈雁冰在《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写道:
就在这个夏天,大约7月光景,陈独秀他们要我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我记得小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芳,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小组开会的内容:交换别地小组的情况,研究发展组织,吸收新成员,研究开展宣传工作等。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新青年》宣传自己的主张。起初小组还利用过《时事新报》,后来张东荪退出小组,研究系的《时事新报》也跟着变了。当时小组还没有搞工人工作,后来大概是杨明斋到工人中去工作过。那时候,在萍乡安源,可能已有工人运动的工作了。……小组当时有个名称,我忘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石川祯浩在其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共传播”“第四节 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在中国的传播”“2.《共产党》杂志介绍欧美社会主义文献”中写道:“《共产党》月刊是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1月创办的党办机关刊物,从其名称可以看出,该刊物的创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陈独秀当了该刊物的主编,李达担任编辑,社址仍设在渔阳里2号。创刊号首发选定在11月7日,那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或许与维经斯基主导有关,他曾在8月17日向伊尔库茨克民族处报告,称这是“革命局”下设的出版处,办了杂志,有了印刷厂,给了编辑印刷经费,还出版了小册子。当时通过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未向社会公布,但在创刊号“世界消息”栏目中,第一次使用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说法。创刊号的发刊词写得很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缩写版。它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家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并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使资产阶级永远不致发生。”寥寥几句话,却掷地有声,标定了中国共产党出发的零公里。
20世纪50年代,即1956年至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部分中文文件,其中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里,载有一份写于1920年秋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篇宣言最早刊载于《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有学者从《共产党》月刊的发刊词和这份宣言的比对中,发现该宣言由正文和一位姓Chang的写于1921年12月10日的“前言”部分组成,正文分成三章,即“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正文仅有两千多字,《党史资料汇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印)第一号做过报道。
《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主张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生产手段收归社会公有,并预言,由于政权、军队等统治机构是保护少数人利益、压迫劳动群众的,将被废除。不过,这些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章中,提出了逐步实现的步骤,强调为了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关于政权,则要像俄国革命一样,从资本家那里夺取政权,最终由工人、农民掌握政权。引人注目的是,这个纲领强调由产业工会组织总罢工,作为对资本制度斗争的方式发挥重大的作用。并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只要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和反革命势力存在一天,就具有积极意义。
比对《共产党》月刊的发刊词,学者考证发现,这正是中共开始组成时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前言”中一段说明:
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去年(1920年)11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他从英文稿翻译过来……(这个宣言)会提交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
C hang 1921年12月10日
写前言的Chang是谁?从何地得到《中国共产党宣言》英文稿?通过考证,Chang不是别人,正是参加过中共一大会议的张国焘。线索出自“远东人民会议”。从1921年12月这个日期推断,无疑是指1922年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当时刚召开过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代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这样写道:
果真如此,Chang就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人,亦即张国焘。而所谓“此地”即指张国焘等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曾长时间逗留过的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只有这样,张国焘才有可能在“此地”找不到《宣言》的汉语原本,只能根据《宣言》的英文本重新翻译成汉语,而《宣言》的英文本则可能是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保存的。
张国焘可能于1921年底在伊尔库茨克看到过《中国共产党宣言》。这种推断是有根据的,那就是上述在伊尔库茨克的俄语刊物《远东人民》创刊号(1921年5月)上刊登的舒米亚茨基的《共产国际在远东》。在这篇文章里,舒米亚茨基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集结起来。

最后署名的Chang,确系张国焘吗?我伏案读张国焘有关此次俄乡之行的回忆文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其中写道:“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我们到达伊尔库次克之后,方才知道远东局的一些内情。它在这里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屋中办公。由施玛斯基兼任主任,那时的施玛斯基等于是西伯利亚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是俄共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苏俄政府西伯利亚区的全权代表,又是西伯利亚军区的主席。他本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铁路工人,一九〇五年以前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二二年曾出任苏俄驻伊朗的大使。他在伊尔库次克局任内的主任秘书,便是我于一九二一年春在北京会见过的那位威金斯基
 ……那位西伯利亚王施玛斯基,在我到达伊尔库次克约两星期后,才抽出时间约我到他家去吃饭,在座的除了他俩夫妇外,尚有威金斯基。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据威金斯基说,是要和我谈些中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先生实在太忙了,连威金斯基都很难见到他,远东局积下的许多事务也要趁这个机会商谈,所以他和我简单谈了一会,便和威金斯基滔滔不绝的商谈他们的公务。我这个不懂俄语的客人只好静坐一旁。”
……那位西伯利亚王施玛斯基,在我到达伊尔库次克约两星期后,才抽出时间约我到他家去吃饭,在座的除了他俩夫妇外,尚有威金斯基。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据威金斯基说,是要和我谈些中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先生实在太忙了,连威金斯基都很难见到他,远东局积下的许多事务也要趁这个机会商谈,所以他和我简单谈了一会,便和威金斯基滔滔不绝的商谈他们的公务。我这个不懂俄语的客人只好静坐一旁。”
张国焘说他见到的“西伯利亚王施玛斯基”,就是舒米亚茨基,其在1921年5月的《远东人民》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共产国际在远东》中说:“至今,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有了七个地方组织,并在更多的地方产业地区成立支部,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近中国在中央召开了共产主义各组织的协商会议。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工作任务做了这样的规定:‘我们的任务乃是组织和集中群众斗争的力量,使其打击更为有力、强大。这一切都将通过宣传工作,组织工人、农民、士兵、职员、学生,成立具有统一中心的强有力的产业工会,以及创建革命无产阶级的唯一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实现。’”比较舒米亚茨基文中所引的任务,正是《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益雄厚。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
毫无疑义,张国焘所说的“西伯利亚王施玛斯基”载文引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宣言》,当时被带到了伊尔库茨克。张国焘所说的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决定的,是收纳党员之标准,故从未向外发表,但是在陈独秀任主编的《共产党》发刊词中,已经有了展示。
不过那些日子,陈独秀心情变得轻松起来,上海城里的梅雨天过去了,数月阴霾心情被秋风一扫,真可谓否极泰来。自辞去北大文科学长后,陈独秀落寞了许久,坐牢,监视,避险,南下,与教育绝缘,做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这个转身竟然这样的决绝和彻底,在他身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已悄然成军。这年10月,粤桂战争爆发,陈炯明兵分三路攻打盘踞在广东的桂系,月底攻克广州;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做了大元帅,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员,重建军政府。陈炯明于是想到了陈独秀,请他去广东当教育委员长。接到邀请,陈独秀专门写信咨询李大钊的意见,要不要南行广东。李大钊回信说,仲甫兄应该去广州,一则领导广东的教育工作,可将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再则还可以在那里发展共产主义组织。英雄所见略同。陈独秀认同李大钊的看法,深以为是,欣然赴任。行前,他把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书记的职务交给了李汉俊,并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交给李汉俊与陈望道,而《共产党》月刊则交给了李达主办。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写道:
本年,孙中山在广州做大元帅,11月,他
 邀约陈独秀去广州做教育厅长,陈把书记的职务交给了李汉俊担任,《新青年》也交给他和陈望道主编。我负责编《共产党》月刊,这份杂志的稿子主要由《新青年》社供给。12月间,威琴斯基
邀约陈独秀去广州做教育厅长,陈把书记的职务交给了李汉俊担任,《新青年》也交给他和陈望道主编。我负责编《共产党》月刊,这份杂志的稿子主要由《新青年》社供给。12月间,威琴斯基
 回到苏俄去了,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却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不成。
回到苏俄去了,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却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不成。

那一段日子,总是生活艰难。新青年杂志社仍然在渔阳里2号。可维经斯基走后,俄共(布)没有人来接头,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甚至连《新青年》以及出版处的经费都捉襟见肘、无米下锅。有一段时间,《新青年》杂志连编辑的薪水都发不出去,令陈独秀也感到头疼。李达出身湖南永州农耕之家,并非世代官宦或商贾之家,他从私塾到蘋洲书院,直至到国外留学,都是靠自己的禀赋天资与勤奋好学。这时,财路断了,生活都可能成问题了,遑论办刊。对于这段生活,李达这样回忆道:
《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二百元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还有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对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一百元,后来李汉俊未能按月编出,该社即不给编辑费,因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满意,这是他两人之间的冲突的起源,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往后因为经费困难,《共产党》月刊出至第二期就中止了。

日子过得真快,江南的夏天姗姗来迟。1921年6月初,第三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尼可洛夫(尼克尔斯基)来到了上海,找到李达,谈尽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于是李达和李汉俊分别给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写信,让他们派两名代表与会。共产国际给了路费,每个代表一百块大洋。李达让夫人王会悟帮着找开会、住宿的地点,并给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们寄出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