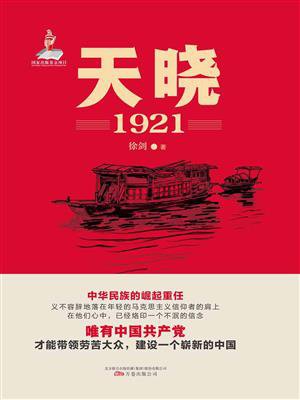1.上海,润之深晤仲甫公
毛泽东已经不是第一次去上海了。
这一次入沪,毛泽东从北京而来。那天,他从北大红楼图书馆走出来,西行,转过故宫东北角楼,沿南河沿大街南行,过南池子,再西拐,往前门火车站而去。这是他又一次入沪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游子送行。
登车时,他想起第一次上海之行,他从一群湖南穷学生住的叫三眼井的地方,去前门火车站,到了售票处,摸了摸腰包,仅够买一张去天津的车票。搭一程算一程吧,天无绝人之路,他是从不信邪的,认定的事情便能做成,相信自己能够抵达上海。
毛泽东抬头看了一眼站台的天空,春天借着天边的鸽哨,掠过北京老城的屋脊。天很蓝,柳条染鹅黄,李花、杏花、西府海棠竞相绽放,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离新民学会第三批赴法勤工俭学人员启程还有二十天,他能赶得上去送行。
一声鸣笛,驶往沪上的列车启动了,缓缓驶出前门站。
毛泽东透过车窗,朝正阳门远远一眺,目光朝着中轴线投去。正南正北,往北是天安门,是端门,是午门,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皇家御花园。彼时,他的目光还没有那么远大,看得不会远及北京城、北方中国乃至整个神州大地,更没有想到二十九年后会在这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只想到离紫禁城东北角楼不远的地方,有一双深情的眼睛目送着自己。
列车朝东南城郭驶出北京,幽燕旷野,小麦正在拔节开花。毛泽东坐在车厢里,春风舞兮,从车窗外吹了进来,铁道旁的村落和杨树急遽向后退却。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去上海,从1918年8月始,他就与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等人推动这件事情,蔡和森甚至找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寻求支持,而他也于这年的8月,约了二十五人一起进京,找湖南在京的杨昌济、熊希龄等名流政要筹集留法经费。第一批和第二批赴法是1919年3月18日,原本他也想去的,可是得知母亲病重,作为家中长子,他不仅辞去了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职务,还最终决定自己不参加赴法勤工俭学。但他还是匆匆赶到上海,为大家送行。第二次上海之行,是去年岁末蔡和森带着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和女友向警予一家赴法。而他此时已被推选“驱张”请愿团团长,虽然未上码头最后作别,只是匆匆一见,足以寄托他对蔡家的殷殷之情。而这一次,老友萧三、熊光楚也要走了,他这次赴沪,一则为会友送别,一则征求上海湘人对“驱张”之后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他还要拜访一个人,即被他视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先生。
那一回青春岁月的旅行,一如他读湖南第一师范时,环洞庭湖步行一样,锤炼体魄,读懂中国农村,而彼时,他用脚步来丈量中国社会与历史。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讲起了这个故事:
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话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祥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呦!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南京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

毛泽东这次到上海,走的时间最长,天津、泰安、曲阜和南京,一路停留,上车下车,整整走了二十五天,他在考察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乡村社会。5月8日抵达上海,次日到码头上送走了萧三、陈赞周诸君,然后住进了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与新民学会张文亮、李思安、周敦祥等人同住一屋,组成自修学社,半工半读。而此行,他要见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陈独秀和孙中山先生。
王会悟说,她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形,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说一口好难懂的湖南话,吃饭叫呷饭,上哪里去叫您到哪点呵,上街叫赶场,从陈先生书房走出来时,高个子,身材修长,一袭蓝布长衫,大襟盘花扣,头发留得长长的,一副特立独行样,一看就与众不同,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很难与那些洋派的日本留学生、北大学生相比,一如他在赴上海之前,于3月14日写给长沙老友周士钊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汲取精华,使它们构成一个明确的概念。”毋庸说,此时年轻的毛泽东的精神世界还处在天人交战的时刻,各种思潮涌来,他还在沉淀、过滤、筛选,直至确定一种学说,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和信仰。而这种思想状态与他1919年12月18日抵京,作为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北京代表团的负责人,有机会接触正在向马克思主义急进的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有极大的关系。在《西行漫记》中,斯诺记录了这样一段毛泽东的谈话:“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毛泽东一点儿也未粉饰自己,他说的是真话。
1919年12月他抵北京时,被称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的李大钊刚在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华丽转身,而陈独秀则还处在从自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途中。彼时,青年毛泽东到了北京,读了大量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
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翻译了大量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部,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在此之前,当李大钊和胡适发生了主义与问题之争时,开始毛泽东并未站在李大钊一边,而是认同胡适“多研究问题”的观点,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并于12月抵京后,专程到胡适府上拜访,争取胡适对湖南“驱张”运动的支持。胡适在1920年1月5日的日记中记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二十九年后,毛泽东已经入中南海,胡适于1951年5月16—17日回忆当时的情景,补记日记:“毛泽东依据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了《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他说,要回长沙去,用‘舟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就回南去了。”
胡适说的毛泽东“回南”,其实就是去了上海。一路行走了二十五天,他在中国历史的莽野上踽踽独行,从岱岳到孔庙,从老子到孔丘,从三国的徐州古城墙到金陵石头城,他要从历史缝隙里寻找一道照亮千年黑暗隧道的光亮,他要伫立于江南石头雉堞之上,来看一个王朝一个国家百年、千年不衰不败的真理,他要解满腹的疑惑和怅然。他在上海住了两个多月,当年与毛泽东住一个屋的李思安回忆道:
在那里,我们住了两个多月,生活很艰难,每人每月三元多钱生活费,大家轮流做饭,蚕豆上市,我们就买蚕豆,掺和一些米煮着吃,大家还是怡然自乐,甘之若饴。
然而,就在这个历史时空的交替点上,毛泽东在渔阳里2号,与仲甫公深晤,这是一次跨越年龄、时空和心理距离的相遇。
那个上海仲夏之夜,陈独秀究竟给毛泽东讲了些什么,以至十六年后,在延安窑洞里昏黄的灯下,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聊天,忆起这一段陈年旧事,仍不乏激动:“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的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
 “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陈独秀与毛泽东,年龄相差十四岁。一个是日本留学生,一个是湖南师范生。当年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当图书馆助理员时,一个月八块大洋,而陈独秀是三百元,是当时众星捧月的人物,一位小小图书馆助理员对于他只有仰望,读他主编的《新青年》,他掀起狂飙般的新文化运动,听他那激荡人心的演讲,在毛泽东心中激荡起来的何止是“湘江北去”“浪遏飞舟”,何止是沧浪入夔门、瞿塘,出巫峡,出西陵,入城陵矶的乱石穿空,卷起千堆雪。可是当时他够不着他,润之与仲甫,韶山与独秀山,仅两山之间的简单的交谈,一种远距离的眺望,一个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对学科长的高山仰止。仲甫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的位置,在陈独秀入狱后,从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创刊号《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思想界巨星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崇敬。陈独秀当时坐牢,或许看不到毛泽东的文章,但在他出狱之后,就能看到一个从湖南乡村走出来,与他一样特立独行的毛泽东,是如何对他推崇备至,甚至喊出来:“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板荡识忠臣,患难见人心。可以确切地说,入狱时的陈独秀还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那八十多天的牢狱之灾,以及出狱后屡受监视,使他的人生信仰发生了一场救赎、嬗变与重生,他对西方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幻想破灭了,转而追求空想社会主义。1920年1月来到上海后,他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的书,尤其与俄乡密使维经斯基多次交谈,随着大量的西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翻译过来,陈独秀已经完成从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涅槃。而就在这个历史时空中,毛泽东与陈独秀在上海相遇了。看来,那一个个仲夏之夜的长谈,陈独秀的新信仰,对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正苦苦思索而处于彷徨之中的毛泽东来说,或许起到了“醍醐灌顶”“穿云带雨”的作用。
改变毛泽东信仰的是三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他对斯诺说:“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年7月,毛泽东要从上海回长沙了。临行前,他最后一次见陈独秀,只提了一个要求,请陈独秀以后多给寄一些书和杂志去,他要在长沙建一个专卖革命书刊的文化书社。
好呀,润之!陈独秀拍手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