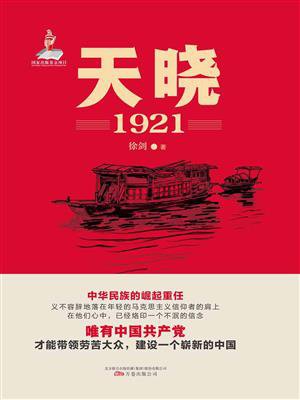3.又见红楼灯亮
那个夏天,张国焘在上海住的时间最久,将近四十天。自从在北京与李大钊先生一别后,他便坐车南下,7月15日抵浦口,过江,心随沧浪之水而动,涌起一股游历的雅兴。船靠岸后,他遂登石头城,极目扬子江,领略六朝古都的虎踞龙盘,又游天王府,为太平天国掬一把金陵残泪。随后第二天便入沪,拜会陈独秀先生。
有学生自北京来,且又是追随李大钊左右的弟子张国焘,陈独秀不亦乐乎。他问张国焘下榻何处,张国焘说还没有找旅馆呢。陈独秀说就住渔阳里2号吧,楼下有三间房,还有一间客房空着。“陈独秀热诚地要我搬到家里来住,以便从长计议”。
霞飞路渔阳里2号是原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宅,当年陈独秀曾在他的麾下当过秘书长(亦有书称为秘书科长),私谊甚厚。1920年1月,陈独秀从北京迁居上海后,便与夫人高君曼一起住在这里。张国焘回忆了陈家当时的住宿情形:楼上有三间屋子,陈独秀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王会悟。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李达住,还有一间张国焘住。
话及王会悟与李达,有一位从湖南省来的党史工作者问王会悟,中共一大会议召开之前,您见过张国焘吗?
也是这样的夏天,只是地点不在梅雨时节的江南,而是仲夏之时的北京,历史很久远了,爱穿大襟盘花扣阴丹棉布上衣的王会悟奶奶,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了,但对青春年华时所经历的往事仍历历在目。她呢喃道,见过呀,那是一个夏天,张国焘在渔阳里2号住了一个多月,与李达同住在楼下的客房里。他应该只比我大一岁,个子高高的,宽脸庞,浓眉大眼。人家是北大高才生,有骄傲的资本,恃才傲物,给人感觉是,一般人他都不太爱搭理。
非也!张国焘说他下榻陈家的最初几天,几乎都是早出晚归,在外面奔忙,先是辞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的职务,随后与黄介民等旧友推杯换盏,酬酢频频,每天见不到踪影,以致陈独秀都有点儿不耐烦了。陈夫人高君曼甚至讥讽他交游甚广,是不是在找女朋友。张国焘哈哈一笑,也未做更多的解释。
终于闲适下来了。
他知道陈独秀的作息时间,晚上和早晨读书写文章,下午见客,高谈阔论,他觉得自己很幸运,继追随李大钊之后,又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后来在香港,面对美国堪萨斯大学口述历史著述学者,他这样描述胡适的安徽老乡陈独秀:“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便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张国焘有幸,与另一位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历史人物毛泽东一样,在青年时代,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两位时代巨子指点迷津般的启迪。两位导师,在北京、上海的时空中,同一座红楼和江南阁楼,时间却是1920年春和夏,一个在前,一个于后,对他俩进行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选择怎样的政党与道路的对话。只是后者修成了正果,而前者则选择荒芜末路,此为后话。
可是那些日子,堪萨斯大学的学者一如当年唐德刚追问胡适一样,追问陈独秀对张国焘谈了什么。
建立共产党。时隔四十多年了,张国焘对陈独秀当年说的话仍旧清晰如昨,他历数了五条:第一,社会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的自我解放,以中国的实际而论,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第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彻底,无政府主义过于空想,议会政策又不能实行,在可以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从事新文化运动。第四,不要顾虑共产主义曲高和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最终目标。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激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残酷镇压。现在我们组建共产党,无非十大罪状再加一条“共产共妻”。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一般工人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益有增加,如果聚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他们甚至还谈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政纲。陈独秀要张国焘将这些话带回北京,告诉守常先生,上海已于8月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希望北京尽快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
张国焘是8月下旬从上海返京的,他立刻赶到了红楼一层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将自己与陈独秀的上海谈话告诉了他。李大钊听过后,略经考虑,便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说目前的问题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他说仲甫在上海,对南方的情况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判断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行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大钊深信,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理论还是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陈独秀讲的那些要点都切实可行。
那么,先生,请根据您的意思回陈先生一封信吧!张国焘请求道。好啊!是该写信与仲甫兄遥相呼应啦,上次他从上海来信,问上海成立党的组织,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我回信,当然要叫共产党了。
那天晚上,北京一进入9月,夜晚便渐见凉意了,李大钊回到家中,匆匆吃过晚饭便入书房,推开窗子,燕山的夜风潜入书斋,已将白日里炎热的秋老虎驱走。
李大钊在书案前落座,边研墨,边抬头仰看北方的秋空,要给仲甫写一封信,告诉他北方与南方相呼应,早已经展开建党工作。其实未见维经斯基之前,李大钊就于年初号召北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北京《晨报》报道说,“回来后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同年5月1日,李大钊与陈独秀真是心神感应,他同样出席了有五百多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称赞苏维埃取得的成就,宣传八小时工作制。何孟雄等走上街头,呼响“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8月16日,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及天津的觉悟社成员共二十一人聚集于北京陶然亭,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张申府发言,促成进步团体的联合。李大钊说各团体要有正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于齐一,对外尤不足以与其他组织联合,李、周第一次携手,决定五个团体合成“改造联盟”,通过了联盟宣言和约章,这都为成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张国焘再来红楼时,李大钊先生的信已经写好了,情词恳切而准确。他们共同签上名后,便寄了出去,这也许是后人说的“相约建党”的第一份重要文献。后来李、陈之间通了许多信,都是有关建党的事情。
然而,关于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三位参与者是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申府和去了香港的张国焘谈及这段往事,却各有版本。
张申府说:“1920年9月十几号,罗素来中国讲学,我去接罗素,到了上海。我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我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大钊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到了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注过。她不干,没有发展。不久张国焘回到北京。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也很活跃,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

而张国焘的说法却与张申府的大相径庭:“我们没有耽搁时间,立即开始活动,首先我们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是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他在一两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留学。我们这三个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留学生中展开活动。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因此消失了。”
“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参加者时,标准不免过严。我的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两位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们欣然参加。李大钊先生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接洽,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五人也应允加入。”
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情况,还有一个权威的资料,那就是1956—1957年由当时的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一部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集,对于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有最可靠的详尽材料。这份报告是出席会议的北京代表(据认为是张国焘)执笔的。对于北京党组织的成立过程,报告这样写道:
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在去年(1920年)10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比较顺利了。
中共驻共产国际报告中提到的几个假共产主义者,一如张国焘的回忆所说,是李大钊先生接洽的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五人,都是当时北大的学生,却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当时北大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抵制,他们还定期出版《民声周刊》,发行一种小册子,对俄国革命一直表示同情,常发表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组成中国共产党的论调,引起了李大钊的注意。然而,他们与共产主义者有一个根本分歧,就是赞成无产阶级革命,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觉得革命尚未成功,离专政还远,便不计分歧,吸收黄凌霜等人携手并进。
那天下午,一群白鸽掠过北大红楼图书馆屋顶,盘旋于苍穹,由一只领头的信鸽引领,发出尖啸般的鸽哨,在湛蓝的天幕留下一道道弓背般的弧线。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一层东南角一隅的李大钊办公室,党的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起初为三人,即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不久,又吸引了一批新成员,他们是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九人。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到任何组织,所以会议未设主席,也没有记录,先由李大钊说明了发起的意义,接着张国焘介绍了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运行的情况。与会者一致表示组党,但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坚持,便不设书记。李大钊负责联络,张国焘负责职工运动的发动,黄凌霜、陈德荣创办《劳动者》周刊,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可是到了11月,北京的党组织发生了意见分歧,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陈德荣等人向李大钊发难,主张自由联合,不赞成党内所谓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反对党的纪律,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进行一致性的宣传。然而经过一番讨论,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固执己见,连一向春风大雅的李大钊也为之头疼,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
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有九人说,还有十人至十五人之说,但俄国人纳乌莫夫根据口头调查于1927年写就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有如下记录:
组织中八位同志,有六名无政府主义者,两位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黄凌霜为首,两位共产主义者是李大钊和张国焘……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不久脱离了北京的组织,但是因为有(一)邓中夏、(二)罗章龙、(三)刘仁静、(四)名字不详等四人的加入反而得到了加强。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肯定了这样的叙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自一开始参加的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后来又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人的加盟,而形成共产主义派的主导了。到了1920年底,这支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已经卓然成军。
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展了一些成员。到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或许,这样的叙事就是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