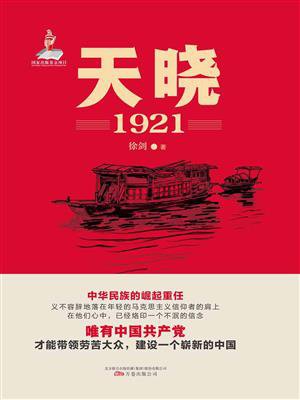路标
韶山,独秀山,十天走过百年
也许是一种巧合吧。
《天晓——1921》最后一程采访,零公里从韶山始,终点是安庆市独秀山。毛泽东—陈独秀,润之公—仲甫公,命运之轮已转过百年,历史路标却指向了从前。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风雨雨,已发展成为一个百年大党。五十多人的党员队伍,如今核裂变般地壮大,发展到九千万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红色军团。随着百岁华诞一天天临近,仿佛是一种巧合,引领我最后一程的采访,竟然是从韶山走向独秀山。
那天,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委员会发来消息,告知七十周年国庆大阅兵后,将在韶山开展中国作家“回到人民中间”活动,询问我能否参加。我没有半点儿犹豫,欣然接受。此行正好与我担纲建党一百周年写作机缘巧合,何乐而不为呢?回首建党大业,怎么能避开真正的主角毛泽东?他老人家的身影覆盖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从少年时起,就对伟大领袖的故事耳熟能详,潜入血脉,而今甚至不用采访也能写上几万字。且还有另外三位一大代表也是湖南人,他们是李达、何叔衡和周佛海。我曾于9月下旬去过李达老家永州,独剩何、周故里,于是决定去湖南韶山干部学院,正好可以再当一回学员,再洗一次心,从韶山冲的视角,领悟毛泽东与中国,一代伟人与一头睡狮的百年传奇。
之前,已经有半年时间了,我从北至南,追寻十三位中共一大参加者的生命遗痕,拜谒故居,走访党史专家,请教对敏感人物的臧否。没承想,最后采访行程居然是从毛泽东故居到陈独秀老家,也是十天,且并非刻意安排,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安排吧。
10月20日中午,我踏上驶往长沙的高铁。抵时,已是夜深,过湘江大桥,从橘子洲头侧身而过,转到岳麓山,仿佛就为寻毛泽东之魂而来。彼时,天仍阴着,潇湘之水绕岳麓,为谁空流到洞庭?雨夜中,青年毛泽东的头像与岸上的霓虹灯光相映生辉,给人以无尽的想象。接站司机说,连着下了一周的秋雨,今天雨小了,天要晴了。住进韶山建国酒店,已是夤夜时分。当晚,一改在京城的失眠苦楚,临江而眠,一夜无梦,醒时已是大天光。伫立于十八楼落地窗前,俯瞰秋山,韶峰兀自而雄,天幕蓝得炫目,田野城郭无云,韶山清晰可见,虽说不上巍峨,却一览岳麓山之小。彼时,太阳从韶峰冉冉而起,朝霞犹如神火点燃,光焰万丈,拂照三湘。转瞬之间,记忆被唤醒。
其实,韶山于我,于我们这代人,一点儿都不陌生。韶山、井冈山、延安等红色地标,成了一代代中国人向往的地方。人间正道是沧桑,百年中国,多少学子奔走于韶山道上。我也几度融入这股激流中,四十多年间,曾三度来韶山。
第一次是十七岁,那时,我就在离此不远的湘西一隅当兵。青春有幸,被送至省城湖南日报社学习。那个冬天,战友来长沙买照相器材,约我同游韶山。一百多公里旅程,有长沙—韶山直达列车往返。长沙站修得很气派,为当年中国之最;韶山站也毫不逊色,湘人皆以此为傲,我们以去圣地为荣。彼时,已入湖南最寒冷的季节,霜色秋山枯,芦荻雪白,山瘦水寒,投目处,尽是冰雨冻三湘。可我们的血是热的,眼睛噙着山野的剔透,脸庞溢着内心的崇敬。拜谒毛泽东故居,天冷,我们二人都穿着军大衣。那时,仿佛从青春中国迤逦而来,伫立于毛泽东故居前的荷塘边上,拍一张合影,芳华从此被毛家祖屋后的韶峰烙印了,再也走不出他老人家的影子。他伟岸的身躯,不仅覆盖了一个时代,也将几代人覆盖于他的光影中,至今不曾消散。
第二次再去,人已到壮年。2009年“十一”长假,我和爱人带女儿去韶山。那是一个稻菽飘香的仲秋,一家人从北京而来,登岳麓,谒韶山,先拜毛泽东铜像,再游故居,后参观纪念馆,午餐就安排在老人家当年下榻的韶山宾馆。我得到了一尊毛泽东铜像,正是如今万众景仰的“人民代表”,出自刘开渠先生之手。我们请于车中,之后的日子,从韶山去怀化,入凤凰古城,再走“黎从榕”,即黎平、从江、榕江,游于贵州之境,辗转于毛泽东当年通道转兵后,用兵如神之地。循着老人家的生命足迹而去,山重水复间,仿佛有一个强大的气场吸引着我们。山风拂过,向东、向南,再掉转车头,北上,西行,至遵义,至贵阳,至黄果树瀑布。那时,夜郎国远非今日可比,山道逶迤,乌江腾细浪,车行贵州屋脊,乌蒙磅礴,荒村野店,几十里无人家。时有夜雨淅沥,山高坡陡路滑,问道不见村舍人影。我们就一条路走到黑,一路向前,向前。
第三次就是这一回了。十年后徐郎再来,已是鬓发染霜。次日上午10点,随中国作家“回到人民中间”活动团向毛泽东铜像敬献花篮。环顾四周,参观者皆抬着花篮,向铜像敬献。人流一拨又一拨,人头攒动,一条大河波浪宽,拥簇在我们的身前身后。我们站成分列式,迂曲向前,人群走得很慢。仰首望韶峰,天幕海水蓝,不见一丝云彩。极目远天,一轮下弦月镶在天穹,月影淡白,犹如一艘白帆船,出湘江,远帆洞庭。那一年是毛主席百岁诞辰,在韶山广场安放毛泽东铜像。12月的湖南,终日阴雨连绵,可是12月26日那天,当毛泽东铜像从江南运抵时,韶山天蓝,百里无云,也是今天这样日月同辉。本来该在3月天开的杜鹃花,一夜之间灿然怒放,成了一道风景,一个传奇。
这样的季节,湖南天空日月同辉本常有之事,不足为奇。等了一个小时,拜过毛泽东铜像,举手宣誓,重温入党誓词,一种久违的感觉,仿佛回到从前,再次被一片光华所覆盖。穿过广场上的人群,朝毛泽东故居走去。毛家祖屋背靠韶峰,坐北朝南。毛泽东故居经修葺后,百年老屋,古拙奇雄。毛家当年,算得上韶山冲的殷实人家,有房产、田地。游于毛家老屋前,感受愈深:曾欲做教书先生的毛泽东并不奢望跻身精英阶层,与那个军阀坐江山的体制苟合。他要寻找一种生活,一个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理想国。于是,他投身大革命洪流,发动秋收起义,与一大批湖南革命者一起前仆后继,奋斗不止。
“芙蓉国里尽朝晖”,想着毛泽东这句家喻户晓的诗,我的激情燃至沸点,身子里外,都变成大江大海,心逐渐平静下来了,在毛家荷塘前再拍一张照片留存。
因《天晓——1921》采访,再入一代伟人的诞生地。毋庸说,历史是芸芸众生创造的,可在某个关键时刻,撬动地球的,改变中国命运的,往往是几位超凡人物。他们有经历、眼光、胆识、胸怀与意志,登高一呼,万人响应。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伟人。韶山纪念馆的红色文物大都是毛泽东1949年入北平、住中南海后的生活用品,原封不动搬回韶山,仿佛还遗留着他的体温与情感。那件七十三个补丁的睡衣,卫士先试穿的棕色皮鞋,都让伟人不再遥远,有了温度,有了烟火气,成了一个普通人,一个恋旧、重情义、不忘老友的长者。那一刻,我对这位至尊长者有了新的发现与认识。
第二天天气骤变。三湘的晚秋悄然而至,冷雨不绝于天,哗啦啦下个不停。我沿着湖湘三位中共一大出席者的生命遗痕,去宁乡,入何叔衡故里,再转道怀化,沿沅水而下,至秦置黔中郡——沅陵,访问一位令沅陵父老乡亲不愿提起的人的家乡。
天一直在下雨。在湖南境内,遇潇湘夜雨。从怀化坐高铁到了山城,又是一幕连一幕的巴山冷雨。那天晚上,我抵重庆北站,因天降暴雨,道路塞车,出不了高铁站,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到酒店时,夜已经深了。站在窗前,潇潇秋雨倾盆而下,随江流而去,从湘江,到沅水,再到嘉陵江,落花流水秋意寒,冷溪寒流从不同的孔道、支流汇入长江,然后出三峡,过洞庭,流经陈独秀老家安庆。沿着这条大江,流到长江入海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一条江与一个政党,一条江与毛泽东、陈独秀,从韶山到独秀山,从湘江到长江,从嘉陵江到长江口,大江东去,流淌了千年万载。逝者如斯夫,建党伟业,只是这条大江流入大海时的一个峰谷与旋涡,却又是这个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伟大江流。而我的采访,鬼使神差,最后的行程居然是沿江而下,从陈独秀最后岁月的寓居地江津——他人生的黯然时刻所在地,直抵他的出生地。
那天的秋雨特别大,天泪滂沱。我站在江津陈独秀旧居陈列馆门前,似乎看到陈独秀与夫人在江津延年医院门前,带了不少行李,被女主人拒之门外,尊严尽失。这样一位骄傲的人,一位痛失两位爱子陈延年、陈乔年的父亲,蛰居江津四载,靠别人接济度日。一度为人写故人传记赚几个看病钱,直到风雨飘摇走向死亡,也走向他的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英雄天地,沧浪之水,一代英雄之泪之血,流淌成一条母亲河。长江东流水,涌向大海,引发一场五千年的历史大变局。我顺江而下,走向这条母亲河的入海口,走向一个百年政党建党大业的零公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循着一条时光的巨流河,走向了一个执政党的初心……
江雨渐次小了。乌云满天,唯有一罅天光,从天穹里射下。我站在安庆独秀园前,看过浮雕,向牌坊走去。
正准备拍照,忽见三个少年从牌坊下走过,你推我,我搡你,闹着,喊着,追逐着。我远远望着,感叹道,少年中国,中国少年,那三个少年仿佛是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年少时的身影,他们聚集着、呼喊着、推搡着,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分别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带着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一条复兴之路。
幸哉,中国!悲哉,独秀!终于抵达他的汉白玉大圆冢前,我躬身行礼,然后顺时针绕坟三圈,再站到他的墓前,默默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