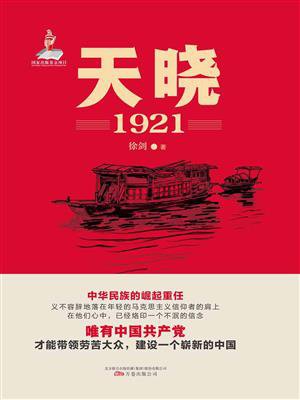1.晨曲 俄乡密使
1990年,王会悟已是九十二岁高龄的老奶奶了。她感到自己真的老了,不仅耳背,眼睛也不好使了。当年金丝边眼镜后面的美眸已经失去光泽,晶体浑浊了,眼前总飘着一层云翳,观物愈发模糊了,得戴一副高度的老花镜才勉强看得清,有时还会认错人。孙辈偶然来家里,总爱驻足于那一幅年轻的美人照前,感慨万千,说会悟奶奶当年绾一个发髻,着一件七分袖旗袍,再戴上金丝边眼镜,就是一位江南淑女呀!2019年初夏,我站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老照片前,注视着这双眼睛,它属于那个远去的年代,明眸如月,秋水一样明净,却飞扬着无限的激情。笑起来,可挽东风一片,眼里溢满了水,能装满嘉兴的两个月湖。
老啦!王会悟摇头,吴语呢喃。孔夫子说,老而不死是为……如今我成了儿孙的拖累呢。哈哈!晚辈们笑了,奶奶说什么呀,您一辈子积德,才会如此高寿啊。王会悟摇头,活那么久做啥呀,自己受罪,还欠别人。好在,我已走在向马克思报到的路上,快到八宝山门前啦。
“人间正道是沧桑。”王会悟常念叨老友毛泽东的那句诗,来路匆匆,去路苍茫,一条人间正道,中国的仁人志士探索了多少年?她就要到百岁了,历史长河,百年不过一瞬。往事如烟云。王会悟率性乐观,不愿纠结旧事、旧人。然,快到建党七十年了,总有报纸、电视以及研究党史的人来访,因她参与过中共一大会议筹备,是唯一健在的亲历者。她摇头,历史早摆在那里了,人老了,爱说车轱辘话,尤其是一个人经历了九十多载时光,繁华如梦、如电、如幻。风雪、风雨过后,早已经换了人间,白发、夕阳、青山,她觉得自己就像一架老唱机,回忆的唱针一放,嵌入一圈又一圈的轨道,最后的落点仍旧是中共一大召开前后那十天,似乎她的光荣与梦想、幸福与缺憾,都浓缩在那十天之间。因此,那些过去的日子,掠过她脑际,从已经不太关风的唇齿间流溢出来的,仍旧是陈独秀、李汉俊、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名字,她只讳谈一个人。
可是,总有年轻记者,会在无意之间碰触到她早已结痂的伤疤。一天,一位记者在访问中突然问道:你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住的时候,见过俄国人维经斯基吗?
维经斯基?王会悟犹豫了一下。历史太久远了,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她一时想不起来,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模样。
年轻的记者将《李达自传》翻了一下,捧着书,凑上前去,说,在《李达自传》里有这个外国人的名字,叫“Voitisky”。王会悟一眼就看到李达的名字,心里咯噔了一下,虽然隔着近百年,隔着一条天河,但是1920年夏天初见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
会悟奶奶!年轻人重复地问了一句,你见过维经斯基吧,他的中文名叫吴廷康。你说吴廷康啊,岂止是见过,我还在他们办的学校念过俄语呢,教员就是维经斯基漂亮的太太库兹涅佐娃,还有杨明斋,后来去莫斯科的少奇同志、任弼时同志、李立三同志,都在他们办的外语学校补习过俄语。
……
一口桐乡话,吴语呢喃。那天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入夏后淅淅沥沥的梅雨,最终化作暴雨倾盆。电视屏上,反复在播一头银发、戴着高度老花镜的王会悟讲着上海贝勒路(今黄陂路)、望志路(今兴业路)交叉口树德里石库门里的那场群英会,还有嘉兴鸳湖旅馆及红船里的故事。她身着一件阴丹士林蓝对襟外衣,神情沧桑,让我灵光遽然一闪,《天晓——1921》的讲述者找到了。这个讲中国故事的老人,非王会悟莫属。
说说万里俄乡来客吧。
那天,王会悟讲起维经斯基的最初来路。
1920年维经斯基出发时,海参崴
 仍旧蛰伏在漫长的冬天里,海山天地白,积雪掩埋了白桦树落叶,褪尽盛装的亭亭白桦,像藏在雪国中的女神,裸着臂膀,将手指伸向了天空,在湛蓝色的天幕上留下一道道抓痕。夕阳一照,仿佛整个苍穹都在流血。
仍旧蛰伏在漫长的冬天里,海山天地白,积雪掩埋了白桦树落叶,褪尽盛装的亭亭白桦,像藏在雪国中的女神,裸着臂膀,将手指伸向了天空,在湛蓝色的天幕上留下一道道抓痕。夕阳一照,仿佛整个苍穹都在流血。
海参崴城通往港口的路上积雪被雪橇碾轧过后,化作一道道坚硬的冰辙,阳光洒下来,红红的,闪闪发光,犹如大地上的一条条脉管,青筋毕露,通向海参崴港,通向远东,也通向世界。
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坐在爬犁上,那年,他刚刚二十七岁。爬犁后边,坐着他的娇妻库兹涅佐娃,还有几个旅行箱。再往后的两架爬犁上,有他的助手季托夫及夫人,还有谢列勃里亚科夫和朝鲜社会活动家金万谦。此行,维经斯基还带上了一个华裔老布尔什维克杨明斋做翻译。
马蹄踩在冰雪上,沙沙声,轧轧声,旋律四起。积雪厚度不同,奏出来的音调亦不同。马蹄声咽,前路茫茫,将要踏上一个古老的国度,会像现在的雪地爬犁一样顺畅无阻吗?维经斯基耳边还回响着俄共(布)远东州委海参崴分局
 的松木屋里,俄共中央政治局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对他的最后交代:格里戈里同志,派您去中国,以远东共和国达尔塔通讯社记者身份做掩护,在那里长住一段日子,把组织搞起来。这几年,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还有俄共远东州委多头并进,对中国、朝鲜甚至日本等远东地区做工作,派往中国的同志有两三拨了,包括布尔特曼、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等人,可他们接触的多是一些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布尔特曼回来说见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邓中夏。
的松木屋里,俄共中央政治局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对他的最后交代:格里戈里同志,派您去中国,以远东共和国达尔塔通讯社记者身份做掩护,在那里长住一段日子,把组织搞起来。这几年,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还有俄共远东州委多头并进,对中国、朝鲜甚至日本等远东地区做工作,派往中国的同志有两三拨了,包括布尔特曼、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等人,可他们接触的多是一些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布尔特曼回来说见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邓中夏。
 波塔波夫倒是见过陈炯明,对他评价很高,说他是中国有名的“社会主义将军”,真的言如其人吗?我有些怀疑。还将中国陈独秀写给列宁的信转到莫斯科,情报未必摸得准啊。俄西伯利亚、俄共远东州委、远东共和国、伊尔库茨克东方民族处,甚至还有共产国际都在向中国派人,各个系统杂乱无序,组织上很混乱。派您到中国,就是因为您有国际视野,在美国待过,应变能力强,您的任务就是调查中国、朝鲜和日本的社会运动,尽可能物色社会主义者,若有可能,帮助他们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波塔波夫倒是见过陈炯明,对他评价很高,说他是中国有名的“社会主义将军”,真的言如其人吗?我有些怀疑。还将中国陈独秀写给列宁的信转到莫斯科,情报未必摸得准啊。俄西伯利亚、俄共远东州委、远东共和国、伊尔库茨克东方民族处,甚至还有共产国际都在向中国派人,各个系统杂乱无序,组织上很混乱。派您到中国,就是因为您有国际视野,在美国待过,应变能力强,您的任务就是调查中国、朝鲜和日本的社会运动,尽可能物色社会主义者,若有可能,帮助他们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明白!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同志。维经斯基的眼里充满了对他的敬重。
爬犁在空旷的雪野上划下两道深深的辙痕。极目远眺,这些辙痕也有维连斯基同志留下的吧?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知道,内战之前,维连斯基曾在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活动,白军叛乱后,硝烟弥漫,战争烽火四起,他从远东避乱回到莫斯科,目睹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国代表身份之争。后来,俄共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大会在鄂木斯克秘密召开,为摆脱“1919年苏俄与外部世界完全孤立”的境地,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们将视线越过乌拉尔山,投向远东。基于此,维连斯基于8月上书俄共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有关在东亚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获俄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并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离开莫斯科赴任。交给他经营远东的使命:一是鉴于中、美、日三国利益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加剧这种冲突;二是唤起中国和朝鲜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三是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与中国、朝鲜和日本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四是积极帮助中国和朝鲜建立游击组织。
 彼时,中亚铁路因为内战中断,维连斯基一路辗转,在俄罗斯大地上颠簸了二十多天才进入西伯利亚,在那里活动,一直滞留到了年底。1920年元旦过后,白军被打败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他于2月14日进入伊尔库茨克,随后再赴海参崴,统领对远东的红色渗透。
彼时,中亚铁路因为内战中断,维连斯基一路辗转,在俄罗斯大地上颠簸了二十多天才进入西伯利亚,在那里活动,一直滞留到了年底。1920年元旦过后,白军被打败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他于2月14日进入伊尔库茨克,随后再赴海参崴,统领对远东的红色渗透。
冷山苍苍,谁主远东沉浮?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很清楚,他是由俄共远东州委海参崴分局派遣的,今后关于中国的报告必须投向那里。可是这一切都瞒不了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同志,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总指挥。那一年,维经斯基二十七岁,已经加入布尔什维克两年了。维连斯基派遣他入中国,或许正是看中他游历北美的经历。说起来,一位底层的布尔什维克能够闯荡世界,在当时并不多见。1893年,维经斯基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十四岁初中毕业后,他就踏入真正的社会大学,当过印刷所排字工人、事务会计。二十岁闯入北美。两年后,加入美国社会党,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来辗转美国、加拿大,生活了五载。1918年春天,维经斯基站在甲板上,朝着故国的海域眺望,大轮船将从中国黄海驶向海参崴,这是他当年从青岛上船,闯西伯利亚走过的一条海路。
时隔百年,我也在悄然叩问、追寻俄乡万里来客们入中国的路线。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一行会走陆路吗?从绥芬河入关,然后从哈尔滨直到北京?抑或走水道,坐船环中国黄海、渤海湾,从天津港登陆?翻阅多部有关中共一大俄乡密使的书,皆无答案。那天晚上,我伏案夜读日本著名中共党史研究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看到《魏金斯基
 的活动》这一节时,眼前遽然一亮:
的活动》这一节时,眼前遽然一亮:
《报告》只说他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派往“中国上海”,没有提到所取的路线——尽管从当时的交通情况判断,一般应该走海路。他们可能先到天津、北京,然后又去了上海,也可能径直去了上海。不过,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信里写到经由北京收到了电报,还报告了天津的联络地址;所以,先到北京的可能性要大些。当时接触过魏金斯基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也说,他先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然后按李大钊的意见去了上海。

我读过的《李达自传》和张国焘《我的回忆》以及《包惠僧回忆录》,三人皆持同一种说法,维经斯基入中国后,先见李大钊,再持信赴上海会陈独秀。显然,石川祯浩的推论更接近史实,维经斯基到中国走的是海路,环太平洋沿岸航行,从天津上岸,第一站是北京。因他与中文翻译杨明斋当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两眼一抹黑,必须找中间的牵线搭桥人,这个人就是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同时兼任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员的中国通鲍立维,以及北京大学法语、俄语教授伊万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