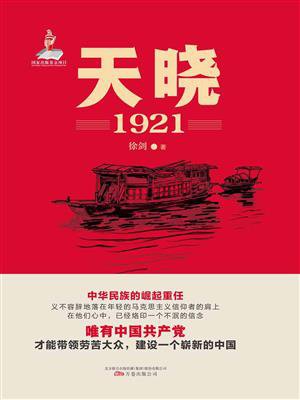2.先见李大钊,再会陈独秀
那天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凭第一直觉,我立即将王会悟定为《天晓——1921》的讲述者。中秋节后,到永州李达故里采访,得到一本纪念李达百年的党史论文集《怀念李达》。夜不能寐,听着湘水和潇水的拍岸声,读到子夜。翻到《李达自传》篇,言简意赅,一种哲学家的冷峻,将情感包裹得严严实实。然,水行至深处,读文进入广阔之域,我的心情却随窗外渐次寒凉的秋水,落到了冰点。李达在自传中透露了三个信息:1920年春季,维经斯基来到了中国,第一站到北京,见到了李大钊。是年夏天,李达由日本归国,到上海拜访陈独秀。次年4月,他与王会悟相爱共同生活,未办婚礼,引来非议如潮。
掩卷已是五更寒。我朝天一叹,李达与维经斯基失之交臂,王会悟恐怕也未见过吴廷康
 。
。
之后的日子,我翻遍两大摞堆成山头的党史书籍,终未发现王会悟与维经斯基交集的痕迹。这意味着,我设想的讲故事人不能贯穿始终,一条草蛇灰线难成。王会悟见过俄乡密使吗?我一次次叩问天穹,考问自己。
剪不断,理还乱,茫然的心绪无法切入写作,《天晓——1921》落笔一拖再拖,怅然至极。
那天傍晚,倚窗冥想,节令恰好是小雪,北京初雪如期而至。俯仰之间,我发现天空酷似老家篾匠编织的簸箕。上天之手轻轻一旋,筛下一粒粒米雪、片雪,落在北方城郭之间,天地一抹白。但在我看来,冬雪更像是精灵,纷纷扬扬,犹如暮色苍茫中扑向大地的一只只飞蛾,一如当年那群革命者,飞蛾扑火般扑向铁壁、铁窗与死亡,撞向坚硬大地,切切嘈嘈之后,喧嚣遽静,一切都归于寂灭。那天,我在寂然中,心头浮起了瞿秋白《集句》中的两句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转身,疾步奔上三楼,从书架上抽出青春年少时偶得的一部张国焘的回忆录,我从湘西带至武汉读军校,毕业时再由武汉带回湘西,最后从湘西带入北京,漂泊南北中国,四十年一路走来,扔掉了许多书,却从未想摈弃这部书。
那个雪落黄昏,一壶浊酒,两只醉蟹,边饮边读,一个人喝至微醺,夜色如潮水般将我湮没,却没有湮没历史。我在浩瀚的史书中发现了光亮,似乎有一种夜幕退尽的豁然。眼前,永定河孔雀城华灯怒放。张国焘提到,1920年7月15日,他婉谢李大钊让他同行去乐亭乡下避一避风头之邀,去了南京。他说:“我在天津住了一夜,次日搭津浦车南下,十五日到达龙蟠虎踞的六朝故都——南京。那时暑假已经开始,又受战争影响,南京各学校的朋友们多数均已离去;加之那时南京城内商业萧条,民气低沉;这些都不免使我有寂寞凄怆之感……不久我到达上海……立即去访问那时迁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他问我此次南来,是否有学生代表的任务。我加以否认,并告诉他在离北京前与李大钊先生谈话的经过。他热诚地要我搬到他家里住,以便从长计议。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女青年王会悟。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我虽抱有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向和热情,但还只是一种空洞的想法,是偏于兴趣方面的,还没有以这一运动为终身事业的坚决打算。因此我住在陈家的最初几天,主要仍是在外面奔忙。”
王会悟,李达!1920年这个夏天,渔阳里2号。我一跃而起,高喊了一句:乌拉!
王会悟又进入了叙事场。她说,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从北京来到了上海,见到陈独秀后,谈到他的中国之旅。他是从中国天津港下船的,码头上乱哄哄的,无车可坐,翻译杨明斋晓得中国城市出行方式——人力黄包车,便招了招手,叫来几辆,让维经斯基夫妇先坐上,两个人坐一辆,行李箱就放在脚下。然后,他操一口胶东话,喊道,去北洋大学。
维经斯基踏上中华大地,纵有杨明斋带路,可是对中国革命运动仍然两眼一抹黑,举目皆是陌生面孔。遂按原定计划去见那个叫鲍立维的俄侨。他在中国深耕多年,从哈尔滨到天津,再到北京,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甫一见面,维经斯基说,鲍同志,我要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领袖?鲍立维沉吟片刻,说只有陈独秀先生与李大钊先生了,他们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
南方有谁,北方又有谁?维经斯基追问。
鲍立维说的,与参加过共产国际一大、二大,甚至为争名额大打出手的江亢虎之辈毫不相同。他开列了一份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第一个当数陈独秀,再一个就是李大钊,可以说,他们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天空里的双子星。鲍立维递给维经斯基这份名单,不无遗憾地说,陈先生已经去了上海。
哦,那怎么办?维经斯基迟疑道。
先去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见李大钊先生吧。
一切都拜托您啦,我听鲍立维同志安排。维经斯基对鲍立维的建议点头称是。
这位鲍立维是何方神圣?
关于鲍立维的身份,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来自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撰的《伟大的开端》,说他1918年秋,从海参崴坐船来天津北洋大学任教,教授俄语。他曾长期在海参崴生活,那里滞留了大量华人,鲍立维由此学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在天津、北京行走,交流无碍。鲍立维到北洋大学后,找到法科主任美国人福克斯,请他帮忙物色一位英文翻译,方便自己与在天津的英美朋友交流。福克斯向他力荐在北洋大学读法科的张太雷,材料上说张太雷是五四运动天津学生领袖,是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之一。当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向鲍立维提出要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时,鲍立维推荐的人选就是张太雷,说他可以联络李大钊。
还有一种说法,出自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他查证过民国时期的日本东京警视厅档案,他的考据是,鲍立维是1918年下半年来华,与天津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有关。还有的说鲍立维在十月革命后做了共产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石川祯浩又从当时中国警方监视档案查阅得知,鲍立维当时住在天津,每周数次到北京大学教授俄语,这足以证实,引维经斯基去见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首推鲍立维。当然还有第二个俄国人,就是时任北京大学法语和俄语教师的伊万诺夫。他的中文名叫伊文,生于俄国,1907年至1917年因参加十二月党人活动被通缉,逃至法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随后,作为克伦斯基的外交代表成员被派到中国。十月革命后,转而支持俄共。五四运动后,新学年开学,他到北京大学教授法语、俄语。维经斯基与李大钊相会,伊万诺夫也是引荐人之一。这一点在维经斯基发回国的报告中有所体现,称他是“来自法国巴黎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法语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报》事实上的编辑”。甚至西伯利亚发给维经斯基的电报,也经过《北京报》收转。同一时期在远东活动的俄国人达林(S.A.Dalin)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回忆录》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相较伊万诺夫,鲍立维在促成维经斯基与李大钊的相见上,当数首功。《包惠僧回忆录》写道:“他们初到北京,人地生疏,无法开展工作,后通过苏俄大使馆的关系,才找到了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又译柏烈伟),鲍原是同情十月革命的。他(维经斯基)由鲍立维的介绍而会见了李大钊同志。”
俄乡密使维经斯基在北大红楼与李大钊见面了。他第一次与李大钊见面,是试探性的,谈得并不深。虽然他对眼前这位被中国进步青年称为“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教授充满了兴趣,但是鉴于自己文化记者的身份,维经斯基不可能一下直奔主题,大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向,甚至商谈建党事宜,更不可能一见即成同志。他们只是泛泛而谈,但是双方都感觉甚好。临别时,李大钊写了一封信,让维经斯基带着到上海去见陈独秀。张国焘在回忆中说,维经斯基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杨明斋做助手,路经北京,由鲍立维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
其实,维经斯基1920年来到中国,当时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一的张国焘,并未见过其本人,也只字未提张太雷从中牵线搭桥之事,他从未听李大钊说起过张太雷带来见面的事情。且维经斯基与李大钊见面之后,张国焘也并未听李大钊说起他与维经斯基谈了什么。
随后,维经斯基又持陈独秀和李汉俊的信返回北京,再度见到李大钊。彼时,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北京的天空徘徊。
张国焘是这样回忆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的情景的:“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个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谈。”
“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来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们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原故。”
王会悟那时住在陈家楼上,她是窥破秘密的第一人。那是一个暮色时分,我见过维经斯基,就在我卧室隔壁一间书房里,王会悟吴语喃喃,回忆道,上海的夏天总下雨,天气很闷,因为陈夫人高君曼身体不太好,总咳嗽,有时还咯血,所以烧水倒茶的事情就交给我了。他们谈得很晚。
也是这样的梅雨天吧。也许那晚的雨没有今天下得这样大。一百年后的江南梅雨天,我站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电视屏幕前,凝视着王会悟老奶奶。我的眼前,总不时掠过王会悟戴金丝边眼镜的那张年轻的照片。且听王会悟老人的娓娓叙事:
那天晚上陈太太高君曼唤我,去烧壶开水,泡茶给客人。我下楼进厨房,烧好开水后入书房续水,那位维经斯基啊,年不过三十,中等身材,体格强健,一看就像长期做过工的人。他目光炯炯,英气夺人。他一直讲俄语,由山东口音的杨明斋翻译。
维经斯基几见陈独秀,他们在法租界见过多少次面,党史尚无记载。但是自从陈独秀与维经斯基见过面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有了活动经费,最突出的变化是《新青年》杂志8月号封面刊登美国社会主义党的徽标,接着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的出版。
那个夏天,维经斯基的心情很轻松,虽然上海的梅雨天没有俄罗斯的夏天舒服,但与20世纪初中国天空中的两颗巨星李大钊、陈独秀见面后,他的兴奋溢于笔端。1920年6月9日,他从上海发出第一份报告,致信海参崴远东局,欣然写道,“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特别是享有很高声望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教授陈独秀是中心人物。除了他公开的记者身份,维经斯基尤其强调真正的使命是了解和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到了8月17日,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致信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这时俄共(布)多家对华和远东工作机构经过整合后,一统于伊尔库茨克东方民族处。维经斯基在信中兴奋地写道:我在这里逗留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个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处,即出版处、情报煽动处、组织处。
也许因为保密,维经斯基没有透露那四位中国革命者姓甚名谁,但可以肯定,陈独秀、李汉俊一定名列其中。这个俄国人所说的革命局,可能就是后来的共产党的前身——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