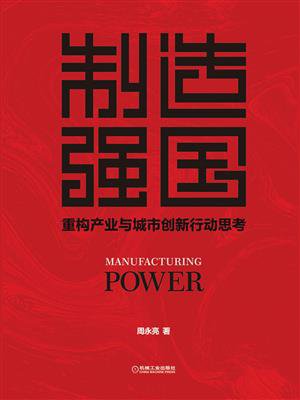二、成长的秘诀:是创造的基因,并非自然的红利
很多人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制造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民营企业家获得的成就是由于享受了时代的红利:大规模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等。这种说法很难说是错误的,但却不是最为关键的,因为这种红利对于所有经济主体、所有时代都是一样的,而且这种红利是一种历史的自然状态,之前也一直保持自然的存在。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与中国企业家的一个基因有密切关系,甚至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要素,那就是饥渴般地学习。乔布斯对于苹果价值观的描述:“Stay hungry”,就是永远保持求知若饥的状态,而中国制造业的很多企业家们绝大部分都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基因,因为他们深知,如果不学习,甚至如果不疯狂地学习,就跟不上这个时代,就随时可能被淘汰,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走上时代舞台的第一代企业家们,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受过良好且系统性的教育,面对中国羸弱的制造业,又见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强大制造业,对于这之间的差距有切肤之痛。
2000年前后,任正非到美国考察,到IBM参观时,一下就被IBM高效而强大的研发管理系统惊呆了,他知道这是正规军和游击队的距离。于是,他下定了决心,无论花多少钱也要学会这套管理模式。IBM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学这些,更没有想到是中国的一家小小的民营企业来学习,于是给任正非报了一个价格:300美元到680美元不等。大家一听到这个价格觉得也太便宜了点,其实不是这样的,IBM当时给华为派了70名顾问,这些顾问每小时的收费是在300美元到680美元不等,这对当时的华为可谓天价,而且他们在华为一待就是5年时间。据统计,这套研发管理系统让华为花了足足2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这几乎是当时华为一年的收入!很多人,估计包括IBM的人,都觉得任正非够“傻”的,对于这个价格都没有讨价还价。今天,还有谁认为当年的任正非“傻”呢?如果没有这“傻傻”的学习,怎么会有今天的华为?
我有一位企业家朋友,是江苏电缆领域的佼佼者,这家企业最早是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双方各占50%股份,使用日本品牌,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制造”绝对是品质的通行证。在高层管理方面,日方没有派一堆人,而是只派了一位总经理过来,具体技术和生产环节倒是相继派人进行指导。2012年前后,合资到期,日方准备撤走,企业品牌也不能再用日本品牌,只能用中方品牌。日方总经理临回国前,中方为他饯行,结果,这个日本人吃饭时酒喝多了。他酒后吐真言:“咱们一起工作将近20年,今天我该走了,告诉你们一件事,当时,我被派到中国来的时候,问上司到了中国企业应该怎么干,上司很神秘地说: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干!心想,这是什么指令啊。到了中国企业以后,我明白了上司的意思,就是不要主动让中国人学技术。”回日本几年后,当退休的他再回到中国看望这家企业的时候,立刻就惊呆了:这家中国企业离开日本的管理和技术,干得比以前好得多,规模也大了不少,其中国本土品牌也已经成为业内的知名品牌。尽管很友好,但是他的内心还是认为,这家企业离不开日本人,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看到他的表情,中方老同事们都开心地笑了:日本人在这儿的10多年里,我们好好地当好学生,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方法、一切时间去学习,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人肯定留着一手,只有千方百计地学习,才能获得真正的能力,才能受人尊重。
在制造业内,像这样狂热学习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正是中国制造崛起的第一个基因。
勤奋致富是第二个基因。中国人的生存意识极强,勤劳的品质全球公认。华人走到哪里,不管面临怎样恶劣的环境,都能够生存下来,而且生存得很好,往往会成为当地相对富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族群。依靠勤劳致富,这可能是中国人祖祖代代传承下来的基因,正像国家领导人提到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人的共同追求,而且这种追求是靠勤劳获得的,中国历来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训。
有一次,在德国的慕尼黑与一位德国朋友聊天,谈到中国人与德国人的比较,我说:“在中国人的眼里,德国人勤奋、敬业、遵守规矩,就像工作机器一样。”结果,德国朋友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周博士搞错了,跟中国人相比,德国人哪里像机器人,中国人可以自觉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连续多年如一日,德国人一天工作八小时,一分钟都不多干,中国人太勤奋了,德国人根本竞争不过中国人。”
我相信,正是有了这种勤劳致富的品质和追求,才能让企业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后退、不逃避,而是迎难而上,坚持到底。我在浙江嘉善看到一位70后汽车零部件企业老板,其企业年收入超过3亿元,毛利润超过了30%。一种普通的汽车零部件,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毛利?等我知道了他每天(不分节假日)都要工作12个小时且没有什么娱乐爱好的时候,看到了他那分散在三个地方的简易车间和简陋的办公楼的时候,其实心中就有了答案。这样的企业家,我在苏浙以及山东一带遇到很多。他们与普通人最大的不同就是罕见的勤劳和专注,以及自律。这正是中国制造崛起的第二个基因。
敢于创新是第三个基因。制造业是不可能依靠自我封闭发展的,只有创新才是唯一正道,而中国制造的成长恰恰就是创新的推动力,这里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思维,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拿来主义创新,也有“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不甘服输的技术创新,还有“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客户需求模式创新。曾几何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有一个观点:新教精神及其形成的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创新机制的根源。同时也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东方的儒家伦理可能是东方不能诞生资本主义的精神根源,而且对现代社会的创新会产生阻碍。这一观点的提出似乎解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创新的崛起以及东方为什么不能诞生现代工业创新体系。其实,这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的总结式分析。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泰勒在他的著作《为什么有的国家创新力强》中谈及20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卡德韦尔阐述的一个定律:从数千年的历史看,一个国家的创造力只能维持短暂的时期。幸运的是,总有国家接过创新的火炬。作者进而认为,这一现象其实与国家体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创新更重要的推动力是“国家不安全感”,因为他已经发现,从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看,创新可以发生在任何一种体制下,只要这种体制活力充沛,有一种生存危机意识,就是所谓的“不安全感”,而中华民族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意识体系中,“居安思危”恰恰是其最底层的逻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繁衍数千年,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出现断裂,与这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有关。而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全面释放了民族的这种危机意识,刺激了我们的企业家群体“只争朝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而这一基因,仍然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家在新时代取得新成就的基础推动力。
鉴于本书篇幅有限,我很难对改革开放40多年的制造业发展进行全景式扫描,力图通过三家典型企业的成长史来探讨优秀企业家在中国制造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