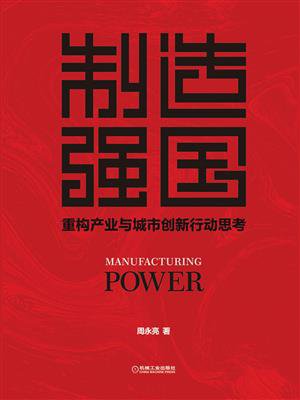三、华为的成长:拼命学习与疯狂研发的中国制造业标杆
创业时期只有14个人、2.4万元资产,靠倒卖海外小型交换机起家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全球营业收入超过8500亿元,不仅成为世界500强的重要一员,排名第61位,还成为电信设备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
华为成功的经验有千万条,我觉得,如饥似渴的狂热学习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条。2014年5月,在英国伦敦接受媒体采访时,任正非反复强调的一个关键词:开放。他强调,唯有开放,才是促进华为进步的力量。两年后,2016年5月,任正非与华为的合作伙伴座谈时说:“苹果公司很有钱,但是太保守了;我们没有钱,却装成有钱人一样疯狂投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华为人大手大脚,而是说苹果因有钱而陷入保守。华为尽管没有像苹果那么有钱,但是因为心存危机感反而心态更加开放了。在任正非看来,华为天生有许多被约束的条件,民营企业、无资本、无背景、无历史,创始团队中无一人有过企业管理的经验,这些都迫使华为必须走开放之路,尤其是在面对国际市场的时候,封闭自我就会被踢出游戏之外。
只有开放才能虚心学习。正是如此饥渴学习的归零心态,任正非用28年时间花费20亿元向IBM学习研发管理以及高科技公司的管理,为了管理的现代化不惜“削足适履”,用他的话说:“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企业需要有全球化的战略眼光才能发愤图强,一个民族需要汲取全球性的精髓才能繁荣昌盛,一个公司需要建立全球性的商业生态系统才能生生不息。”基于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任正非都强调不搞“自主创新”,义无反顾地获取可以获取的现成技术,早期是能模仿就模仿,不怕别人笑话自己“模仿”和“偷学”,“拿来主义”更加务实高效,他说,“在我们创新的过程中,只做我们有优势的部分,别的部分应该更多地开放与合作”。
毫无顾忌地向标杆学习、向对手学习、向具有特殊优势的企业学习,成了任正非的饥渴学习性格。为此,他的一句口头禅是:“不要脸”才能生存。他说他最“不要脸”,所以他进步最快,他也要求所有干部如是。“要脸”的人自尊心较强,就会不善于学习,也觉得没什么可以学习的,容易故步自封,成为井底之蛙。任正非心中明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尤其是华为所处的电信设备以及信息技术领域更是一个瞬息万变的领域,稍有不慎,则万劫不复。
因为有了如此强烈的学习意识,华为的进步就变成了为生存而奋斗,其内在动力可想而知。
第二条经验,疯狂无解的研发投入。业内都知道,华为的研发是疯狂的,尽管它没有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早期也很难从银行那里借到钱,但是,任正非认准了一条道:身处这样的一个行业,核心技术是生存之本。因此,华为几十年如一日将研发费用保持在销售收入的15%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公开的资料,2015年,苹果营收2330亿美元,实际研发投入为81.5亿美元,高通营收253亿美元,实际研发投入为55.6亿美元,而华为营收608亿美元,实际研发投入为90亿美元,比对手高通高出近40%。这算不算疯狂的投入呢?
投入这么多值得吗?任正非说过,华为研发20年浪费了至少1000亿元。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巨大的沉没成本怎么能有收获呢?当2019年5月16日美国签署法令,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对华为实施“禁用”和“禁供”之后,有的美国议员直接在社交账号上发了一个“推特”:华为死了。但是,令美国人,更令全球惊诧的是,第二天,华为正式启用自己的芯片——海思芯片替代美国供应商的芯片,即使全部美国供应商断货,华为手机照样可以正常生产。“备胎”研发计划开始为世人所知。
1991年,华为就成立了Asic设计中心,即海思的前身。2004年,海思正式成立,主要是设计路由器芯片和网络设备调制解调器。2011年,余承东成为华为终端负责人,华为开始考虑为手机设计芯片。2012年,华为最神秘的部门“2012实验室”成立,这是华为的总研究组织,名字来源于2012年上映的电影《2012》。任正非观影后认为未来信息爆炸会像数字洪水一样,华为要想在未来生存发展,就要未雨绸缪,需要构造自己的“诺亚方舟”,并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芯片每投片一次的成本都在百万美元以上。可以说,海思的麒麟芯片是任正非用大把大把的钱“烧”出来的。
凭借如饥似渴的开放学习、疯狂且不计成本的研发,华为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给中国的制造业树立了一个标杆:如果想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如果想成为行业的领袖,没有脱胎换骨的疯狂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个战场太残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