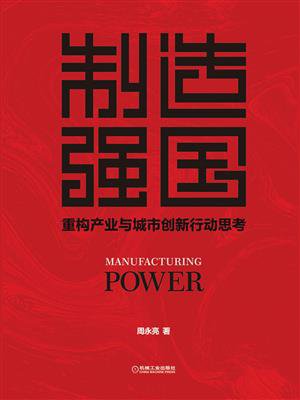三、中国制造的严峻挑战:内在的劣势与外部的“卡脖子”
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是有目共睹的,从内部而言,劳动力廉价的客观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在一些重要环节甚至比美国的人工成本还要高。不仅像富士康、福耀玻璃等知名大型企业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一些中小制造企业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我的一位师兄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巴尔的摩建了一个礼物蜡烛厂,员工月薪为1000美元,若干年后应家乡招商引资吸引,他在杭州开发区也建了一个同样的工厂,月薪当时是3000元,算是较高的,具有明显的人工成本优势。到了2010年,美国工人的工资依然是1000美元,杭州的月工资6000元都很难找到一线员工了,这还不包括社保等相关成本,最后只能关门大吉,他又将工厂搬到了越南。经过我本人的调查,类似的情况在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家电等领域也存在。当然,环境治理、税费高等也都让很多传统的制造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根据《2016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制造业企业认为当前负担重的领域依次为人工成本(64%),融资成本(55%),水、电、气、土地等要素成本(50%)。在收费领域,45%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水、电、气等机构收费负担最重,其次为银行收费(39%)。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税费成本偏高、能源原材料成本较高、汇率成本提高和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过高等问题仍有待改善。
不过,更为严重的是在高速发展中的装备制造业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严重“内伤”和“硬伤”。
所谓内伤,就是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发展中的体制还不是很顺畅:一是,我们的重大技术装备规划制定、创新研发、产品推广与应用、扶持资金等职能分散在多个国家部委办局,缺乏强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资金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在形成合力方面尚需进一步加强。二是,体制内的创新能力尚未有效释放。以大型央企为代表的骨干力量发展活力欠佳,创新效率与市场变化的节奏明显有差距。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零部件制造企业难以进入相对封闭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体系,存在创新资源在体制内“打圈圈”的现象,有时会出现有些主管部门拨付的款项花不完,但不少民营装备制造企业却面临“断顿”的危险。
我国装备制造业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内伤”就是推广、应用难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徐东华教授在《智慧中国》杂志2019年第10期发文指出:“在重大短板装备需求中,研发产品已经工程化定型但亟待产业化推广应用的约占25%,科研成果与产业化应用脱节现象仍然较为严重,我国企业在投入巨资研制出首台(套)产品后,国外垄断企业往往通过数倍降低同等产品价格等方式进行打压。”同时,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差距。近几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5%,远低于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技术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14年,国家科技部统计显示,47.3%的(国家主体科技计划)课题成果得到了转化。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基于905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截至2014年年底的全部有效专利数据测算出,高校专利许可率为2.1%、转让率为1.5%,科研单位专利许可率为5.9%、转让率为3.5%。2015年,清华大学教授通过对全国682所高校进行专项问卷调查测算出,“高校近5年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估值为17.6%”。也就是说,科研成果的浪费现象值得关注,国家花费了大量经费支持科研,如果只是变成了论文或者专家评估通过的成果而不是能经受市场检验的成果,那对于我国的制造业实际上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除此之外,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硬伤”更值得关注,即高端装备和关键部件受制于人。一是,重点领域发展急需的专用生产设备、专用生产线及专用检测系统等存在明显短板,如集成电路、新材料、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产线装备绝大部分依赖进口。二是,部分关键部件仍未掌握核心技术。初步统计,重大技术装备进口免税目录中直接进口的零部件和原材料涉及十多个重点领域。三是,一些高端装备长期面临发达国家封锁。国家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95%以上的12英寸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100%的高端医疗CT球阀依赖进口,液晶面板关键生产设备基本由美国企业提供;我国95%以上的高档数控系统依赖进口;六轴或以上高端工业机器人市场近90%被日本和欧美企业占据;民用飞机航空发动机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动力电池等核心技术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生产一致性、循环寿命等关键指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高技术船舶概念设计对外依存度较高,且我国尚未进入设计建造难度非常大的大型游轮领域。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这就是俗称的“卡脖子”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