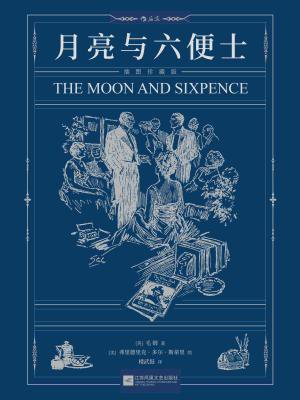8
回头读读我笔下的斯特里克兰夫妇,我发现他们竟显得有些模糊。要让书中人物栩栩如生,必须赋予他们相应的性格特征,我却没能写出这些特征。想到这或许是我的错,我开始绞尽脑汁地回想那些能让他们生动起来的气质癖好。我觉得,若能详述某些说话技巧或奇特习惯,我应该就能呈现出他们的特别之处。而像现在这样写,他们就像旧挂毯上的人像,无法从背景中分离出来。远远望去,几乎连轮廓也看不清,只能瞧见一团漂亮的颜色。我能找到的借口只有一个:他们给我的印象便是如此。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有些人就是如此模糊。他们生活在这个有机体内,也只能依附着它而活。这些人就像人体里的细胞,虽必不可少,但只要健康活着,就会淹没在一个巨大的整体里。斯特里克兰一家就是普通中产家庭的一员:讨人喜欢、殷勤好客的妻子热衷结交文艺界小名人,但这种嗜好也无伤大雅;沉闷无趣的丈夫,尽心尽力地过着仁慈上帝为他安排的生活;最后便是两个漂亮健康的孩子。这样的家庭再平凡不过,我真不知道他们身上哪儿还有能引起好奇者关注的东西。
回想后来发生的事,我不禁自问:我是否真的太过愚钝,才没看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非凡之处?或许是吧。时隔多年,如今我已深谙人情世故,但即便在初识斯特里克兰夫妇时便有此阅历,我应该也会做出同样的判断。但因为我已经知道人心难测,所以现在的我不会像那年初秋刚回伦敦时一样,为那个消息惊讶万分。
返回伦敦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我便在杰明街碰见了罗丝·沃特福德。
“你看起来真高兴,”我说,“乐什么呢?”
她笑了,眼里闪着我熟悉的那种狡黠之光。这意味着,她又听到了某个朋友的丑闻。这位女作家的直觉相当敏锐。
“你见过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了,对吧?”
不仅脸,她的整个身体都透着股轻快劲。我点点头,心想那可怜的家伙是不是在证券交易所血本无归,或者被公共汽车撞了。
“难道不可怕吗?他丢下妻子跑啦。”
沃特福德小姐肯定觉得,在杰明街边说这事对这个话题不公平,于是像个艺术家一样,只抛出事实,随后便声称对细节一无所知。我虽然并不认为如此微不足道的环境问题能阻止她讲述此事,但她就是不肯让步。
“我说啦,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激动地问了几个问题后,她却只快活地耸耸肩,“我相信,伦敦的哪家茶室,准有个年轻姑娘辞职了。”
她冲我笑笑,说已经跟牙医约了时间,便喜滋滋地走了。
得知这个消息,我其实并没多么苦恼,反而勾起了更多兴趣。那时候,我亲身体验的事情并不多。所以,只会发生在书中人身上的事,竟发生在我认识的人身上,顿时让我兴奋起来。诚然,岁月已经让如今的我习惯这样的事,但当时的我,还是有点儿震惊。斯特里克兰肯定已过四十,这把年纪的男人还牵扯情爱之事,真是令人作呕。过于年轻让我傲慢地认为:一个男人陷入爱河,却又不会让自己成为大傻瓜,那他绝不能超过三十五岁。此外,这个消息也给我带来了些许困扰。因为我在乡下时就写信给斯特里克兰太太,不仅告知了我的返程日期,还说她若不回信另作安排,我就找一天去跟她喝茶。而这天就是今天,我也的确没有收到斯特里克兰太太的回信。她到底想不想见我?心烦意乱之下,她很可能早已把我的信抛到脑后。或许,我应该明智地不去赴约。可话说回来,她或许想瞒下此事,那我若表现出已得知这个奇怪的消息,就太草率了。我左右为难,既怕伤害她的感情,又担心去了惹她心烦。她现在肯定很痛苦,我不想看别人痛苦,自己却爱莫能助。但我又打心里想去瞧瞧斯特里克兰太太会如何应对。这想法真让我觉得有点儿羞愧。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最后,我突然想到:完全可以若无其事地登门拜访,先让女仆进去通报,问问斯特里克兰太太是否方便会客。这样,她便有了能将我打发走的机会。然而,跟女仆说出这番早已准备好的话时,我还是相当尴尬。站在幽暗的走廊等待回复时,我必须鼓起全部勇气,才没有临阵脱逃。女仆回来了。可能过于兴奋让我胡思乱想,但从她的举止来看,我真觉得她已经彻底知晓这桩家庭惨剧。
“先生,请这边走。”她说。
我跟着她走进客厅。百叶窗没有完全拉开,免得屋里太亮。斯特里克兰太太背光而坐。她的姐夫麦克安德鲁上校站在壁炉前,就着还未燃旺的炉火烘烤后背。我觉得自己来得真不是时候,肯定让他们很意外。斯特里克兰太太之所以让我进来,不过是忘了叫我推迟来期而已。我还觉得,上校肯定很讨厌我这番中途打扰。
“我不确定你是不是在等我。”我努力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当然盼着你来。安妮,赶紧上茶。”
即便客厅昏暗,我也看出斯特里克兰太太的脸都哭肿了,她那向来不怎么好的皮肤,如今更变成了土灰色。
“你还记得我姐夫吧?假日前,你们在那次晚餐上见过。”
我们握了握手。我正腼腆地不知该说什么好,斯特里克兰太太解救了我。她问我这个夏天是怎么过的,我总算循着话头说了几句,直到女仆端来茶水。上校要了一杯威士忌苏打。
“你最好也来一杯,埃米。”他说。
“不,我还是喝茶吧。”

这是第一个暗示:的确发生了不幸的事。我佯装不知,竭尽全力地跟斯特里克兰太太闲聊。上校依旧站在壁炉前,一言不发。我寻思着再过多久才能体面地告辞,也很奇怪斯特里克兰太太到底为什么让我进来。屋里没有花,夏天收起来的各种小玩意儿也没有再摆出来。以往那般亲切愉快的房间,似乎生出某种阴郁僵滞之感,让人觉得非常奇怪,仿佛墙的另一边躺了个死人似的。我喝完了茶。
“来根烟吗?”斯特里克兰太太问。
她四下寻找烟盒,却没找到。
“恐怕已经没了。”
她突然失声痛哭,匆匆跑出了客厅。
我吓了一跳。估计烟向来都是她丈夫买,现在找不到了,又让她想起了丈夫。发现从前习以为常的小小慰藉都没有了,这种新的感觉仿佛扎了她一刀。她意识到,过去的生活已经远去,不复存在。我们亦再也无法维持表面的交往。
“我看,我该走了。”我边对上校说,边站起身。
“你估计已经知道,那个浑蛋把她抛弃了吧。”他突然大声嚷道。
我迟疑了。
“你知道,人们总要说闲话的,”我回答,“有人含含糊糊地跟我说出了事。”
“他跑了。跟一个女人去巴黎了。离开埃米,一分钱都没留下。”
“非常抱歉。”除此之外,我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上校一口喝掉了威士忌。他又瘦又高,五十来岁,留着两撇下垂的八字须,头发灰白。他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嘴巴显得没什么生气。上次见面后,我就记住了他这张傻乎乎的脸,也记得他如何骄傲地自夸,说他离开军队前一周打三次马球,十年都未间断。
“我想,我不该再打扰斯特里克兰太太了,”我说,“请您转告她,我很难过。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我很乐意效劳。”
他没搭理我。
“真不知道她以后怎么办。还有孩子呢。难道让他们喝西北风长大吗?十七年啊!”
“什么十七年?”
“他们结婚十七年,”他厉声道,“我从没喜欢过他。当然,他是我妹夫,我已经尽量容忍。你认为他是绅士吗?她就不该嫁给他。”
“难道一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她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和他离婚。你刚进来时,我正在跟她说这个。‘亲爱的埃米,向法院递交诉状,’我说,‘为了你,也为孩子。’最好别让我见到他,否则我非把他打个半死不可。”
我忍不住想,麦克安德鲁上校怕是没这本事揍人。因为斯特里克兰身强力壮,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在道德上遭到侮辱的人,却没有直接惩戒罪人的力量,总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我正打算再次告辞,斯特里克兰太太回来了。她已擦干眼泪,并且在鼻子上扑了粉。
“真对不起,我刚才没忍住,”她说,“很高兴你没走。”
她坐了下来。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好意思谈论与自己无关的事。那时,我还不了解女人根深蒂固的恶习:热衷于跟任何有意倾听的人谈论自己的私事。看起来,斯特里克兰太太似乎已经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大家都在说这件事吗?”她问。
我大吃一惊。她竟认为我已经完全了解这场家庭变故。
“我刚刚回来,只见过罗丝·沃特福德。”
斯特里克兰太太握紧双手。
“告诉我,她到底说了什么。”我有些迟疑,她却不依不饶,“我特别想知道。”
“你知道别人会怎么说。她不太靠得住,对吧?她说,你丈夫抛弃了你。”
“就这些?”
我没有复述罗丝·沃特福德临走时,提起的那句茶室姑娘的话。我撒了谎。
“她没说他跟什么人一起走的吗?”
“没有。”
“我只想知道这个。”
我有些困惑,但不管怎样,我该走了。跟斯特里克兰太太握手告别时,我说要是有什么能做的,我非常乐意效劳。她挤出一个疲惫的笑容。
“非常感谢。我不知道谁还能为我做什么。”
我腼腆得无法表达同情,于是转身同上校告别。他没有跟我握手。
“我也要走了。如果你从维多利亚街走,我们同路。”
“好,”我说,“那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