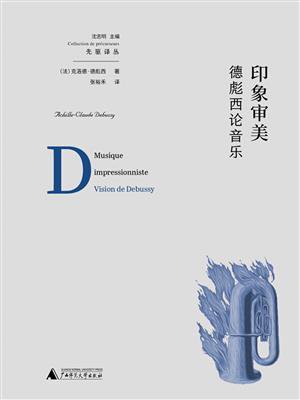夏尔·古诺

许多没有定见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是音乐家——心里在想为什么歌剧院执意要上演《浮士德》呢?这其中有许多理由,而最佳的理由是,古诺的艺术代表了法国人一段多愁善感的时期。大家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古诺的那些作品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关于《浮士德》,杰出的音乐评论家曾责难古诺歪曲了歌德的思想。同样,这些杰出的人物,从不曾想到去看一看瓦格纳是否曾经歪曲过汤豪塞
 这个人物。汤豪塞在传说里完全不是瓦格纳塑造的那个悔过的好小伙子,他那被怀念维纳斯的烈火烧焦了的树棍从未重新开花。在这次创作中,古诺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是法国人,而汤豪塞和瓦格纳,二位都是德国人,那就不可饶恕了。
这个人物。汤豪塞在传说里完全不是瓦格纳塑造的那个悔过的好小伙子,他那被怀念维纳斯的烈火烧焦了的树棍从未重新开花。在这次创作中,古诺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是法国人,而汤豪塞和瓦格纳,二位都是德国人,那就不可饶恕了。
我们法国人喜爱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喜爱音乐就少了。可是有些很有能耐的人,由于每天听音乐,而且什么牌子的音乐都听,便自称是音乐家。不过,他们从来不写曲子……他们鼓励别人写。一般说,一个学派就是这样创立起来的。你们不要跟这些人去谈论古诺。他们会从他们偶像的高度对你们表示蔑视。他们偶像的最可爱的品质,就是可以换来换去。古诺不属于任何学派。这有点儿跟群众惯常的态度一样。群众对许多审美诱惑的回答是,回到他们已经习惯了的东西上去。这并不总是最好的趣味。这样做,不当心会从《胜利大爷》 [1] 摇摆到《女武神》那边去,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的。很奇怪,构成社会精英的那些人,可以为知名人士或权威人士敲锣打鼓,进行炒作,不过这只是昙花一现,没有任何效果。教育者忙得上气不接下气,而群众不为人知的伟大心灵却不肯上当。艺术继续在自己愿意的地方传播……歌剧院固执地上演着《浮士德》。
然而人们应当有自己的主见,并承认艺术对群众是绝对无用的。艺术更不是少数精英人物(他们常常比群众还要愚蠢)的自我表达方式。艺术只是一种潜能巨大的美,需要的时候,便会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爆发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命令群众爱美,也不能要求群众倒过头来用手走路。顺便说一说,柏辽兹对群众的影响几乎是公认的,没有任何事先的宣传,这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说古诺的影响是可以否认的,那么瓦格纳的影响就十分明显了,但他的影响只涉及专业工作者,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影响是不全面的。应该承认,没有什么比新瓦格纳派更令人悲哀的了。在这个学派的作品里,法兰西精神被穿短筒靴的“沃坦”和穿天鹅绒上装的“特里斯坦”的冒牌货淹没了。
虽然古诺没有写出人们所期望的圆润的旋律,人们应当赞美他巧妙地摆脱了气势逼人的瓦格纳风格的影响。瓦格纳的十足德国人的概念,在他所期望的艺术融合中也没有解释得十分清楚。艺术融合,现在差不多成了为文学招揽读者的一句口头禅。
古诺虽有欠缺之处,仍是不可少的。首先他的音乐修养很好。他谙熟帕莱斯特里纳的作品,跟巴赫“合作”
 过。他对传统的尊重是相当明智的,所以不去大声宣扬格鲁克的名字——另一个相当难以捉摸的外国影响。他宁愿建议年轻人喜欢莫扎特,这证明他非常无私,因为他从未受过莫扎特的启发。他跟门德尔松的关系比较清楚,他从门德尔松那儿学会了在不同音高上发展旋律的办法。当人们灵感不来的时候,这办法用起来十分方便。(总之,门德尔松对他的影响要比舒曼对他的影响更直接一些。)此外,古诺放过了比才,这是很好的。不幸,比才死得太早了,只留下一部杰作。虽然如此,法国音乐的命运还是再度成了问题。她又一次像个漂亮的寡妇,由于身边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给她引路,而投入糟蹋她的外国人的怀抱。我们并不否认,艺术上的某些联姻是必要的,至少,联姻要带来些好东西。选择叫得最响的人做亲,不等于跟了最伟大的人物。这种联姻关系只是利害关系,这是屡见不鲜的,而且暗地里被当作手段,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成功。像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一样,这种联姻是没有好结果的。进口到法国来的艺术,让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收下吧。不过我们也不要让人家骗了。不要听见芦笛就心醉神迷。相信吧,外国人是不会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正相反,我们的和蔼可亲,换来的是外国人的那副板着的面孔,既无礼貌,又有点儿可笑,这态度是我们惹出来的。
过。他对传统的尊重是相当明智的,所以不去大声宣扬格鲁克的名字——另一个相当难以捉摸的外国影响。他宁愿建议年轻人喜欢莫扎特,这证明他非常无私,因为他从未受过莫扎特的启发。他跟门德尔松的关系比较清楚,他从门德尔松那儿学会了在不同音高上发展旋律的办法。当人们灵感不来的时候,这办法用起来十分方便。(总之,门德尔松对他的影响要比舒曼对他的影响更直接一些。)此外,古诺放过了比才,这是很好的。不幸,比才死得太早了,只留下一部杰作。虽然如此,法国音乐的命运还是再度成了问题。她又一次像个漂亮的寡妇,由于身边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给她引路,而投入糟蹋她的外国人的怀抱。我们并不否认,艺术上的某些联姻是必要的,至少,联姻要带来些好东西。选择叫得最响的人做亲,不等于跟了最伟大的人物。这种联姻关系只是利害关系,这是屡见不鲜的,而且暗地里被当作手段,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成功。像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一样,这种联姻是没有好结果的。进口到法国来的艺术,让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收下吧。不过我们也不要让人家骗了。不要听见芦笛就心醉神迷。相信吧,外国人是不会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正相反,我们的和蔼可亲,换来的是外国人的那副板着的面孔,既无礼貌,又有点儿可笑,这态度是我们惹出来的。
最后,这篇札记谈及的想法,由于篇幅太短而无法尽言,而且有时跟古诺的思想有矛盾。让我们不要拘泥于僵硬的信条,借此机会,恭恭敬敬地向古诺致意吧。我们还要看到,被人怀念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并不一定需要什么了不起的理由。使大部分的同时代人感动,这是最好的理由。古诺以博大的胸怀,为此尽心尽力了,将来谁也不会想到要否认这一点的。
[1] 《胜利大爷》( Père la Victoire )是19世纪末的一首流行歌曲,由吕西安·德洛梅尔和莱翁·伽尼埃作词,路易·伽纳作曲。伽纳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以写轻歌剧和流行歌曲著称。